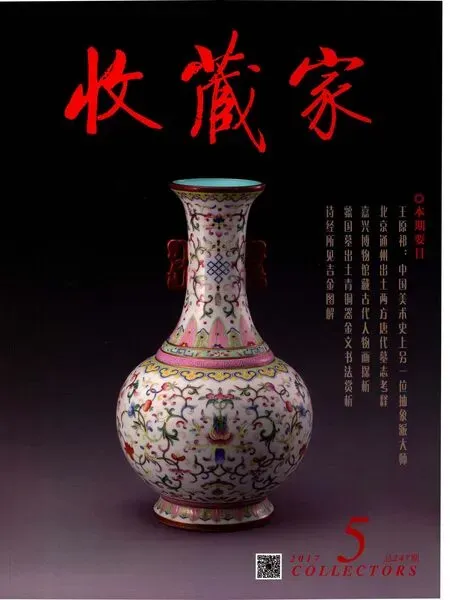《詩經》所見吉金圖解吉金藏詩禮 精神孕山岳
□ 王宏
《詩經》所見吉金圖解吉金藏詩禮 精神孕山岳
□ 王宏
“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一首首詩,道盡上古初民的悲歡離合,摯愛情殤。她猶如一幅活脫脫的歷史畫卷,將上至達官顯貴,下至黍離百姓的生活場景盡顯眼前:既有戰(zhàn)場上“擊鼓鏜鏜,踴躍用兵”的喋血廝殺,也有情侶間“舒而脫脫兮,無使尨也吠”的卿卿我我;既有王侯將相“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的歌舞升平,也有布衣農夫“無衣無褐,何以卒歲”的饑寒交迫。字字句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恰如奔騰的長河,清澈、純美、潺潺不絕。這也許就是孔夫子“去其重,取可施予禮儀三百五篇”的精華所在吧。
在那個敬鬼神、尚禮儀的年代,金光燦燦的青銅器以其具有“明尊卑、辨等級”的藏禮作用而被時人冠以“吉金”的美稱,更因其活躍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為世間所珍視。那么《詩經》所言的銅器到底長什么樣子,有什么作用,在人們的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就讓我們依據傳世及考古所見的青銅器資料,比照《詩經》所載,通過文圖對照的方式,為大家奉獻這一份吉金之美吧。

圖1 西周鼎及銘文拓片
一、吉金之祭祀篇
《詩經·絲衣》: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這首詩中青銅炊器有鼐、鼎、鼒,皆為祭祀用烹煮器。毛詩傳:“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是以知“鼐”、“鼒”皆為鼎之別稱。自名為“鼐”的鼎目前還沒有發(fā)現,1940年陜西扶風任家村出土一件鼎,銘曰“作父庚鼒,□冊”(圖1)。這是考古材料中“鼎”可以稱為“鼒”的實物例證;2004年安陽大司空村南商代墓葬出土一件馬危鼎,出土時內部貯存許多獸骨,確證鼎確實可以作為炊煮器(圖2)。除圓鼎以外,還有方鼎,主要流行于商代至西周早期,上海博物館保藏有一件西周早期的厚趠方鼎(圖3),裝飾華美,極其金貴,器主厚趠是西周時期的高級貴族。
酒器有兕觥。觥作為酒器,在商末周初最為發(fā)達,是商人重酒的典型表現。美國佛利爾美術館藏有一件商代晚期的獸面紋觥,整個器體由鳳鳥紋、獸面紋和浮雕帶雙角的夔龍組成(圖4),這件經過精工設計,紋飾變化多端的器物,是尊神重鬼的商人精神世界的形象表現。還有一種寫實性的動物形觥,學術界稱為犧觥。美國哈佛大學藝術博物館保藏有一件牛形犧觥,背部還有一夔龍形捉手的蓋子,造型十分生動(圖5)。

圖2 .1 商代 馬危鼎

圖2 .2 馬危鼎內獸骨

圖3 西周早期 厚趠方鼎

圖4 商晚期 獸面紋觥

圖5 牛形犧觥

圖6 西周 鄧仲犧尊
《絲衣》是描寫貴族祭祀場面的史詩:主人穿著潔白明秀的祭服,帶著崔嵬的高冠,邁著輕緩的步伐,表情嚴肅莊重,從廟堂里到門內,鼎里的牛、羊、豬熱氣騰騰,彎彎的兕觥盛著清潔的酒水,香味濃郁而又芳香。主人進退有節(jié),禮讓有度,虔誠的進行祭祀,希望祖先神靈保佑子孫健康長壽。祭祀用“牛、羊”,屬于祭禮品級中的“太牢”之禮,可見規(guī)模之大,等級之高!
《詩經·閟宮》: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
犧尊為《周禮》“六尊”之一,是做成動物形象的一種盛酒器,在考古發(fā)掘中較為常見。1984年西安市長安區(qū)馬王鎮(zhèn)張家坡西周墓出土一件西周時期的鄧仲犧尊,為一帶翼神獸造型,體表裝飾獸面紋,前胸、頭頸及臀部各有一爬龍,背部還有一鳳鳥形捉手的蓋子(圖6)。圓圓的雙眼、緊閉的雙唇顯示出惟妙惟肖的靈動之氣,十分可愛。還有一種鹿形犧尊,2012年寶雞石鼓山墓地出土的鹿尊,大致輪廓跟鄧仲犧尊有些相似,也是西周時期犧尊中的精品(圖7)。
《閟宮》是歌頌魯僖公文治武功的詩篇,內容主旨在于希望魯僖公能夠恢復魯國在西周初年為諸侯尊長的顯赫地位。詩文將魯僖公進行“秋嘗”之禮時的祭器一一羅列。獻祭之時,盛酒的犧尊互相碰撞,發(fā)出鏗鏗鏘鏘的聲音,用燒烤的小豬熬煮肉湯,盛入籩豆、大房這樣的祭器當中,祭祀的舞者長袖翩翩,匯成一片彩色的海洋,魯公的尊貴盡顯無遺。
《詩經·生民》: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
“豆”是一種高腳的盛食器,“登”是陶質的豆,《爾雅·釋器》云:“瓦豆謂之登。”1989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一件獸面紋假腹豆(圖8),紋飾華美,端莊大方。最為著名者有隨州擂鼓墩1號墓出土的曾侯乙豆(圖9),器主為戰(zhàn)國時期的曾國國君,地位十分顯赫。西周時期還流行一種自名為“鋪”的器物,器型似豆,是豆的一種派生物,與豆的區(qū)別在于“鋪”的口沿較豆略淺,柄部較粗且鏤空,而豆是實體柄,1976年陜西扶風莊白窖藏出土的微伯鋪,是西周時期的鋪中精品(圖10)。
《生民》是描寫農神后稷祭祀上帝的場景:后稷將祭品盛放在木豆里、再盛放在陶豆里。當祭品的香味裊裊升起的時候,上帝就來享受后稷的祭祀。飯菜的味道實在是太鮮美了,后稷開始創(chuàng)制了祭祀之儀。
《詩經·韓奕》: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壺,盛酒器。《周禮·秋官·掌客》:“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視飱牽。……壺四十。”鄭玄注:“壺,酒器也。”正是具有盛酒的功能,青銅壺才能在酒文化發(fā)達的先秦社會存在近千年之久。除酒器外,春秋以后壺還可以作為水器,在禮儀生活中和盤配套,代替匜、盉充當盥洗用器的角色。
這首詩是描述韓侯朝見周宣王離京時由朝廷卿士餞行的盛況:韓侯朝見宣王出京后,照例進行出行祖祭的禮儀,禮畢之后住宿于屠這個地方,顯父前來為韓侯餞行,奉上清酒百壺。餞行用清酒百壺,反映韓侯重要的政治地位及享受的尊榮。

圖7 西周 鹿形犧尊

圖8 假腹豆

圖9 戰(zhàn)國 曾侯乙豆

圖10 西周 微伯鋪

圖11 西周 三年壺

圖12 西周 十三年壺
二、吉金之軍旅篇
《詩經·采芑》: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玱玱。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方叔率止,執(zhí)訊獲丑。戎車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
軧、衡,都是戰(zhàn)車構件。2013年湖北葉家山曾國墓地出土有西周時期的車軧實物(圖14);2012年寶雞石鼓山石嘴頭墓葬中出土有西周早期的車衡(圖15)。
鸞即鑾,裝飾在車上的鑾鈴,在車子運動中發(fā)出悅耳的響聲。1980年扶風黃堆鄉(xiāng)4號墓出土兩件西周早期的鑾鈴(圖16),保存完整,十分精美。
鉦,一種青銅樂器,軍旅之事中用于軍隊的進退行止,鉦人泛指掌管軍旅樂器的官吏。1958年陜西旬陽縣城北出土有戰(zhàn)國時期的一件銅鉦(圖17),可以說是“鉦”的考古實物例證。鼓即戰(zhàn)鼓,青銅戰(zhàn)鼓的起源很早,1977年湖北崇陽就曾出土過商代晚期的青銅戰(zhàn)鼓,體量很大,制作精美(圖18)。戎車即兵車,青銅兵車出土極為罕見,1965年江蘇漣水三里墩出土一套戰(zhàn)國時期的戰(zhàn)車戰(zhàn)馬,車上還有一御手,頭束高髻,舒臂執(zhí)轡,表現出一副策馬驅馳的緊張神態(tài)(圖19)。

圖13 戰(zhàn)國 曾侯乙壺

圖14 西周 車軧

圖15 西周早期 車衡

圖16 西周早期 鑾鈴

圖17 戰(zhàn)國 銅鉦

圖18 商晚期 青銅戰(zhàn)鼓
《采芑》是描繪周宣王卿士、大將方叔為威懾荊蠻而演軍振旅的畫面。著重表現方叔指揮的這次軍事演習的規(guī)模與聲勢,同時盛贊方叔治軍的卓越才能。
《詩經·長發(fā)》: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鉞,兵器。戰(zhàn)爭中秉鉞為權力的象征,《尚書·牧誓》“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即是明證,山東益都蘇埠屯墓地出土一件人面紋銅鉞(圖20),紋飾恐怖猙獰,上有銘文“亞醜”二字,年代在商代晚期,武王所秉當即此類。陜西寶雞竹園溝13號墓曾出土過一件人頭銎鉞(圖21),銎作人首狀,造型奇特,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長發(fā)》是描寫成湯討伐夏桀之戰(zhàn)中,成湯威風凜凜,兵勢所向無前的軍旅場面。
《詩經·無衣》: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戈、矛、戟皆是戰(zhàn)斗兵器,在考古發(fā)掘中屢有出土。
戈,勾兵器,常用于先秦車戰(zhàn)當中,用于勾斷敵人脖頸。戈在考古中出土數量很多,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收藏的秦“櫟陽”銅戈(圖22),年代在戰(zhàn)國時期,戈正面刻有銘文“高武”,背面刻有銘文“櫟陽”。“高武”即“高奴”,故地在今陜北延安一代,戰(zhàn)國時屬秦國轄地,“櫟陽”系戰(zhàn)國時期秦獻公遷移的都城所在,所以這是一件秦人所用的戈;1978年隨州擂鼓墩1號墓出土的曾侯乙戈(圖23),制作精良,上鑄有銘文:“曾侯乙之用戈。”說明這件兵器是曾侯乙親自所用。
矛,刺兵器。2006年扶風上宋鄉(xiāng)五郡西村出土一組帶銎銅矛(圖24),年代在西周早期,中脊很高,矛體修長,鋒利無比,反映出西周時期武備的發(fā)達。
戟,勾刺合用兵器。1972年甘肅靈臺白草坡2號墓出土一件青銅戟(圖25),年代在西周早期,說明中國兵器中用戟的時代之早。

圖19 戰(zhàn)國 戰(zhàn)車戰(zhàn)馬

圖20 商晚期 人面紋銅鉞

圖21 人頭銎鉞

圖22 戰(zhàn)國 櫟陽戈

圖23 戰(zhàn)國 曾侯乙戈

圖24 西周早期 帶銎銅矛

圖25 西周早期 青銅戟

圖26 戰(zhàn)國 建鼓座

圖27 西周 編镈
《無衣》大意為:誰說我們沒衣穿?與你同穿那長袍。君王發(fā)兵去交戰(zhàn),修整我那戈與矛,殺敵與你同目標。誰說我們沒衣穿?與你同穿那內衣。君王發(fā)兵去交戰(zhàn),修整我那矛與戟,出發(fā)與你在一起。這是秦人的一首戰(zhàn)前誓詞,展現了秦人在大敵當前同仇敵愾、慷慨激昂,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

圖28 戰(zhàn)國 曾侯乙編鐘

圖29 西周 銅鈴

圖30 秦 盾牌

圖31 秦 青銅箭頭
三、吉金之朝覲、宴饗篇
《詩經·靈臺》:于論鼓鐘,于樂辟雍。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鼓,這里的鼓不似前面的軍旅用鼓,宴饗用鼓主要用于奏樂助興,如建鼓一類,當是放在支架上敲擊的一類鼓,曾侯乙墓出土有建鼓座(圖26),惜鼓面已經殘失。鐘,樂器。先秦禮器中常和磬組合伴奏,1985年陜西眉縣楊家村窖藏出土一套編镈(大型打擊樂器,圖27),造型優(yōu)美,紋飾精致。湖北隨州擂鼓墩1號墓出土的曾侯乙編鐘(圖28)是迄今所見規(guī)模最大的完整的編鐘,它既考慮了鐘與鐘虡之間的物理性能,又充分照顧到觀者的審美觀瞻的需要,對于橫梁、立柱、色彩組合等方面的搭配都有周密的設計,更以銅人,獸形圓柱,透雕花瓣等裝飾與編鐘相配合,構成了復雜多變而又恢弘博大的氣勢,先秦貴族生活質量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這是描寫君主在辟雍燕閑游樂場景的詩章:燕閑中鐘鼓齊鳴,樂聲大作,翩翩起舞,氣氛甚是歡快。
《詩經·載見》: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鸧,休有烈光。
鈴,馬飾,系于馬項。1976年陜西扶風縣莊白1號窖藏出土有7件銅鈴(圖29),表面飾變形獸面紋,應當就是使用于裝飾馬匹的裝飾物。
《載見》的大意是:諸侯開始朝周王,請賜法度和典章。龍旗圖案鮮又亮,駿馬和鈴叮當響。金飾韁繩耀眼光,整個隊伍雄又壯。
這是描寫參加助祭武王的諸侯覲見成王時候的恢弘場景,熱烈隆重的氣氛,浩大磅礴的氣勢,有聲有色,八方匯集,表現出對周王室權威的無限臣服與敬意。

圖32 西周 古父己卣

圖33 西周 伯格卣

圖34 商晚期 亞疑簋及銘文拓片

圖35 西周早期 方座簋

圖36 西周簋
四、吉金之頌功篇
《詩經·時邁》: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橐弓矢。
干,盾牌。西周的青銅盾牌發(fā)現很少,但是在陜西臨潼秦始皇帝陵出土有秦代的彩繪盾牌(圖30),裝飾流云紋,異常精美。矢,箭。秦始皇帝陵陪葬坑就曾發(fā)掘出土成束的青銅箭頭(圖31),箭鋌部位有絲線纏繞痕跡,和箭桿連接在一起,裝于箭箙,箭桿、箭箙皆已朽壞,僅存殘跡。
這是歌頌武王德政的詩篇,敘述武王繼承文王大業(yè),偃武修文,“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墟”,開創(chuàng)一個太平新世界。
五、吉金之賞賜篇
《詩經·江漢》:厘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
卣,是一種用來裝盛用黑黍、香草釀造的酒的高級酒器,考古多見。由于卣是一種高等級的酒器,所以大多數的卣都有著華美的外觀與獨特的造型,如上海博物館藏的古父己卣,腹部有一對浮雕的牛角,造型十分別致(圖32);1980年寶雞竹園溝西周墓葬出土的伯格卣,造型之美,紋飾之精,在整個商周青銅器群中都是十分罕見的(圖33)。
此為記述周王賞賜召伯虎平淮夷之功所作的詩篇,周王賞賜給召伯虎玉圭瓚、香酒、土田等等,希望他能夠勤于王事,多為國家出力。
六、吉金之述憤篇
《詩經·大東》: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言顧之,潸焉出涕。
簋,盛食器。上海博物館收藏有一件商代晚期的亞疑簋(圖34),金光燦燦,綠銹瑩瑩,通體飾方格乳釘紋,保存非常完好,體現了商代晚期青銅鑄造藝術的高超水平;1981年寶雞紙坊頭1號墓出土了一件方座簋(圖35),在方座的四角上部各有一對牛角紋,和方座正面的獸面紋相互配套組合,乍看上去,就好像給獸面增添了一對雙角,更有虎虎生威的感覺,是西周早期國的禮器;1976年扶風莊白1號窖藏出土了8件簋(圖36),造型紋飾一模一樣,成組成套,是西周列鼎列簋制度的現實體現。

圖37 西周匕及銘文拓片


圖38 戰(zhàn)國 蟠螭紋方座簋

圖39 西周 牛紋罍

圖40 商晚期 皿天全方罍
匕,挹取器,類似現在的勺子。1976年扶風莊白1號窖藏出土的匕品相完好,造型精致,上面有銘文“微伯作匕”(圖37)。是匕類器中的精品。
2002年湖北九連墩2號楚墓出土的蟠螭紋方座簋(圖38),出土時就有一件匕放在里面,正好證實了《詩經》中簋、匕配合使用的文獻記載,是證經補史的好資料,具有十分重大的歷史價值。
《大東》的大意是:簋里熟食滿蕩蕩,棗木勺兒彎又長。大路平坦如磨石,筆直好像箭桿樣。貴人路上常來往,小民只能瞪眼望。轉過頭來心悲傷,眼淚汪汪濕衣裳。反映出被征服地區(qū)百姓的凄慘生活。
《詩經·蓼莪》:瓶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
罍,大容量的盛酒器,有時候也可以用作水器。罍起源于商代晚期的安陽殷墟地區(qū),西周中期以后趨于消亡,西周晚期為它的派生物所取代。四川彭縣竹瓦街窖藏出土的牛紋罍(圖39),鑄造工藝十分高超,體表裝飾側牛紋,代表了四川地區(qū)青銅藝術的獨特水平。該器通高達79厘米,是目前所見最大的青銅圓罍,堪稱“商周青銅圓罍之王”,在商周青銅酒器中占有重要地位;1919年湖南桃源縣出土的皿天全方罍(圖40),通高達88厘米,做工精良、紋飾華麗,銘文書體遒勁有力,其宏大的氣魄與高貴的氣質在先秦罍類器中罕有其匹,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價值,堪稱商周“方罍之王”。這件罍在出土不久就器蓋分離,蓋幾經輾轉后為湖南博物館所收藏。器身在與蓋分離后歷遭磨難,一度流失于海外若干收藏家之手。2014年3月19日,湖南省博物館在社會各界的傾力協(xié)助下,將流失海外幾近一個世紀的皿方罍器身迎回國內,安厝于湖南省博物館,至此終于實現了永久的器蓋合一。
《蓼莪》的大意為:汲水瓶兒空了底,裝水壇子真羞恥,孤獨活著沒意思,不如早點就去死。此詩以瓶子比喻勞動人民,以罍比喻統(tǒng)治者,意思是說老百姓都已經窮成這樣了,統(tǒng)治者不應該感覺到羞恥嗎。老百姓已經民不聊生了,還不如死了的好。
《詩經》的內容豐富多彩,包羅萬象,體現出的人文精神源遠流長。《詩經》宛如群星璀璨的星空,青銅器就是其中十分耀眼的一顆,值得我們仔細的去鉆研、探索。
(責任編輯:牧風)
Jijincangshili jingshenyunshanyue
Wang 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