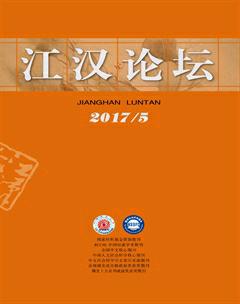可持續生計與農民工城市化決策



摘要:伴隨著農民工進入城市時間的逐漸延長,農民工年齡日益增長,尤其是第一代農民工逐漸進入退休階段,這一批農民工是留在城市還是回到農村成為這一批農民工的選擇難題。本文在可持續生計框架下,從制度經濟學和資產組合理論出發,用效用最大化原理分析農民工城市化決策的機制,并基于調研數據用二元logistic實證分析五類農民工資產對農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響。理論分析表明,戶籍制度及土地產權制度均既降低了農民工達到城市化必需資產積累的可能性,又減弱了農民工城市化的意愿,實證結果顯示五類生計資產(城市型、農村型)對農民工(第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化意愿影響程度均呈現出顯著的差異。政府要通過改革和完善戶籍制度、土地產權制度、農民工社會保險制度和形式多樣的社會培訓制度來促進農民工城市化,提高農民工的幸福獲得感。
關鍵詞: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決策;可持續生計
中圖分類號:F3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7)05-0025-06
一、引言與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
農民工是從農村進入城市的精英,也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同時還是城市建設的主力軍。隨著農民工進入城市時間的逐漸延長,農民工越來越熟悉城市的生活,相反,對農村的生活越來越陌生。農民工進入城市時間的逐漸延長,農民工年齡日益增長,尤其是第一代農民工逐漸進入退休階段,這一批農民工是留在城市還是回到農村成為這一批農民工的選擇難題。解決好農民問題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而農民工問題又是農民問題的重點,目前農民工面臨的迫切問題就是農民工城市化問題。因此,研究農民工是否愿意城市化以及如何城市化成為政府和學術界越來越關注的熱點問題。
從現有文獻的研究來看,大多數關于農民工遷移的研究都是從社會學、人口學視角進行分析,從經濟學視角進行分析的研究比較少,這可能與數據比較難取得相關。從僅有的少數經濟學研究文獻來看,也主要是在傳統的西方勞動力遷移理論的基礎上稍做擴展,然后利用統計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并沒有對影響勞動力遷移的深層次原因進行理論探討。鑒于上述局限性,本文在可持續生計框架下,從制度經濟學和資產組合理論出發,用效用最大化原理分析農民工城市化決策的機制,并基于調研數據用二元logistic實證分析五類農民工資產對農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響。
可持續生計框架是伴隨著對生計概念的完善而發展起來的。生計(livelihood)本來是一個相對寬泛的概念,主要指經濟主體的生活狀態、謀生方式或者為求得生存而產生的計策,直到Chambers and Conway(1992)提出可持續生計(sustainable livelihoods)的概念,他們認為可持續生計包含了各種能力、資產和活動,這些都是可持續生計的手段,并且經濟主體可以憑借這些能力、資產、活動提高生計水平①。隨著可持續生計概念的不斷發展,關于可持續生計的理論也不斷完善,其中DFID(1999)發展的可持續框架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它既包括可持續生計,又包括制度②。本文根據農民工生計特點,結合李樹茁等③ (2010)、靳小怡等 ④ (2011)的相關研究,將農民工城市化問題納入DFID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中,如圖1所示。
在改進后的框架中,為研究農民工行為的代際差異,我們將農民工分為第一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兩個群體。同時將每個農民工家庭所持有的五類生計資產又進一步細分為農村型和城市型,以分析農民工城市化的意愿和路徑。每個農民工家庭在戶籍制度和土地產權制度等約束下做出短期生計資產配置的策略,以及在遠期是否進行城市化的抉擇。
在圖1呈現的框架下,我們可以對生計資產配置約束下農民工的城市化決策展開分析。從短期來看,資產配置的核心在于如何使資產增值,即在控制風險的情況下使收益最大化,或者在控制收益的情況下使風險最小化。而從長期來看,資產配置的核心在于如何分配消費與儲蓄以實現終身效用最大化,即通過資產配置實現消費的平滑。農民工生計資產的短期和長期風險收益特征總結如表1所示。
基于表1中列示的各類生計資產的不同風險收益特征,從短期資產配置來看,對于全部勞動都在外務工的家庭,可以放棄對自然資產和農村型物資資產的配置,而應該集中在城市型社會資產和城市型金融資產的配置上,通過城市型社會資產的配置,并通過城市型社會資產轉換為金融資產,實現金融資產的快速積累;對于部分勞動力在外務工的家庭,從短期來看,應該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形成城市勞動力,同時,應該提高城市型社會資產的配置,利用城市型社會資產實現替換工作或者就業的目的,從而將社會資產轉換為金融資產。
從長期來看,農民工面臨城市化與不城市化之間的抉擇,這取決于農民工對城市生活和農村生活的偏好。如果農民工偏好于城市生活,則可以選擇城市化,并通過市場定價方式把自然資產和農村型物資資產流轉給其他農民,把自然資產和農村型物資資產轉換為金融資產,再把金融資產配置到人力資產和城市住房當中;相反,如果農民工偏好于農村生活,則可以持有自然資產和農村型物資資產,放棄城市型金融資產并將存款內金融資產轉換為農村型金融資產,加大對人力資產的配置,以實現人力資產與自然資產的結合從而轉換為金融資產。
二、基于效用最大化的理論模型建構
其中,c表示農民工購買城市住房的成本,方程左邊表示農民工的資產積累,右邊表示農民工城市化至少的資產積累,當方程成立時,說明農民工的資產積累足夠支撐農民工城市化。
從方程(9)可知,制度(1)是影響農民工財富積累重要的影響因素,我們從戶籍制度和土地產權制度兩個層面來分析制度如何影響農民工財富積累。
對于戶籍制度而言,農民工進入城市務工,由于戶籍制度的原因被限制在正規勞動力市場之外,其勞動力并未得到有效利用,勞動力要素價格也被市場扭曲,因此降低了農民工生計資產的積累。對于土地產權制度而言,擁有農民身份的農民工,自然資產是其相對于城市居民的主要特殊資產,但由于土地產權制度的不明確,使得農民工無法有效利用自然資產,更無法獲得自然資產的全部收益,這使得農民工生計資產的積累速度被大大減緩。
總之,戶籍制度和土地產權制度都降低了農民工的收入水平,從而導致方程成立的可能性下降,因而降低了農民工實現城市化的必要條件。從效用的角度,根據方程(3)—(4)可知,制度約束由于降低了收入水平,從而減少了農民工對城市組合商品的需求,而農民工對農村組合商品的需求并沒有發生變化。因此,方程(8)中“城市化”決策成立的可能性降低,即現存制度約束降低了農民工城市化的意愿。
三、數據來源、變量選取與實證分析
從理論上分析了農民工在生計資產和現行制度約束下的城市化選擇行為后,我們將利用建筑業農民工的調查數據,進一步分析五種生計資產稟賦對農民工城市化決策的影響程度。由于農民工選不選擇城市化的決策為定性響應變量,本文因此采用logit的估計方法,實證方程設定為:
其中,Pi=1表示農民工選擇城市化,Pi=0表示農民工不選擇城市化。核心解釋變量x為自然資產、物資資產、金融資產、人力資產和社會資產等五種生計資產,控制變量z為其他因素。
1. 數據來源與相關概念界定
本文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獲取所需的數據⑦,樣本選自**集團公司下屬建筑企業在北京、武漢、西安三市的建筑工人,總共發放問卷2000份,其中200份預調查問卷,1800份正式調查問卷,最后回收1800份問卷,通過檢查、剔除遺漏、邏輯混亂的問卷后,共計收集到有效問卷1386份,為了提高有效問卷的有效性,在無效問卷中對留下聯系方式的問卷進行回訪,從而又得到有效問卷123份,合計有效問卷1509份。
此外,本文對“城市化意愿”和“新生代農民工”進行定義。本文使用“是否希望成為xx市民”作為衡量農民工城市化意愿的代理指標,使用農民工是否已經在城市購買房產判斷農民工是否已經實現城市化。本文定義的新生代農民工是1980年及1980年以后出生的農民工為新生代農民工。
2. 變量
基于本文的分析框架,根據調查的實際情況⑧,我們的主要變量設計如表2所示。在控制變量的選擇上,本文參考侯紅婭⑨(2004)、黃乾⑩(2008)等研究文獻,將性別、婚姻狀況和農民工在城市居留時間作為控制變量。因此,本文在控制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和農民工在城市居留時間的情況下,研究自然資產、物資資產、金融資產、人力資產和社會資產對農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響。
3. 實證結果
表3報告了五類生計資產對農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回歸結果。從前文可知,每一類生計資產可細分為農村型生計資產和城市型生計資產,而農村型生計資產和城市型生計資產對農民工城市意愿的影響存在較明顯的差異。因此,我們除在表3的第1、3、5列中報告了五類生計資產總量的影響外,在表3的第2、4、6列,還將分析細分生計資產(農村型和城市型)對農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響。同時,由于第一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擁有的資產組合存在明顯的差異,有必要單獨分析生計資產對第一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響。因此,在表3的第1-2列、3-4列、5-6列,我們分別報告了生計資產對農民工總體、第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的影響。
從回歸結果和分析可知,總體而言,自然資產對農民城市化意愿影響為負;農村型物資資產對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為正,城市型物資資產對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為正,物資資產對農民工城市化意愿綜合影響為正;農村型金融資產對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為負,城市型金融資產對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為正,金融資產對農民工城市化意愿綜合影響為正;農村型人力資產對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為負,城市型人力資產對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為正,人力資產對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的綜合效應為負;農村型社會資產對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為負,城市型社會資產對農民工城市意愿影響為正,社會資產對農民工城市化意愿綜合影響不顯著。
對于第一代農民工而言,自然資產對第一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顯著為負;農村型物資資產對第一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顯著為正,城市型物資資產對第一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顯著為正,物資資產對第一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綜合影響為正;農村型金融資產對第一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不顯著,城市型金融資產對第一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顯著為正,金融資產對第一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綜合影響顯著為正;農村型人力資產對第一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顯著為負,城市型人力資產對第一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顯著為正,人力資產對第一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綜合影響顯著為負;農村型社會資產對第一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顯著為負,城市型社會資產對第一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顯著為正,社會資產對第一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綜合影響并不顯著。
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自然資產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不顯著;農村型物資資產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顯著為正,城市型物資資產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不顯著,物資資產對新生代農民工綜合影響顯著為正;農村型金融資產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不顯著,城市型金融資產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顯著為正,金融資產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綜合影響顯著為正;農村型人力資產和城市型人力資產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均不顯著,人力資產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綜合影響也不顯著;農村型社會資產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不顯著,城市型社會資產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影響顯著為正,社會資產對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綜合影響顯著為正。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在可持續生計框架下,從制度經濟學和資產組合理論出發,用效用最大化原理分析農民工城市化決策的機制,并基于調研數據用二元logistic實證分析五類農民工資產對農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響。
理論分析表明,由戶籍制度造成的勞動力市場分割,以及土地產權制度的歸屬不明所帶來的交易成本都降低了農民工生計資產的積累。上述制度約束既降低了農民工達到城市化必需資產積累的可能性,又減弱了農民工城市化的意愿。實證結果表明,自然資產、物資資產、金融資產、人力資產以及社會資產對農民工總體的城市化意愿影響程度各異;將每一類資產進一步細分為農村型和城市型再回歸分析,得到農村型、城市型生計資產對農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響呈現出明顯的差異;五類生計資產總量、農村型和城市型生計資產對第一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城市化意愿的影響同樣呈現出顯著差異。
基于本文的研究結論,我們認為政府要通過采取如下措施來促進農民工城市化:
第一,改革和完善戶籍制度。有效的制度可以提升效率,而無效的制度只會提高交易成本,降低社會效率,改革和完善戶籍制度才能打破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給予農民工更公平的就業機會,促進農民工人力資產向金融資產的轉換。
第二,改革和完善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和完善土地產權制度,農民工通過改變土地使用方式而實現土地收益最大化,提高農民工資產的積累速度,提高農民工自然資產向金融資產的轉換。
第三,改革和完善農民工社會保險制度。社會保險是農民工金融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金融資產對于促進農民工城市化具有顯著的作用,因此,改革和完善社會保險制度可以提高農民工持有的金融資產的數量,從而提高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并使農民工城市化時間提前。
第四,建立完善的社會培訓體制。雖然新生代農民工人力資產水平有所提升,但農民工整體人力資產水平較低,綜合素質較差。政府要審時度勢,構建多元培育機制,積極履行對社會組織的支持培育職能。對于教育培訓、養老服務、留守兒童關愛服務、社區環衛、社區醫療衛生等專業性、技術性較強的公共服務,由政府通過公開招標,擇優選擇各類專業化服務機構,與之簽訂購買服務合同,由專業化服務機構直接提供服務{11}。通過完善社會培訓體制,提高農民工人力資產水平并實現人力資產向金融資產的轉換,則可以提高農民工資產的積累速度,從而提高農民工城市化意愿和城市化速度。
注釋:
① R. Chambers and G. R. Conway,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 IDS Discussion Paper 296,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2.
②The Department for L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1999.
③ 李樹茁等:《退耕還林政策對農戶生計的影響研究——基于家庭結構視角的可持續生計分析》,《公共管理學報》2010年第7期。
④ 靳小怡等:《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應用的新領域:農民工生計研究》,《當代經濟科學》2011年第3期。
⑤ 該組合產品指日常生活用品,包括衣、食、行等產品,不包括對住房的消費。
⑥ 為使模型更簡潔,把農村組合商品價格設定為1。
⑦ 限于篇幅,文中不列示“農民工生活及務工情況調查問卷”。
⑧ 由于通過調查所獲得的數據具有不同的量綱、數量級和變化幅度,本文沿用楊云彥和趙峰(2009)的做法,使用極差標準化的辦法進行處理,即:Zi=。
⑨ 侯紅婭、楊晶、李子奈:《中國農村勞動力遷移意愿實證分析》,《經濟問題》2004年第7期。
⑩ 黃乾:《農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影響因素——基于五城市調查的實證分析》,《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
{11} 王亞南:《新型農村社區公共服務供給中的縣級政府職能研究——基于Z市“多村一社區”的調查分析》,《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
作者簡介:程先勇,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漢,430072。
(責任編輯 陳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