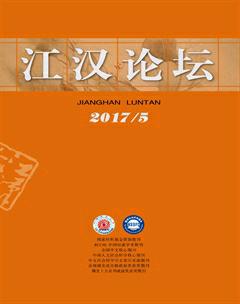闡釋的邊界:文本闡釋的有效性問題探析
張良叢+唐東霞
摘要:“強制闡釋論”提出文本闡釋的邊界問題,指出了體現作者意圖的文本闡釋有效性是唯一的標準,體現出對“反意圖論” 的回應。這種觀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把文本意義的闡釋完全局限于作者意圖,就排除了其他有效性的闡釋意義。對文本意義的闡釋,應該對意義的存在方式和闡釋中心的流變作縱向考察,注意到開放文本觀和闡釋學的主客觀統一的語境,綜合考量文學闡釋各種有效性因素,才更為合理。以文本為闡釋的邊界,但并不封閉文本和闡釋活動,我們主張一切在文本中找到依據的闡釋都是有效的。
關鍵詞:強制闡釋論;闡釋的邊界;闡釋的有效性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當代美學的基本問題及批評形態研究”(15ZDB023)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7)05-0061-06
張江指出:“強制闡釋是指,背離文本話語,消解文學指征,以前在立場和模式,對文本和文學作符合論者主觀意圖和結論的闡釋。”① 強制闡釋論在文本意義闡釋方面指出了當代文學批評存在的基本問題,可謂一針見血,針砭時弊。當代文學批評的確存在著強制闡釋,而且呈現的狀態很嚴重。理論先行,把文學文本當作理論驗證的材料,在文學批評中常見。對此,張江提出了文學批評的倫理問題,強調了批評家的道德律令。但是,張江隨后指出,“對文本闡釋的公正性要求,是包含正確地指出文本的本來含義,或者由作者所表述的文本的本來含義”②。在張江的表述中,文本闡釋的依據局限于作者以及由作者意圖制約的文本。從文本學和闡釋學來看,這種對于文本意義的觀點是可商榷的。本文結合文本觀念的變遷和闡釋中心的轉移,進一步探討文本意義的來源,從而探討闡釋的邊界、闡釋的有效性問題。
一、文學意義的存在方式
文本闡釋首先就要求證意義存在于何處。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同時代的文本理論有不同的答案,圍繞著作品、文本、讀者發生了多次中心轉移。意義存在的中心轉移顯示出研究者對于文學意義理解的變化,也反映了其背后文學觀念的變化。從文本觀念變化看,文本逐漸走向一種開放的觀念,對意義的理解也呈現出多元模式。
作品觀是古典文論理解意義存在方式的文本觀。“古典文藝理論稱文藝作品為作品,強調的是作品與作者的關系。”③ 作品的概念背后是古典文藝理論作為支撐的。作者被認為是文學活動的核心,形成作者中心論的闡釋方式。作品是體現作家原意的語言編織物。作品的意義來源于作者,作者決定作品的意義。作品把闡釋的目標指向作者,閱讀、闡釋的重點在于作者。作者是文本意義的根據,而作品不過是意義的載體。與之相關,作者成為文學意義的根源,而作品似乎無關緊要的了;作品觀使得研究作者取代了對作品的解析。古典文論的一些闡釋方式體現出這種作者中心論的觀念。如社會歷史批評著重考察社會歷史通過作家在作品中的體現,作家的個人經歷、社會背景成為主要的闡釋重點,作品成為佐證。浪漫主義批評闡釋作家的才性、情感、想象等主體因素在文學活動中的作用,作品也是作家的這些品格的證明。在20世紀初期作者中心論受到批判,文本中心論就是以此為靶子而建構起來的。
20世紀初期建構的文本觀是語言學轉向的產物。現代語言哲學認為世界是意義構造物,而意義則是由語言編織的,語言就是世界本體。與之相適應,在文學文本中,語言不再是表達意義的工具,語言本身就是文學的本體。這樣,文學文本就沒有必要再去作者、世界那里尋找意義,自身就是意義所在。文本中心論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本獨立于社會歷史之外,是封閉的、自足的語言系統。這種觀念始于俄國形式主義,發展于新批評,在結構主義那里達到了高峰。俄國形式主義首啟文本中心觀。它面對的靶子首先是19世紀末以來占據文壇的社會歷史批評、傳記批評等作者中心論的闡釋模式。俄國形式主義要摒棄文學之外的因素的干擾,追求藝術的自主性。雖然俄國形式主義并沒有明確使用文本概念,但是他們將作品與作家、社會分離,確立了作品的核心位置,已經是現代文論形態的文本概念。新批評是較早使用文本概念的現代文論流派。新批評追求的也是文學的自律性。它所面臨的首要任務便是擺脫作者的限制。新批評的先驅艾略特指出:“詩歌不是個性的表現,而是個性的偏離。”④ 對個性的驅逐,就是剔除作者的作用,不再把文本當成作者內在因素的表達,也就是避免了批判的“意圖謬見”。同時,新批評還批判了讀者“感受謬見”對意義形成的誤導。每一個文本都是一個意義自足體,作者意圖和讀者感受不能成為衡量文學價值的標準。文本是文學意義的核心,一切盡在文本中。在法國結構主義這里,文本觀念更加深入一步,意義的根據在于深層的結構系統。“結構詩學的對象不是文學作品本身:它是研究文學本身,即一種特殊類型的話語特性。因此,任何一部作品都只被看作是某一個比它抽象得多的結構的實現,而且是它的多種可能的實現方式之一。”⑤ 在這里,我們看到作家不再是文學意義的創造者和賦予者,一切都是深層結構決定的。具體文本只不過是言說了結構的某種可能性。文本最根本的所在不是表層的言說,而是深層的、穩定的結構。這種自足的文本觀面對闡釋者封閉了自身,將其根據完全放在了文本自身,文本成為闡釋的中心,摒棄了作者和讀者在文本闡釋中的重要作用,也把文本與世界分離開來。
其后,后結構主義開始反思結構主義的文本中心論,文本內部的差異性更為重要。“我們應該從每個故事中,抽出他的特有的模型,然后經由眾模型,引出一個包納萬有的大敘事結構,再反過來,把這大結構施用于隨便那個敘事。這是苦差事,竭精殫思,終究生了病厭,因為文本由此而失掉了它自身內部的差異。”⑥ 文本是一種由多層意義交互起來的一個系統,文本的闡釋不是尋找一個穩定的、不變的核心,不過是意義的展開。文本中心觀需要突破,這就需要新的因素介入。后結構主義理論是重新引進文學活動的主體——讀者來完成的。讀者作為文學活動的第二主體,他的差異性閱讀構成了差異性文本的來源。在《S\Z》中,羅蘭·巴特把文本分為可寫的文本和可讀的文本。其中,可寫的文本指的是,讀者可以自由發揮,參與意義構造的文本。羅蘭·巴特推崇“可寫的文本”,因為在這種文本中,讀者成為文本意義的創造者,由于個體的差異性,必然會創造出不同個性的文本,從而獲得創造性的愉悅。在《文之悅》中,羅蘭·巴特又進一步把文本分為“快樂文本”和“極樂文本”,強調的都是文本的讀者參與性,讀者的創造性的、拆解文本而來的愉悅。在后結構主義文本觀中,由于讀者的引入,文本已經突破了封閉性、自足性的結構,成為一種開放性的存在。文本的意義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讀者的閱讀發生差異性。耶魯學派的解構主義則在文學意義闡釋上進一步解構文本中心觀。布魯姆則提出誤讀理論,肯定了文本意義的讀者闡釋。閱讀是個體讀者的一種延異行為,包含著個體的因素,不可能還原作者原意。而且誤讀本身是一種創造性的行為,前人對后人的影響,就是通過后人的誤讀、修改來實現的。影響即誤讀。這種讀者意義上的多種可能性,使文本已經走向了一種自我的解構,逐步走向了讀者決定論。
文本意義的決定權交給讀者并不是突然興起的,也不是理論的自我言說,而是與真實的文學藝術活動變革有著直接聯系。意大利批評家艾柯指出,當代文學藝術出現了這種傾向:西方當代藝術家在創作中,故意給接受者留下發揮的余地。音樂作品中,作曲家不是以確定的、封閉的形式來組織作品,而是一種多種可能性的組織方式,從而給演奏者留下了發揮的余地。演奏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感受理解作曲者的說明,進行真正的干預,自己決定一些音符持續時間的長短。在繪畫中也是如此,如考爾德的《活動的裝置》,布魯諾·程納里的《可活動的繪畫》都是接受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和外在的環境形成作品的呈現樣態。在文學作品中,象征主義詩人馬拉美通過《書》這本傾其一生都沒有完成的作品給詩歌確立一種明確的準則,“一本書既沒有開頭,也沒有結尾:最多它只是裝做這樣。”⑦ 讀者可以自己隨意排列,形成不同的詩歌。在這樣的文本實踐中,讀者闡釋的主體性具有合法性。重視讀者在文學活動中的權力,這個傾向在20世紀的文學理論中逐漸得到了響應。在現象學、接受美學等理論流派中,文本的基本構成部分就是讀者。現象學美學家英加登提出,文本是一個意向性的客體,本身具有很多空白點,留待讀者的填充。接受美學更進一步肯定了讀者的權力,文本是一個召喚結構,讀者的創造性閱讀是作品形成的最后環節。
總之,在文本理論歷史中,文本意義的存在從作者、文本到讀者發生了多次轉變。文本逐漸走向了開放性。尤其是互文本觀念更是放大了文本的開放性。“互文本正意味著語言學模式的文本與歷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經濟的文本的相互關聯”⑧,互文就使得文本之間、文本與社會文化之間的多重關系得到了肯定,打破了封閉的、確定的意義,作者、讀者、文本構成了一個對話的狀態。文本之外因素的關注,文本與社會、歷史文化的重新鏈接,構成了一種新的文本。在文本觀的理論走向中,文本觀念是逐漸走向開放,包容性越來越大。由此,在這種理論觀念的視域中,對文本的理解不能完全局限于某種因素,不能自我封閉,應該秉承開放的文本觀念。但是,開放性文本觀并不意味著否定其他因素在文本意義建構中的作用,而應將其放在一個文本因素的系統中。
二、闡釋中心的轉變
文學意義的存在方式發生了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讀者中心三種轉向,那么闡釋理論在20世紀發生了怎樣的轉變?與文本觀的類型一致,闡釋學理論的發展也經歷了這三種中心的轉移。艾柯在《詮釋與過度詮釋》中提出闡釋活動有三種意圖:作者意圖、闡釋者意圖和文本意圖。這恰恰是闡釋學自身發展所尋找的三種闡釋中心,也是闡釋學自身形成的三種模式。
一種模式是作者意圖的闡釋學。這種闡釋學認為,文本既然是作者寫作的,文本的意義必然是作者賦予的。闡釋的目的自然就是發現和重新還原作者意圖。古典闡釋學雖然形態各異,但是其堅持作者中心論傾向是一致的。闡釋一詞的本來含義,就是希臘諸神的信使赫爾墨斯對神的意志的闡釋。其后興起的圣經注釋學,目的是通過文本語義和考古學分析,使讀者理解其中隱含的上帝旨意。當然這些形態還是早期的闡釋學,本身離現在的闡釋學有一定的距離,但是其主旨是一致的。古典闡釋學家施萊爾馬赫的普遍闡釋學認為,“解釋的重要前提是,我們必須自覺地脫離自己的意識而進入作者意識”⑨。只有脫離闡釋者自己的意識,才能進入作者意識,從而理解和闡釋的文本意義才具有合法性。威爾海姆·狄爾泰認為:“對陌生的生命表現和他人的理解建立在對自己的體驗和理解之上,建立在此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⑩ 狄爾泰在施萊爾馬赫的闡釋傳統基礎上進一步論證了讀者闡釋能夠還原作者原意的哲學基礎,在于作者和讀者的生命共同性。正是在生命共同性的基礎上,讀者通過生命體驗就可以還原作者賦予給文本的意義。美國當代闡釋學家赫什就提出闡釋的基本對象就是作者意圖,有效的闡釋就是理解了作者意圖,除此之外都是錯誤的。作者意圖被看作鑒別闡釋意義正誤的標準。當然,赫什這些觀點的提出,目的是對抗“反意圖”論者,有一種極端傾向。作者意圖的闡釋學把闡釋當作一種接近、還原作者原意的方法,作者意圖是文本意義的根據。只有尋找到了作者意圖,闡釋活動就成功了。在作者意圖的闡釋學中,并沒有把闡釋者自身作為獨立的個體性的存在,去考慮他的因素對闡釋活動的影響,忽視了他在闡釋過程中的作用,給后來的闡釋理論發展留下了建構的空間。
以闡釋者意圖為核心的闡釋學也是一種模式。這種模式來源于海德格爾。海德格爾的闡釋學是一種本體闡釋學。闡釋學在他那里,“不再是一種神學的,或哲學的、注釋學的方法,甚至不是精神科學的方法,而是一種對存在的、具體的、特殊情景的、歷史的、語言的和動態的此在的昭示性理解,一種關于在顯現中、顯現出來的事物的初始觀念的現象學”{11}。闡釋活動不是一種方法,而是一種對此在的顯現。這里已經隱含了闡釋者意圖的轉向。其后闡釋者意圖的凸顯在伽達默爾的闡釋學那里完成了。“本文的意義超越它的作者,這并不是暫時的,而是永遠如此的。因此,理解不只是一種復制行為,而始終是一種創造性的行為。”{12} 伽達默爾強調了文本意義超越作者,是一種創造性行為。這個創造性行為就是讀者的行為。可以說,伽達默爾的哲學闡釋學進一步發展了讀者中心論,并使之系統化。他提出闡釋活動是一種創造性的活動,讀者的“偏見”在闡釋中具有合法性。闡釋不過是作者視野和讀者視野兩種視野不斷融合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文本意義得到創造。作者不再是文本闡釋的唯一根據,闡釋活動會永遠超越作者意圖,顯示出對闡釋者意圖的重視。其后,受現象學、闡釋學影響的接受美學把這個問題發展到了極端,為后來的闡釋理論所批判。
“在最近幾十年文學研究發展進程中,詮釋者的權利被強調的有點過火了。對于文學作品的開放性閱讀必須從作品文本出發,因此,它會受到文本的制約。”{13} 對于文本闡釋過于強調闡釋者意圖的傾向,當代闡釋學家認識到它的弊端。艾柯的闡釋理論批判了過度闡釋的傾向。他雖然要求文本是開放的,但是其闡釋必須受到文本制約,體現出文本意圖的回歸。法國闡釋學家利科爾也認為,以前的闡釋學在作者和讀者之間的關系上,往往偏執一端,出現偏頗。文本是溝通作者和讀者的橋梁,闡釋學應該把文本視為闡釋的中心。利科爾指出,在作者和文本之間有一種闡釋學的距離,文本意義并不是作者賦予的。闡釋的目的不是揭示文本背后的意圖,“而是展示文本面前的世界,那么真正的自我理解正如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想說的,乃是某種可以由‘文本的內容所找尋的東西。與文本世界的關系取代了作者的主觀性關系,同時讀者的主觀性問題也被取代了”{14}。文本意圖是利科爾闡釋學的核心,闡釋的目的就是要達到文本世界的彰顯。當然,艾柯和利科爾雖然重視文本意圖,強調文本自身的客觀性對于闡釋活動的制約,但是并沒有完全忽視闡釋者本身的作用,只是沒有過于強調。
那么,如何理解三種闡釋意圖?我們可以從主觀和客觀方面加以區分。作者意圖和讀者意圖是主觀的,而文本意圖則是客觀的。從闡釋學的歷史到當代,圍繞著意義來源于主觀還是客觀一直在爭論,并沒有形成共識。因為“作者意圖非常難以發現,且常常與文本的闡釋無關”{15},在當代闡釋理論中,作者意圖很少被重視,闡釋活動的主客觀成分剩下的主要是讀者意圖和文本意圖。艾柯就指出當代闡釋論過于突出讀者個性色彩,易形成“過度詮釋”。他重點批評了過度闡釋的問題,指出過度闡釋否定了文本原意的存在,闡釋過程具有很大的隨意性。這是一種“妄想狂式的詮釋”,應該加以防范。那么,如何理解文學活動中的讀者與文本意圖的關系。艾柯的理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他將文學活動中的兩個主體——作者和讀者區分為標準作者、標準讀者和經驗作者、經驗讀者。“文本意圖并不能從文本表面直接看出來。 ……文本的意圖只是讀者在自己的位置上推測出來的。”{16} 文本意圖需要標準讀者來探究,從而窮盡文本所有的可能性。標準作者則是標準讀者勾勒出來了,亦即能夠創造出所有文本意義的作者。顯然,這里的標準讀者與接受美學的“隱含的讀者”不同,“隱含的讀者”是作者意圖的體現者。而標準讀者則是一個幾乎等同于文本意義的完整體,再現的是全部的文本意圖。當然,標準讀者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是理想化的。而經驗讀者和經驗作者則是閱讀活動中實際存在的。在闡釋活動中,經驗讀者是文本意義闡釋的主體,經驗讀者的最完美的體現是標準讀者。由無數的經驗讀者的無數次闡釋活動,最后才能靠近標準讀者。艾柯指出文本意義的豐富性和多元性,闡釋者永遠無法窮盡文本的意義。但是艾柯把這些意義又劃分出一條標準:“對一個文本某一部分的詮釋如果為同一文本的其他部分證實的話,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能,則舍棄。”{17} 闡釋的最后決斷因素回歸到文本那里。文本意圖成為闡釋的決定因素,讀者闡發出來的文本意義必須具有文本佐證才有效,沒有文本佐證便成了過度闡釋。在這種意義上,闡釋學歷史上的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兩種觀點得到調和,主觀成分和客觀成分形成了一種新的關系。其實闡釋學中心的轉移,乃至對于作者、文本和讀者關系的研究,已經為當代人們如何闡釋文本意義提供了基本框架。尤其是,艾柯的“過度闡釋”對于“使用文本”與“闡釋文本”的區分更是與“強制闡釋論”有一些內在的相通性,具有區分闡釋邊界的問題意識。
三、闡釋的限度和有效性
張江指出:“公正的文本闡釋,應該符合文本尤其是作者的本來意愿。文本中實有的,我們稱之為有,文本中沒有的我們稱之為沒有,這是符合道德要求的。”{18} 文本闡釋的唯一依據來源于作者的文本意義,大體上屬于作者意圖的闡釋方式。這種觀點有其合理性,肯定了作者對文本形成的決定意義,符合文學創作活動的實際。但是作者意圖會完全決定闡釋活動嗎?作者只是文學活動的一環,闡釋活動所面臨的對象是一個由語言構造起來的文學文本。文本創造出來就不再完全受制于作者。作者對于闡釋的影響是通過文本與闡釋者潛在對話而實現的。而文本闡釋更是一個歷史存在,闡釋具有歷史性。“闡釋歷史性的提出,使我們認識到文本意義的闡釋是一個無限的過程,它隨著歷史的延伸而不斷的生成,這就形成了闡釋的無限性和開放性。……也就是說,讀者的每一次闡釋都不過是闡釋的無限性的一個有機的構成部分,永遠無法窮盡作品的意義。”{19} 闡釋的歷史性就對作者意圖提出了挑戰。由此,理解文本闡釋問題,局限于某一因素的思維定式似乎不可能,綜合考量多種因素才會更具有合理性。
卡勒提出,文本意義由意圖(作者)、文本、語境和讀者四個要素組成。“關于這四個要素的論證本身就表明意義是非常復雜的,難以表述的。”{20} 這四個要素中,語境作為文學闡釋涉及到的基本要素普遍存在于各種闡釋學中,而其他三個要素則成為不同的闡釋傳統所依賴的支柱。在歷史上的文本觀念和闡釋學理論的基礎上,我們應該綜合考察四要素在文本闡釋中的作用。
首先,作者作為文本的創造者,作者意圖制約了文本生成的樣態,必然存在于文本中,是文本意義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作者意圖是文本意義來源,闡釋活動首先應該重視作者意圖。雖然不可能完全如古典闡釋學主張還原作者原意,但是作者意圖間接制約了闡釋者的闡釋文本意義的走向。作者意圖對于文本非常重要,但是也應該指出的是作者的作用也是有限度的。“作者意圖顯然是我們闡釋文本的重要依據,但并不是唯一依據。”{21} 而且很多時候,作者與文本的關聯性并沒有確切的證據,難以按圖索驥。其次,在整個闡釋活動中,文本才是核心,是闡釋活動面對的客體。文本具有意義生成的多重性,作者意圖只是其中之一,其本身意義生成具有多種可能性。這與文本自身的語言構造有直接關系。文本具有明確性和含混性,就決定了文本的不確定性和確定性兩種成分并存。確定性就來源于作者意圖,而不確定性是隨著不同情境變化而變化。闡釋的目標就是在確定性的基礎上發掘不確定性的意義。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是無論闡釋的結果如何,它始終是哈姆雷特。文本的制約性就得到了證實。不確定性變化的因素最為重要的是語境。正如艾柯所言:“當文本不是面對某一特定的接受者,而是面對一個讀者群時,作者會明白,其文本詮釋的標準將不是他或者她本人的意圖。而是相互作用的許多標準的復雜綜合體,包括讀者及讀者掌握語言的能力……即這種語言所產生的文化成規以及從讀者的角度出發對文本進行詮釋的全部歷史。”{22} 這種文化成規就涉及到社會歷史文化語境,對于批評家而言還涉及到闡釋的歷史。“語境包括語言規則,作者和讀者的背景,以及任何其他能想象出的相關的東西。”{23} 語境是不作為顯在的因素出現的,它是闡釋的潛在因素。讀者所處的語境,乃至作者所處的語境,都使文本意義發生不斷的變遷。最后,讀者作為闡釋學主體,其在文本意義生成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從表面上看,闡釋活動就是讀者和文本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由此考察讀者本身闡釋意義的條件也成為分析闡釋有效性的基本條件。在闡釋學理論中,讀者受到的制約就是歷史性因素。伽達默爾的“先入之見”,姚斯的“期待視野”都指出了讀者具有客觀的、先在的理解前提。闡釋的差異性與共識性也都與這種前提有直接關系。
從總體上看四種要素:作者是文本的創造者;語境是闡釋活動的場景,伴隨著闡釋活動的始終;文本是核心,溝通作者和讀者;讀者是闡釋的主體,潛在地與作者對話。作者、文本、語境、讀者四種要素同時存在于闡釋活動中,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理解文本意義的來源必須綜合考量四種要素,不能單獨偏于一端。尤其在當前的新媒體文學創作中,文學活動的要素更是發生了新的變化。例如在網絡文學中,作者的創作不是封閉的,也不是完成整個作品后才給讀者閱讀。網絡文學是在一個虛擬網絡社區中來創作的,每一天完成一定的量來給讀者閱讀。在創作過程中,作者一邊寫,讀者一邊看。作者在寫作之余也會看看讀者的評論,或者把寫作大綱發給讀者征求意見。讀者也會通過各種方式把自己的意見反饋給作者。尤其是網站編輯也會通過各種方式指導作品的寫作方向。也就是說,網絡文學的創作中,作者、讀者還有“文學中介人”構成一個系統,文本意義的塑造變成了一個共同體。因此,對于文本意義的來源更難以確定為一個因素了。
那么,在明白文本意義來源的共同體后,我們怎么樣判斷文本闡釋的邊界和有效性?這也是“強制闡釋論”所提出的問題。張江明確反對“用理論闡釋文本,對文本做無邊界、無約束的發揮”{24}。張江擊中了當前文本闡釋存在的關鍵問題。文本意義的生成是無限的,闡釋活動也是無限的,雖然不存在唯一正確的闡釋,但是存在闡釋的邊界。在四要素中,作者和語境只是潛在地發揮作用,而讀者和文本則是具體的。確立文本闡釋的邊界,首先應該在二者之間尋找。在文本意義的結構中,我們可以將其區分為兩種成分:讀者解讀出的意義是主觀成分,作者提供的文本材料是客觀成分。主觀成分應該受制于客觀成分。也就是說,讀者闡釋出的意義是在與文本的對話中實現的。在肯定讀者主體作用的同時,必須以客觀的文本作為驗證的最后依據。對此,艾柯提出文本闡釋的“證偽”原則:雖然無法證明何種闡釋是準確的,但是可以證明何種闡釋是錯誤的,其標準就是文本自身。對于這一點,我們贊成張江的觀點,一切要以文本為依據,文本自身就是闡釋的邊界。
確立了文本闡釋的邊界,還需要確立一下什么樣的闡釋才是有效的,是不是只有從文本中解讀出作者的原意才是有效的,其他的解讀都是無效的?在《闡釋的邊界》中,張江重申了“突出強調對作者意圖和文本自在含義的積極追索”{25} 作為闡釋有效性的依據。在我們看來,這個劃分是狹窄的。我們認為,闡釋的有效性指的是文本意義解釋的合理性,而不是唯一性。不管是意義還是意味,凡是能在文本中找到依據的闡釋,都是有效的。由此來看,這個有效性并不是局限于作者意圖,而是包含著作者、文本、語境和讀者四要素的綜合。當代的闡釋理論雖然強調一種因素,但是都能認識到其他因素的作用,認識到闡釋的復雜性。當然,闡釋者發現作者意圖的闡釋是有效的,無可挑剔的。但是這里有一個核心問題:如何確定作者意圖,作者解說自己的意圖了嗎?很明顯,我們大部分時候很難找到作者提供的闡釋文本的材料。由此,對于絕大部分作品而言,尋找作者原意似乎是不可能的。作者意圖的重建就只能是一種理論的言說。文本的意義主要是給闡釋者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意義就是在這個框架中衍生的。 所以,對于文本闡釋而言,最后的根據就是文本自身,去尋找作者意圖是費力不討好的事情。
另外,文本開放性結構決定了意義的多元性。排除了艾柯所說的那些作者故意留空白的作品,就文本自身而言,文本意義的呈現并不是明白無誤的、確定無疑的,它是以意象或形象的方式呈現出來的。這里就具有了許多模糊性、不確定性。“一件藝術作品,其形式是完成了的,在它的完整的、經過周密考慮的組織形式上是封閉的,盡管這樣,它同時又是開放的,是可能以千百種不同的方式來看待和闡釋的,不可能是只有一種解讀,不可能沒有替代變換。對作品的每一次欣賞都是一種闡釋,都是一種演繹,因為每次欣賞它時,它都以一種特殊的情景再生了。”{26} 文本自身的開放性,就決定了闡釋者本身會根據語境的不同去闡釋文本意義。只要他的闡釋在文本中能找到依據就是有效的。在現在的文學場域中,我們不能以作者意圖的合法性,去封閉文本自身,否定根據文本闡釋的有效性。如《小二黑結婚》中的三仙姑形象就隨著文化語境的變遷而發生變化。在中國文化語境中,她是一個老來俏的、為老不尊的家伙;而在美國語境中則被闡釋成個性解放的典型。這兩種闡釋都是有效的,因為文本自身的人物性格特點符合這種闡釋意義。
注釋:
①{18} 張江:《強制闡釋論》,《文學評論》2014年第6期。
②{24} 張江:《批評的公正性》,《中國文學批評》2015年第2期。
③ 張法:《全球化時代的文藝理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頁。
④ 艾略特:《艾略特文學論文集》,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頁。
⑤ 波利亞科夫:《結構——符號文藝學》,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頁。
⑥ 羅蘭·巴特:《S\Z》,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頁。
⑦{26} 艾柯:《開放的作品》,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9頁。
⑧ 王一川:《語言烏托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頁。
⑨ 弗里德里希·施萊爾馬赫:《詮釋學箴言》,《理解與闡釋》,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頁。
⑩ 威爾海姆·狄爾泰:《對他人及其生命表現的理解》,《理解與闡釋》,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頁。
{11} 帕爾默:《海德格爾的本體論和伽達默爾的哲學闡釋學》,《安徽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
{12}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頁。
{13}{15}{16}{17}{22} 艾柯:《詮釋與過度詮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24、26、68、72、72頁。
{14} 利科爾:《詮釋學與意識形態》,《理解與闡釋》,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467頁。
{19} 張良叢:《文本解釋的限度和有效性》,《文藝評論》2009年第1期。
{20}{23} 喬納森·卡勒:《文學理論入門》,譯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69、40頁。
{21} 周憲:《文學闡釋的協商性》,《中國文學批評》2015年第2期。
{25} 張江:《闡釋的邊界》,《學術月刊》2015年第9期。
作者簡介:張良叢,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黑龍江哈爾濱,150080;唐東霞,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江蘇南京,211168。
(責任編輯 劉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