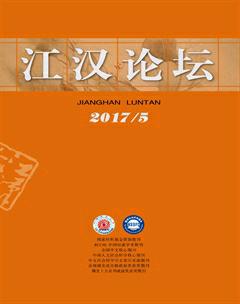漢字批評:文論闡釋的中國路徑
摘要:無視西方語言與漢語言的根本性差異是導(dǎo)致“強(qiáng)制闡釋”的重要原因,故中國文論避免“強(qiáng)制闡釋”的途徑之一是回歸“漢字批評”,即在文論闡釋中回歸漢字思維、漢字意識和漢字本位。“漢字批評”的學(xué)理依據(jù)有三。其一,中國文論的根在古文字(殷虛卜辭、商周銘刻、周秦籀篆),故文論闡釋須追溯字義根柢及字文化淵源,從形、聲、義的不同層面詁訓(xùn)語根,詮釋語義,演繹語義之原生、衍生、再生及生生不息,辨析本義與他義(如古代梵語與近現(xiàn)代西語)的博弈或格義。其二,漢語的性質(zhì)是表意,意之所隨者緣境而異,高度語境化決定中國文論闡釋對文本的高度重視,故須依據(jù)文學(xué)及文論文本返回語義現(xiàn)場,于敷陳事理與攝舉文統(tǒng)的互通中厘清中國文論的理論內(nèi)涵。其三,漢語生命力強(qiáng)盛以及長壽的秘訣在于常用常新,就中國文論之語用而言,因其通而亙古亙今,因其變而日新其業(yè),故須在會通適變之際重識中國文論的語用生命,揭示其歷史意蘊(yùn)及現(xiàn)代價值。中國文論孳乳于漢字語根、鮮活于語境而通變于語用,文論闡釋的中國路徑必然創(chuàng)生并通達(dá)于追根、問境和致用之際。
關(guān)鍵詞:漢字批評;文論闡釋;追根;問境;致用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xué)基金重大招標(biāo)項目“中國文化元典關(guān)鍵詞研究”(12&ZD153)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7)05-0067-07
在論及不能用西方理論強(qiáng)制闡釋中國文論的實踐及理論緣由時,張江教授指出了“一個基本事實”:“西方語言與漢語言,無論在形式還是表達(dá)上都有根本性的差別,用西方語言的經(jīng)驗討論和解決漢語言問題,在前提和基礎(chǔ)上存在一些根本的對立。不能簡單照搬,也不能離開漢語的本質(zhì)特征而用西方語言的經(jīng)驗改造漢語。……實踐證明,語言的民族性、漢語言的特殊性,是我們研究漢語、使用漢語的根本出發(fā)點(diǎn),也是我們研究文學(xué)、建構(gòu)中國文論的出發(fā)點(diǎn)。離開了這一出發(fā)點(diǎn),任何理論都是妄論。”①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xué)教程》將漢字歸入“表意體系”,隨后宣稱他的研究“只限于表音體系”②。當(dāng)我們別無選擇地要用漢字闡釋中國文論時,首先需要回答的卻是:作為“表意體系”的漢字,其根本性特征是什么?而緊隨其后的追問則是:由漢字的特征所決定的中國文論闡釋的路徑何在?漢字的語根太深,故須追“根”;漢字的語境太重要,故須問“境”;漢字的語用是其長壽秘訣,故須致“用”。由追“根”而問“境”,由問“境”而致“用”,似可探出一條文論闡釋的中國路徑。
漢語的根柢深藏在古文字(殷墟卜辭、商周銘刻、周秦籀篆)之中,需要刨“根”才能問底。從20世紀(jì)初的甲骨文,到21世紀(jì)初的清華簡、上博簡,每一次考古發(fā)現(xiàn)都是一次刨根問底。隨著“新”的文字材料的不斷出現(xiàn),“新”的古文字被不斷識認(rèn),中國文論闡釋的新景觀新氣象新收獲便在刨“根”中不斷呈現(xiàn)和展開。
漢語的性質(zhì)是表意,意之所隨者緣境而異。漢語之“表意”既無時態(tài)標(biāo)識,亦不重空間定位(如前后、內(nèi)外、出入等所指頗為隨意),更有反訓(xùn)、隱喻、假借、轉(zhuǎn)注、諧音之類,使得漢語的言說與解讀高度語境化,若脫離語境則“不知所云”。中國文論的話語體系“話中有話”,故闡釋之時先須問“境”,先須返回語義現(xiàn)場,非如此不能釋名彰義、敷理舉統(tǒng)。
漢語“長壽”的秘訣在于語用,《周易》“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宏大之用,《文心雕龍》“‘心哉美矣,故用之焉”是微觀之用。經(jīng)史子集,周秦漢唐,無不因重“用”而致“用”。漢語的致“用”釀成中國文論的致“用”,中國文論的歷史意蘊(yùn)及現(xiàn)代價值在語用中激活,在語用中衍生、再生乃至生生不息。
一、追“根”
黃侃論及“清代小學(xué)之進(jìn)步”,贊其“一知求本音,二推求本字,三推求語根”③。這里的“語根”是在聲韻和訓(xùn)詁的層面談文字;若在文字、聲韻和訓(xùn)詁的層面談中國文論闡釋,則應(yīng)將古文字視為中國文學(xué)及文論的語根。張江《闡釋的邊界》稱“文本的能指是文本闡釋的出發(fā)點(diǎn)和落腳點(diǎn)”④,所謂“文本的能指”即文學(xué)和文論文本的語言。文論闡釋的首務(wù)在于“推求語根”,這個意義上的“語根”,實則包括了黃侃所說的“本音”、“本字”以及最早的形、聲、義對字之“本義”的規(guī)定和鑄造。
文字乃經(jīng)藝之本,故許慎解“字”說“文”皆重“推求語根”即看重“本義”。⑤ 王力指出:“許慎抓住字的本義,這是從根本上解決訓(xùn)詁問題。本義是一切引申義的出發(fā)點(diǎn),抓住了本義,引申義也就有條不紊。本義總是代表比較原始的意義,因此,與先秦古籍就對得上口徑。”⑥ 又稱“從本義可以推知許多引申義,以簡馭繁,能解決一系列問題”⑦。中國文論闡釋,用黃侃的話說,需要“推求語根”;用劉勰的話說,需要“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彰)義”⑧。對于中國文論闡釋而言,不求語之“根”,不原字之“始”,則無法表其末,更無從釋其名、彰其義。
“中國文論”又稱“中國古代文學(xué)理論”,其中“中國古代”與“理論”分別標(biāo)明時空與領(lǐng)域,而“文學(xué)”為其核心范疇即關(guān)鍵詞。如何釋“文學(xué)”之名,彰“文學(xué)”之義,事關(guān)中國文論話語體系的當(dāng)代建構(gòu)和中西文論的平等對話。而我們今天對“文學(xué)”這一關(guān)鍵詞的詮釋,從高校教材到學(xué)術(shù)專著,從期刊論文到大眾傳媒,大體上是襲用20世紀(jì)以來的西方文論的定義,強(qiáng)調(diào)的是“文學(xué)”的審美性、虛構(gòu)性和意識形態(tài)屬性,依據(jù)的是三分法(現(xiàn)實、理想、象征)和四分法(詩歌、小說、劇本、散文)。⑨ 用這種從近現(xiàn)代西方文論引進(jìn)的“文學(xué)”概念,向“前(昔)”不能解釋古代文學(xué)(比如經(jīng)史子集中的文學(xué)文本),向“后(今)”不能解釋當(dāng)下文學(xué)(比如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文學(xué)文本),從而導(dǎo)致“文學(xué)”這一關(guān)鍵詞之“能指”與“所指”的分離,導(dǎo)致文藝學(xué)理論與文學(xué)史事實的分離。
導(dǎo)致“分離”的原因自然是強(qiáng)制闡釋,是強(qiáng)制闡釋中對漢語言與西方語言之根本性差異的無視或忽略,是文論闡釋中未能追問漢語“文學(xué)”的文字之根。 “文學(xué)”的語根是“文”;那么,“文”的語根又是什么?許慎《說文解字》:“文,錯畫也,象交文,凡文從屬皆從文。”段玉裁在注明“錯當(dāng)作逪”之后,斷定“逪畫者文之本義”⑩。許說和段注皆強(qiáng)調(diào)“文”的符號性、裝飾性和結(jié)構(gòu)性,似與西語“文學(xué)”的審美性相契合。然而,《說文解字》所說的“文”,并非“文”的語根,因而亦非“文學(xué)”的語根。“文”的語根在殷墟卜辭,而殷墟卜辭出土于19世紀(jì)末20世紀(jì)初。因而,無論是生活于1至2世紀(jì)之交的許慎,還是生活于18至19世紀(jì)之交的段玉裁,皆無緣見到甲骨文,無緣得知“象正立之人形,胸部有刻畫之紋飾,故以文身之紋為文”{11} 的甲骨文釋義,無緣尋覓“以文身之紋為文”的“文”之本義。
《說文解字》用的是篆體,篆體的“文”字,看字形已經(jīng)丟失了甲骨文“文”字上本有的胸部之紋身,因而也丟失了“文”之本義,從而在某種程度上遮蔽了“文”的語根。刨根問底,文,首先是一個動詞,因為文身是一種動作,一種行為。《禮記·王制》有“被發(fā)文身”,鄭玄注曰:“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這種動作或行為有藝術(shù)味道,有創(chuàng)作性質(zhì),故可以說是一種藝術(shù)行為(或如今人所謂“行為藝術(shù)”)。文,同時也是名詞,因為文身的結(jié)果只能用“胸部有刻畫之紋飾”的“文”來祼呈或確證。文,又是一個形容詞,意謂文身的、文飾的、有文采的等等,類似于后來加上了“彡”的“彣”{12}。不同的是,“文”是文身之飾而“彣”則是以毛飾畫亦即許慎“彡,毛飾畫文也”{13}。從廣義上講,“文身”可以說是人類最早的“文學(xué)”(即“文化”創(chuàng)作);就文身這一文學(xué)創(chuàng)作活動的全過程而言,用作動詞的“文”是行為或曰文學(xué)活動,用作名詞的“文”是文本或曰文學(xué)作品,而用作形容詞的“文”則是屬性或曰文學(xué)性。由此可見,漢語“文學(xué)”的全部義項及特征,都可以在甲骨文的“文”之中尋覓到它的語根。
文身,作為人類最早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或文化行為,其主體與客體都是人:“人”飾畫其身;文身飾畫于“人”的身體。我們今天常說“文學(xué)是人學(xué)”,其根柢正在于此。其一,人體與文體集于一身,人體就是文體,文體就是人體。雖然隨著書寫工具或媒介的進(jìn)化,“文體”逐漸與“人體”分離,但二者在根柢處依然血肉相連。中國文論經(jīng)常性地借“人體”來說“文體”,借人體的其異如面來說文體的風(fēng)貌萬千。于是,我們有了“文學(xué)文體學(xué)”和“文學(xué)風(fēng)格學(xué)”。其二,文身刻畫于人的胸部,亦即心之表,文乃心畫心聲,根于心緣于情,文自于人,文心自于人心,文學(xué)的歷史是人類心靈的歷史。于是,我們有了“文學(xué)心理學(xué)”。其三,文身是原始部落的人類行為,其行為動機(jī)不僅僅是裝飾,更是對部落圖騰的顯示,故所“文”之“紋”,有明顯的人類學(xué)意味。于是,我們有了“文學(xué)人類學(xué)”。其四,文身是“人為”的,更是“為人”的,既為了個體身體的美飾,亦為了不同部落的辨識,無論是在功利的還是在超功利的層面考量,“為人”的文學(xué)都具有深刻的倫理學(xué)內(nèi)涵。于是,我們有了“文學(xué)倫理學(xué)”。
概言之,“以文身之紋為文”是“文”的語根,因而也是漢語“文學(xué)”的語根。無論是從《論語·先進(jìn)》的“文學(xué),子游,子夏”到《世說新語》的“文學(xué)”之門,還是從屈原的“青黃雜糅,文章爛兮”到劉勰的“聲文、形文、情文”,漢語的“文學(xué)”釋義從來都是與西語的定義大相徑庭的。究其根由,則可以從“文學(xué)”的語根處得到合理的解釋。即便是到了西方文論話語呈霸權(quán)趨勢的20世紀(jì)初,我們依然能夠看到以漢語的“文”為語根的“文學(xué)”釋義。
章太炎《國故論衡·文學(xué)總略》:“文學(xué)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xué)。”{14} “著于竹帛”的是“文”,著于龜甲獸骨和鐘鼎銘器當(dāng)然也是“文”,而且是更早更古更為根柢的“文”。章太炎的這一條關(guān)于“文學(xué)”的定義,表面似將“文學(xué)”與“文字學(xué)”等同,實質(zhì)上是在根柢處找到了“文學(xué)”與“文字”的關(guān)聯(lián),從而部分地尋覓到了漢語“文學(xué)”的語根。
黃人《普通百科新大辭典》收錄“文學(xué)”詞條:“我國文學(xué)之名,始于孔門設(shè)科,然意平列,蓋以六藝為文,篤行為學(xué)。后世雖有文學(xué)之科目,然性質(zhì)與今略殊。漢魏以下,始以工辭賦者為文學(xué)家,見于史則稱文苑,始與今日世界所稱文學(xué)者相合。敘藝文者,并容小說傳奇(如《水滸》《琵琶》)。茲列歐美各國文學(xué)界說于后,以供參考。以廣義言,則能以言語表出思想感情者,皆為文學(xué)。然注重在動讀者之感情,必當(dāng)使尋常皆可會解,是名純文學(xué)。而欲動人感情,其文詞不可不美。故文學(xué)雖與人之知意上皆有關(guān)系,而大端在美,所以美文學(xué)亦為美術(shù)之一。”{15} 黃人關(guān)于“文學(xué)”的定義,雖然受到西方近現(xiàn)代文學(xué)觀念的影響,但他看到了漢語“文學(xué)”的特質(zhì),在一定程度上觸及到了“文學(xué)”的漢語語根。
二、問“境”
中國文論的“根”深深地扎在殷虛卜辭、商周銘刻、周秦籀篆等古文字之中,故文論闡釋之首務(wù)是追“根”。根深則葉茂,葉茂則華實,中國文論的衍生、更生、再生乃至生生不息,必定發(fā)生在具體的文本或曰具體的文本語境之中。即以上一節(jié)對“文”的刨根問底而言,如果離開了語境(如卜辭銘文、先秦元典、秦漢字書等),是根本說不清楚的。是故劉勰《文心雕龍·序志》篇要講“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振葉”無以尋根,不“觀瀾”無以索源。在某種意義上說,劉勰所講的“葉”和“瀾”是指中國文論歷史的和文本的語境。福柯指出:“我們必須完全按照話語發(fā)生時的特定環(huán)境去把握話語。”張江亦認(rèn)為:“我們應(yīng)該在那個時代的背景和語境下闡釋文本的意圖。超越了那個時間或時代闡釋文本,以后來人的理解或感受解讀文本,為當(dāng)下所用,那是一種借題發(fā)揮,有明顯強(qiáng)制和強(qiáng)加之嫌。”{16}中國文論闡釋之語境大體上可分為兩類:一是大語境即歷史文化語境,二是小語境即具體的文學(xué)及文論文本。就前者而言,要追問并探求中國文論與儒道釋文化的關(guān)系;就后者而論,則要追尋并返回文本語義現(xiàn)場。二者交相呼應(yīng),相得益彰,共同構(gòu)成中國文論闡釋的“問‘境”之途。
先說大語境。中國文學(xué)理論批評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歷朝歷代的文學(xué)觀念及理論術(shù)語,或標(biāo)舉時代風(fēng)貌或革前代之故鼎后代之新,均與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化語境相關(guān)。先秦兩漢是中國文論的創(chuàng)立和奠基期,其文論創(chuàng)生與這個時代從儒道爭鳴到儒學(xué)獨(dú)尊的文化語境密切相關(guān)。儒家文論的“詩言志”、“興觀群怨”、“文質(zhì)彬彬”、“以意逆志”,道家文論的“虛靜”、“大音希聲”、“心齋坐忘”、“得意忘言”,無一例外是特定文化語境下的產(chǎn)物,故其闡釋的有效性取決于歷史語境的還原。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文論的繁榮期,其文論新變緣于玄學(xué)新變及儒道會通。從曹丕的“文氣”到陸機(jī)的“緣情”到劉勰和鐘嶸的系列范疇及命題,均須在玄學(xué)語境下方能作深度解讀。唐宋金元是中國文論的多元時代,其文論路徑是“載道”、“取境”和“妙悟”的分途或并進(jìn),其文化語境則是該時段儒、道、釋的三教合流。明清是中國文論的總結(jié)期,其文論闡釋的總歸性特征是以傳統(tǒng)文化之總匯以及各體文學(xué)之總備為語境的。近代是中國文論的轉(zhuǎn)型期,此時期的文論闡釋帶有明顯的中西交通和古今交融的特征,而此特征理所當(dāng)然是由“西學(xué)東漸”的時代語境所釀成。概言之,無論是在小時段還是在大時段闡釋中國文論,一個別無選擇的選擇是問“境”。
次說小語境。如果說本文第一節(jié)所言“文學(xué)”是根本層面的關(guān)鍵詞,那么“文體”則是基本層面的關(guān)鍵詞,故中國文學(xué)批評史上空前絕后的理論巨制《文心雕龍》,被稱為“我國的文體論”{17}。“文學(xué)”的語根是“文”,“文體”的語根是“體”。甲骨文有“身”而無“體”,《說文解字》許說概言為“體,總十二屬也”,段注將“十二屬”詳言為人體的十二個部位,故知“體”的本義是指人的身體。“體”,作為中國文論的元關(guān)鍵詞可獨(dú)立語用,同時又是諸多關(guān)鍵詞的語根,后者如文體、語體、大體、體用、體性、體貌、體要、體目、體植等等。無論是獨(dú)立成詞抑或作為構(gòu)詞元素,“體”之立義皆緣“境”而生,故 “體”之釋義須問“境”而成。
以《文心雕龍》的諸“體”為例。劉勰在《序志》篇中論及《文心雕龍》的寫作動機(jī),先是悲嘆他那個時代的文學(xué)“去圣久遠(yuǎn),文體解散……離本彌甚,將遂訛濫”,然后贊嘆“周書論辭,貴乎體要……辭訓(xùn)之異,宜體于要”。這一段文字中,“體”字三見,在不同的上下文(即語境之中),其詞義及詞性是大不相同的,若忽略其語境則難以辨察其異。“文體解散”云云,“解散”的“文體”絕非指文類意義上的某一種(或多種)“體”,而是總體甚至本體意義上的整個時代的文學(xué)體統(tǒng)或體制,有“總體”、“整體”、“本體”之義。{18} “貴乎體要”或“宜體于要”,兩個“體”皆用作動詞,作體察、體會、體悟來講(另有《征圣》篇四次談到“體要”)。當(dāng)然,這兩種意義上的“體”均與其語根(身體)相關(guān):前者源于其總體,后者源于其功能。
除了總體性與功能性的“體”,《文心雕龍》的“體”還有多種用法,如《征圣》篇的體用之體(“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體性》篇的文學(xué)風(fēng)格之體(“若總其歸途,則數(shù)窮八體”),以及《諧隱》《麗辭》諸篇的身體之體(“體目文字”;“體植必雙”等)。此外,《時序》篇有“體貌英逸”,“體貌”用作動詞,有禮敬、敬重、以禮相待之義。后來紀(jì)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贊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各以韻語十二句體貌之”,其“體貌”也是用作動詞,意謂體悟之、描繪之,其“體”之義異乎《時序》卻同于《序志》。
中國文論闡釋所問之“境”,除了上述宏觀之文化歷史語境與微觀之文本章句(即上下文)語境,還有介于二者之間的文本篇籍語境。以司馬遷“發(fā)憤著書”為例。其微觀語境是太史公排比的“古來圣賢,不憤不作”的八個例子;其宏觀語境則是太史公所處的帝國政治及社會生活狀態(tài),其中包括家境衰敗及李陵之禍。而介于二者之間的則是兩個文本:《報任安書》和《史記·太史公自序》。同一個“憤”字,在兩個不同的文本之中,其語義、語感、語用以及與其語根的關(guān)系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有著雖細(xì)微卻不容忽略的差異。
《太史公自序》作為《史記》的導(dǎo)引性文本,承擔(dān)著自言其志和自塑其人格的重要使命,故作者用很大的篇幅宣講圣人的《春秋》大義,于此宏大語境下自謙式地描述自己的著史大業(yè)。到《自序》快要結(jié)束的時候,太史公才提到“發(fā)憤著書”,并將“憤”的內(nèi)涵歸結(jié)于“人皆意有所郁結(jié),不得通其道也”。司馬遷對“憤”的這種詮釋,頗合于“憤”的語根義。《說文解字》有“憤,懣也”,又有“懣,煩也,從心滿”,還有“悶,滿也。從心,門聲”,《說文》所收屬于“憤”系列的字還有惆、悵、愾、燥、愴、怛、慘、悲、惻、惜、愍、慇等等。這里的“憤”并非我們后來所理解的“憤怒”甚至“仇恨”,而是“懣”即郁悶、煩悶和憋悶。如果說“憤怒”的心理指向是向外的,其程度是強(qiáng)烈的;那么,“憤懣”的心理指向則是向內(nèi)的,其程度是亞強(qiáng)烈的。這里的“憤”與《論語》的“不憤不啟,發(fā)憤忘食”,《楚辭·九章》的“發(fā)憤以抒情”大體相類似。
《報任安書》的“發(fā)憤著書”,其文字其例證與《太史公自序》完全相同,但由于文本語境有別,故“憤”之語義及語感大異。《報任安書》是書信體,朋友之間的交談是坦陳的,無須掩飾或遮蔽。我們看司馬遷在好朋友面前,字字血、聲聲淚地敘述李陵之禍和家世之衰,抒發(fā)悲怨之怒和絕望之情。在由怨怒和絕望所釀成的獨(dú)特語境之下,其“憤”已遠(yuǎn)離了先秦的詞根義而開啟了引申義,后者頗類似于李贄的“憤書”說。晚明李卓吾《焚書》標(biāo)《忠義水滸傳》為“憤書”,其“憤”之所指為“憤怒”:“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也。”顯然,在這里“憤”的心理指向是朝外的,所謂“泄其憤”;“憤”的內(nèi)容則事關(guān)朝野,事關(guān)古今,所謂“憤二帝之北狩”,“憤南渡之茍安”。{19}
“發(fā)憤著書”作為中國文論的一個重要命題,在不同的文本中,因其語境的差異,其“憤”之語義和語態(tài)是有很大差別的,由此可知問“境”之不可或缺,又由此可知文論闡釋須返回歷史語義現(xiàn)場。陳曉明指出:“避免‘強(qiáng)制闡釋的方法論途徑可能就在于,更為直接地回到作品文本,從作品文本的文學(xué)性生成中激發(fā)理論要素,概括理論規(guī)律,建立理論范式及連接的形式。”{20} 張江在談到中西文論之差異時亦指出,“中國古代文論,從文本出發(fā),牢牢依靠文本,得出有關(guān)文學(xué)的各種概念和理論”{21}。中國文論若要避免“強(qiáng)制闡釋”,需要返回文學(xué)及文論文本的語義現(xiàn)場:講“詩言志”須回到《尚書》和《左傳》,講元白的“諷諭”須回到《與元九書》,講李贄的“童心”須回到《焚書·續(xù)焚書》和《藏書·續(xù)藏書》,講“悲劇”須回到《紅樓夢評論》和《人間詞話》……
三、致“用”
人類軸心期五大文明(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希臘、古印度、古華夏)在其輝煌之時皆有自己的文字。而這幾種古文字,今天仍在使用的惟有漢字。漢字亙古亙今,生生不息,個中緣由非常復(fù)雜,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用”。因其重“用”、致“用”,故方塊字既沒有被梵化,也沒有被拉丁化,在今天更沒有被歐美化。許慎《說文解字·敘》:“蓋文字者,經(jīng)藝之本,王政之始。”詮解經(jīng)藝要用漢字,推行王政要用漢字,譯迻外來佛典要用漢字,元代蒙族和清代滿族在得天下之后依然要用漢字……漢字在幾千年的使用之中,有通有變,常用常新。陳曉明指出,漢語文學(xué)“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漢語言特性與現(xiàn)代意識、民間的原生態(tài)與現(xiàn)代主義小說技巧等諸多方面,可發(fā)掘的學(xué)理問題當(dāng)是相當(dāng)豐富復(fù)雜”{22}。漢語文學(xué)如此,漢語文論亦然。漢字的致“用”,直接導(dǎo)致了中國文論的致“用”,因而成為我們今天探討文論闡釋之中國路徑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
漢字致“用”早在五經(jīng)之首《周易》中就有鮮明之顯現(xiàn),《周易·系辭上傳》既有“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總體上強(qiáng)調(diào)文辭的巨大功能和作用;又有“《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分列《周易》的四大功用:“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23} “尚其辭”者,重其辭也;后面的“尚其變”、“尚其象”和“尚其占”,實際上是說如何在不同的領(lǐng)域使用《周易》的文辭,故四“尚”實為一“致”:致其“用”也。
《系辭上傳》將“四尚”歸結(jié)為“圣人之道”,本文即以為例來講中國文論闡釋之致“用”。《周易》有“形而上者謂之道”,但“道”的本義(原始義)其實是“形而下”的,即《說文解字》所釋“所行道也”,“一達(dá)謂之道”{24}。“道”在漫長的語義演變之中,由“形而下”上升為“形而上”,特別是在經(jīng)過老莊道家的語用之后,成為一個“寂兮寥兮”具有超越性和本體論特征的元關(guān)鍵詞。但是,即便是在老莊那里,“道”的語義演變過程及其結(jié)果,依然具有致“用”之特征。
“道”的本義為道路,由此則有三大義項。其一,凡道路皆有起點(diǎn)與終點(diǎn),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道”的此一義項上升為形而上,則為對“本源”或“終極”的追問: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這一追問其實是敘事性,或者說是用敘事的方法提出追問,類似于“楊朱泣歧路”,這是關(guān)于“道”的敘事之用。其二,凡道路皆有邊界與軌跡,在道上行走者不能越“界”或越“軌”,否則輕者傷身重者喪命。所謂“在道上行走”,是喻指“按規(guī)律辦事”,尊重規(guī)律,恪守規(guī)則。這是關(guān)于“道”的隱喻之用。其三,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行走者,有不同的行道之方,或艱難跋涉,或安步當(dāng)車,或自騁驥馬錄,或御使軒轅。上升為形而上,則是不同的方法或技藝。方法或技巧是拿來“用”的,用得好就成為某家某派的招牌或標(biāo)志,用得不好自然是砸牌子壞名聲。這是關(guān)于“道”的方法之用。
“道”之用,不僅有形下、形上之別,還有名詞、動詞之分。當(dāng)“道”在先秦元典由形下“所行道”抽象為形上“天之道”時,就成了各家各派不得不道的關(guān)鍵詞。道者,言說也,闡釋也。《莊子·天下篇》:“《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可見儒家是用六經(jīng)說自家的“道”,正如墨家用《墨子》道自家的“道”,道家用《老子》和《莊子》道自家的道,所謂各道其道是也。
先秦諸子的文學(xué)理論和批評,各家各道其道,各家各用其道。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足見“道”對于儒者是何等重要;孔子又說“吾道一以貫之”(同上),此語實乃后世文論“文以貫道”之元生義。作為先秦儒家文論的總結(jié)者,荀子將孔儒之“道”視為文學(xué)的“管”、“一”、“歸”、“畢”(《荀子·儒效》篇),從而開中國文論“原道宗經(jīng)”之先河。老子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老子·四十一章》),講的也是道之用;而莊子作為先秦道家文論的總結(jié)者,大講審美創(chuàng)造的“神乎技”之道,諸如心齋坐忘、法天貴真、卮言日出、得意忘言等,對后世文論產(chǎn)生深遠(yuǎn)影響。
漢魏六朝文論,由經(jīng)學(xué)而玄學(xué),由玄學(xué)而回歸儒學(xué),儒家的“道”始終是“體用”之“體”。兩漢的屈原及楚辭批評,由劉安、司馬遷的褒揚(yáng)到揚(yáng)雄、班固的褒貶參半,再到王逸的只褒不貶,結(jié)論不同,路徑相似:將“道”用之于文學(xué)批評,并完成了“道”對文學(xué)批評的制約和規(guī)訓(xùn)。{25} 劉勰《文心雕龍》以《原道》開篇,以“道”作文學(xué)本源及本體之論,其實質(zhì)是重道之“用”,因重“用”而致“用”。《原道》篇講“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實則是兩重意義上的“道”之“用”:圣人將“道”垂示為“文”,明道之文成為萬世經(jīng)典,此其一;明道之經(jīng)典“旁通”且“日用”,既用之于文學(xué),亦用之于軍國,亦即《序志》篇所言“唯文章之用,實經(jīng)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而《文心雕龍·原道》引《周易·系辭上傳》“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以終篇,又可見劉勰是將《周易》的致“用”之道一以貫之了。
唐宋兩代有諸多差異,但在重“道”這一點(diǎn)上并無二致。以唐代韓愈為代表的儒道譜系重建者,摒除“道”的佛老成分而還原儒家先王之道。韓愈從國計民生的層面,實實在在地討論儒道之利國利民,佛道之害國害民,從而將“文以明道”用作古文運(yùn)動的理論綱領(lǐng)。柳宗元論“道”更重其“用”,《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提出“輔時及物之道”,將有用和有益于時代和社會作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根本。宋代文論的“道”或“理”當(dāng)然也是儒家的,北宋新古文運(yùn)動繼承韓柳“文以明道”之傳統(tǒng),如歐陽修批評那種“棄百事不關(guān)心”的文士(《答吳充秀才書》),主張“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以事”(《與張秀才第二書》)。王安石更是主張“所謂文者,務(wù)為有補(bǔ)于事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縷繪畫也。……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縷繪畫為之容而已”(《上人書》)。
到了明代,由陽明心學(xué)的心性之道,走向王學(xué)左派的百姓日用之道,后者尤其看重道之“用”。作為王學(xué)異端的代表性人物,李贄用他的《焚書·續(xù)焚書》和《水滸》評點(diǎn),在明代的文學(xué)理論批評中,為“道”這個關(guān)鍵詞添加了頗有異端和啟蒙色彩的思想內(nèi)涵。晚明的“百姓日用”之道,向上承接《周易》的憂患之道,向下開啟清代三大思想家顧、黃、王的啟蒙之道。清季以降,“道”之用有兩個新義項值得注意。一是以“道—器(技)”博弈應(yīng)對外族進(jìn)攻;二是以“道—logos”對談應(yīng)對中西文化及文論沖突。漢語的“道”既可以是名詞也可以是動詞,這與希臘語的logos正好可以互譯互釋。錢鐘書《管錐編》釋《老子王弼注》的“道可道,非常道”,稱“古希臘文‘道(logos)兼‘理(ratio)與‘言(oratio)兩義,可以相參”{26}。由此亦可見,不同時代的文學(xué)理論批評對“道”的不同之“道”(言說)和“用”(貫道),標(biāo)識著不同時代的文學(xué)觀念、認(rèn)知路徑和言說方式。
中國文論闡釋中的致“用”,還表現(xiàn)在其批評文體注重語用實例的列舉。浩若煙海的歷代詩話、詞話、曲話、文話等批評文體,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歷代文學(xué)創(chuàng)作及批評的實例薈萃,是張江所說的“僅僅源于文學(xué)的理論”:“中國古典文論的許多觀點(diǎn)就是僅僅來源于文學(xué),比如眾人皆知的各種詩話。”他還指出:“沒有抽象的文學(xué),只有具體的文本。離開具體的文本,離開對具體文學(xué)的具體分析,就沒有文學(xué)的存在。無感情、無意義的符號必然導(dǎo)致對文學(xué)特性的消解,導(dǎo)致理解的神秘化。”{27}文論闡釋若離開了具體的文學(xué)文本,離開了鮮活靈動的文學(xué)例證,不僅會導(dǎo)致神秘虛妄,還會導(dǎo)致枯槁死寂。即便是編寫辭典或字書也要重語用,也要多舉例,“盡可能舉出例證。例證是字典的血肉,沒有例證的字典只是骷髏”{28}。同樣的道理,中國文論之闡釋如果沒有豐富而鮮活的語用之例證,其闡釋文字也會成為無血肉無生機(jī)的骷髏。
就重視語用而言,文論闡釋的致“用”,與其追“根”和問“境”是密切相關(guān)且三位一體的。我們以劉勰的“風(fēng)骨”闡釋為例。《文心雕龍·風(fēng)骨》篇闡釋“風(fēng)骨”,用的是“鳳”還有“雉”和“鷙”作喻例。對于“風(fēng)骨”而言,“鳳”既是“語境”,又是“語用”,還是潛在之“語根”;就“語境”而言,以“鳳”為主角的三禽,為“風(fēng)骨”的出場提供了一個充滿生機(jī)、洋溢詩意的禽系列語義環(huán)境;就“語用”而言,“鳳”之意象則屬于本節(jié)前面所歸納的“敘事”、“隱喻”和“方法”之用;就“語根”而言,“風(fēng)骨”之語義根柢與“鳳”神鳥之“八象”和“五德”相關(guān)。《說文解字》解“鳳”這個字,許慎用了很長的一段文字來舉例:“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像也,麐前鹿后,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于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昆侖,飲砥柱,濯羽弱水,莫(暮)宿鳳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從鳥,凡聲。”{29} 天老是黃帝的臣子,許慎引“天老曰”,將“鳳”這種神鳥的外形、來歷、特性、功力描述得清清楚楚,既繪形繪色,又申名申義。段注詳引郭璞《山海經(jīng)》說“鳳”之“八象其體,五德其文”,不僅繪畫其形而且撮舉其義。我們今天闡釋劉勰關(guān)于“風(fēng)骨”的闡釋,似應(yīng)回到“鳳”的語義現(xiàn)場,向前(昔)追溯許慎所引“天王曰”之用例,向后(今)重述段玉裁所引《山海經(jīng)》之用例,非如此,無法窺見“風(fēng)骨”之語義根柢。由此可見,追“根”、問“境”和致“用”,三者立體交叉地構(gòu)成文論闡釋的中國路徑。
“一達(dá)謂之道”,行走于斯,何“道”不“達(dá)”?這正如“風(fēng)骨”的闡釋和闡釋之闡釋,寄形寓意于“鳳”神鳥,從公元1至2世紀(jì)之交的許慎,到5至6世紀(jì)之交的劉勰,再到18至19世紀(jì)之交的段玉裁,再到20至21世紀(jì)之交的吾輩學(xué)人,一路走來,風(fēng)清骨峻,藻耀高翔。
注釋:
① 張江:《當(dāng)代西方文論若干問題的辨識》,《中國社會科學(xué)》2014年第5期。
② 費(fèi)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xué)教程》,高名凱譯,商務(wù)印書館1980年版,第50—51頁。
③ 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xùn)詁筆記》,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頁。
④{16} 張江:《闡釋的邊界》,《學(xué)術(shù)界》2015年第9期。
⑤⑩{13}{24}{29}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63、425、424、75、148頁。
⑥⑦ 王力:《中國語言學(xué)史》,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35、40頁。
⑧ 本文引《文心雕龍》均據(jù)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8年版。
⑨ 參見童慶炳主編:《文學(xué)理論教程》(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99—220頁。
{11} 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2006年版,第996頁。
{12} 段玉裁說“彣”的本義是“彣彰”,不同于“文”的本義是“逪畫”,但就“文”的甲骨文語根而言,其本義與“彣”有相通之處。
{14} 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頁。
{15} 黃人:《普通百科新大辭典》子集,國學(xué)扶輪社1911年版,第106頁。
{17} 徐復(fù)觀:《文心雕龍的文體論》,《中國文學(xué)精神》,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頁。
{18} 《文心雕龍》有“才量學(xué)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顏氏家訓(xùn)·文章》有“文章當(dāng)以理致為心腎,氣調(diào)為筋骨,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均以“身體”為喻,均含有“整體”“總體”或“本體”之義。
{19} 李贄:《焚書·續(xù)焚書》,岳麓書社1990年版,第108頁。
{20}{22} 陳曉明:《理論批判:回歸漢語文學(xué)本體》,《文學(xué)評論》2015年第3期。
{21} 參見李曉華:《關(guān)于“強(qiáng)制闡釋”的追問和重建文論的思考》,《江漢論壇》2016年第4期。
{23} 本文所引《周易》,均據(jù)阮元:《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
{25} 參見黃霖、李青春、李建中主編:《中國文學(xué)理論批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76—78頁。
{26} 錢鐘書:《管錐編》第2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08頁。
{27} 張江:《強(qiáng)制闡釋論》,《文學(xué)評論》2014年第6期。
{28} 王力:《中國語言學(xué)史》,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97頁。
作者簡介:李建中,武漢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湖北武漢,430072。
(責(zé)任編輯 劉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