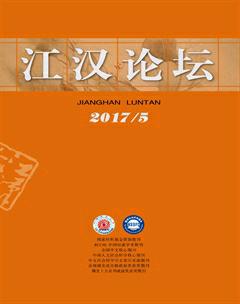作為“現代性”表象的女性描寫
聞一多+鄧捷
摘要:聞一多對愛人、祖國、文學藝術的“裸體的天使和彩鳳”的想象,是他“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的主張和文學審美觀的表露。這一女性表述在兩個層面上體現了聞一多文學活動的矛盾:對以西洋為模式的文學現代性的向往和愛國主義激情之間的矛盾,以及作為表現者的詩人個人的困境:用典雅的形式規范時代的橫暴的激情。而前一種矛盾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由知識分子先驅性的努力而誕生的五四文學所內含的宿命般的課題。
關鍵詞:聞一多;魯迅;現代性;女性;裸體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7)05-0074-05
一、留日作家的“現代性”表述——女性·故國·咖啡·象征詩
1926年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回國的穆木天,這樣感嘆上海沒有好的“咖啡館”和“女侍”:“回想起,在東京……的高架電車里,我站在不知名不知姓看不見臉的伊的背后,聞伊的脖頸上的香,頭發上的香,我的手輕輕的放在距伊不遠不近的地方,我只好出神無語。在日本我常說:女子者,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者也;可是,到了上海,官能的滿足,算是找不到了!”①
用現在女性主義的觀點,我們從這種官能鑒賞中看出男性作家的女性蔑視。但是在當時,對留日學生來說,咖啡店的體驗及對女性身體的描述,和他們所追求的文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1923年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法文系的穆木天的詩、國民文學的主張及象征詩理論是在東京大地震后凌亂的廢墟和大學課堂以及周邊的咖啡館等醞釀出來的 。他在《譚詩——寄沫若的一封信》里一邊講述“純粹詩歌”必須表達詩人的內生活、內生命的飛翔,一邊提倡詩也必須是“國民文學”,要表達鄉土感情、國民意識和描寫國民生活。“國民生命與個人生命不作交響(Correspondance),兩者都不能存在,而作交響時,兩者都存在。……國民文學是交響的一形式。”在“交響”(通感)后面特別注出的法文是象征詩理論的關鍵詞,同時也是當時他們體驗日本社會流行的“咖啡趣味”的關鍵詞。穆木天在向郭沫若興奮地談論純粹詩歌的行間里,冒然地穿插詩人馮乃超準備退學回國開咖啡館的計劃,可見詩論和他們咖啡體驗的關系。郭沫若在《創造十年》里略帶諷刺地挖苦銀座的色香味聲音觸覺渾然一體的咖啡情調為“交響曲一樣的雞尾酒、雞尾酒一樣的交響曲”。穆木天最有名的詩《落花》就是把對戀人的想象、對自身漂泊的哀傷乃至對故鄉的向往這兩種感情“交響”而結晶為“一片一片的墜下的輕輕的白色的落花”的意象,來實現所謂內生命的統一和飛翔的。
對女性的描述也是穆木天詩里非常顯著的特征,《旅心》收錄了1923至1926年在日本寫作的詩作,詩集里反復出現“妹妹”這一戀人形象。詩人對戀人的吟唱雖然古典色彩濃厚,但對女性身體的具體想象卻是嶄新的。作為詩人追尋的希望一般的“妹妹”形象,被描述為有“你象牙雕成的兩雙足”(《淚滴》)、“桃紅的素足”(《雨后》)的女性。
眾所周知,日本女性健康的“素足”(裸足)對來自纏足的中國的留日作家而言是一個很大的沖擊,同時也是他們關注描寫的對象。1906年初到日本的周作人在魯迅下宿的家中看到赤腳忙上忙下的少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② 郁達夫《沉淪》的主人公為日本女性鮮艷的和服下露出的渾圓的白色小腿迷茫苦惱。與郁達夫相比,穆木天筆下的女性顯得和諧健康而清新。除了“妹妹”以外,他還描寫東京風景中的少女,郊外農家的胖胖的姑娘、樸素的老婦人等等,詩中滲透出將自身的詩情融入異國風景中的詩人的余裕。
伊藤虎丸在描述創造社的文學性格時指出:“對他們這些高校帝大出生的人來說,‘文學被置于和‘學問同等的地位,是在大學講堂和高等學校生活的閱讀中、以及周邊的茶店等……也就是說,是作為新的知識和教養來學習和吸收的。”③ 對上述創造社的作家而言,如果說咖啡是表達文學的現代性的一個裝置的話,那么女性也同樣可以說是現代性的表象。穆木天在東京大學攻讀最先端的法國文學,目擊地震后的廢墟和舉國的重建,他筆下的健康清新的女性形象可以說是詩人對從毀滅到重建的日本國家這一“現代性”的體驗的表象。1924年陪同泰戈爾訪問日本的徐志摩贊揚日本民族在大地震面前的強韌和樸素古風的鄉村,《沙揚娜拉》里如蓮花一般含羞的女性形象也是在大地震后的日本體驗中誕生的。與這些不同的是比穆木天早五年來到日本的郁達夫,《沉淪》里的女性對主人公來說具有強烈的性魅力,李歐梵把她們解讀為“迫害者”,“那些‘迫害者在性事方面挑逗他,叫他時常屈服于她們的誘惑之下,后來卻受盡自咎和懊悔的折磨。”④ 郁達夫筆下的女性形象所表現的是大正時期蒸蒸日上的日本的“現代性”,這對異國游子來說魅力十足卻又具有巨大的威懾力和破壞力。
女性表述,可以說承載著一個作家對現代的體驗和想象:現代性為何?中國的現代該以什么樣的姿態出現?任重道遠的文學又該如何展開?圍繞這些問題,魯迅和聞一多的女性描寫呈現出極有意義的對照。
二、魯迅的女性表述:裸體和裸體的解體
魯迅去日本留學,比郁達夫早十年左右,正置日俄戰爭前后富國強兵的明治時期。縱觀魯迅留學期間的文章,我們幾乎找不到有關女性的描述。唯一讓我們窺探到魯迅留學期間的有關女性的間接資料,是他計劃用于雜志《新生》創刊號上的封面畫(出版計劃最終受挫),那是19世紀后半期活躍于英國的著名畫家喬治·費德里科·沃茨的作品《希望》——躬身坐在懸浮于宇宙空間的地球上的“詩人”,雙眼被一塊白布蒙住,懷抱的豎琴,琴弦斷裂,僅剩隱約的一弦。以英國金發女郎為模特而創作的沃茨在繪畫上寄語:“希望不來自期待,希望令我們傾聽那僅有的一弦的樂音。” 雖然“希望”成為日后魯迅文學的重要主題,但魯迅終究沒有在他的作品里描寫出一個充滿希望的形象。魯迅在日本對“現代性”的體驗,正如促成他棄醫從文的契機——幻燈事件——一樣,是和女性表象毫無關系的。他對西洋的“現代”,并非以某種“鏡像”來接受。對他來說,和“現代”的遭遇,首先意味著發現“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的“愚弱的國民”里隱藏的中華民族的病根。在魯迅看來,中國的現代化,必須從對民族歷史的徹底否定、對國民性的毫不留情的批判開始。
在絕望的華大媽(《藥》)、單四嫂(《明天》)、豆腐西施(《故鄉》)、吳媽(《阿Q正傳》)、祥林嫂(《祝福》)等以外,魯迅也寫了為補天殫精竭慮的女媧(《補天》)。她為拯救人類而傾盡自身一切,卻被自己創造的“小東西”“冷笑”、“痛罵”。這位創造女神被描寫為裸體,非常性感誘人:“伊在這肉紅色的天地間走到海邊,全身的曲線都消融在淡玫瑰似的光海里,直到身中央才濃成一段純白。……這純白的影子在海水里動搖,仿佛全體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但伊自己并沒有見,只是不由的跪下一足,伸手掬起帶水的軟泥來,同時又揉捏幾回,便有一個和自己差不多的小東西在兩手里。”⑤但是擁有自己文明后的“小東西”們卻“累累墜墜的用什么布似的東西掛了一身,腰間又格外掛上十幾條布,頭上也罩著些不知什么,頂上是一塊烏黑的小小的長方板”,站在為補天辛勤勞作的女媧的兩腿之間向上看,遞上寫著文字的竹板,試圖用“裸裎淫佚,失德蔑禮敗度,禽獸行”等“文明”的語言規戒她。在這里,“裸體”被置于衣冠、文字、語言等傳統文化的反面,可以說是魯迅對傳統文化以及被其囚禁馴服的國民進行批判的一個文學表現。女媧最終在大風和火焰之中,為拯救人類用盡自己的一切軀殼。魯迅之后也不斷地描寫裸體,《野草》里的《復仇》、《頹敗線的顫動》的裸體像與自我犧牲的女媧相比,更是一種基于絕對的愛、以不作為和沉默的顫動進行“大復仇”的形象。以賣身養育了兒女卻被子孫鄙夷唾罵的垂老女人,在曠野里石像似赤身露體地矗立,口唇間漏出非人間所有的無詞的言語。裸體、石像、獸、無詞的語言都是反現實人間世界的象征。但是這種單純的反現實人間世界也是作者要否定超越的,他想象了一個裸體頹敗顫動的形象,石像仿佛解體,顫動如魚鱗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一同振顫,仿佛暴風雨中的荒海的波濤。垂老女人的“無詞的語言也沉默盡絕”,只有顫動如太陽光回旋在空中,如颶風奔騰于無邊的曠野。赤身露體的垂老女人是對絕望的現實的強烈否定,而頹敗顫動(解體)的裸體形象,更是對這種否定的再否定,雙重的否定,具有一種推翻眼前選擇判斷而重新設定世界的力量,也即隱含著一切的感情,人間的非人間的、愛的恨的、祝福的詛咒的,都被融化、被重新組織構建的契機。
三、聞一多的女性表述:裸體的天使和彩鳳
葛紅兵在《身體政治》里說:“把國家比作母親,是五四人的愛國主義發明,此前的國家因為是皇帝的國家,所以沒有人敢用一個女性的身體來象征之,而現代文學家和思想家則不這樣,他們把國家賦予女性身體的形象。……類似的比喻把身體和對國家政治感情、政治想象緊密地結合起來。”⑥ 年輕時的聞一多也是把祖國當著愛人來吟頌的。
和魯迅一樣,留美期間聞一多基本不描寫異國的女性,也很少在詩作里描寫當地的風景。除了描寫芝加哥潔閣森公園的《秋色》、《秋深了》等幾首外,很難找到明確的對美國風景的描述,即使在這些僅有的描述里,也總是傾訴著游子的悲傷和對祖國、家庭、母校、故人的思念。聞一多結婚后不久赴美,《紅豆篇》可以說是寫給妻子的思念篇章。“這些字你若不全認識/那也不要緊”(《紅豆篇》14),詩中的愛人是妻子同時又是祖國的意象。“假如黃昏時分/忽來了一陣雷電交加的風暴/不須怕得呀,愛人/我將緊拉著你的手/到窗口并肩坐下/我們一句話也不要講/我們只凝視著/我們自己的愛力/在天邊碰著/碰出些金箭似的光芒/炫瞎我們自己的眼睛”(《紅豆篇》40)。對這位“愛人”的形象,聞一多是這樣想象的:“我若替伊畫像/我不許一點人工的產物/污穢了伊的玉體/我并不是用畫家的肉眼/在一套曲線里看伊的美/但我要描出常夢著的伊——/一個通靈澈潔的裸體的天使!/所以為避免誤會起見/我還要叫伊這兩肩上/生出一雙翅膀來/若有人還不明白/便把伊錯認作一只彩鳳/那倒沒什么不可”(《紅豆篇》39)。對于攻讀西方繪畫的聞一多來說,“裸體的天使”,可以看作是西方文化的象征,那么,“彩鳳”當然就是他從清華學校時代起就仰慕不已的祖國文化的意象了。我們從聞一多的女性表述中可以看出,他所想象的“現代”,是文化的西方,但同時它也可以被置換成中國文化。當然,聞一多并不是復古的國粹主義者,他憑著現代的知性和感性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文化并對其寄予莫大的期待。年輕時的聞一多的“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主張,在他的女性表述里留下了清晰的印記。
魯迅反復描寫的裸體形象象征著對傳統和文化以及被之馴化的中國人國民性的批判和反抗,充滿痛苦和解體的危機,但同時也有一種強烈的負的力量。中野美代子在《作為衣裳的思想——中國人的肉體不在》里通過對中國繪畫和文學作品的分析,特別是以《禮記》中的各種繁文縟節的禮儀為例,指出中國人的思想是重視肉體的庇護者即衣裳的倫理,稱魯迅為“中國文學史里凝視肉體的最初也是最后的作家”⑦。這一說法雖然難免偏頗,但她將魯迅的一系列作品如《狂人日記》《藥》《復仇》《鑄劍》的主題解讀為肉體對衣裳的復仇,這從文化史的角度上看是有說服力的。有意思的是,她認為《禮記》的繁文縟節,在語言方面被高度精致化后,就出現了唐代文化的精華即杜甫的律詩的世界。
聞一多想象的裸體,不是用畫家的“肉眼”去描繪的“曲線”。裸體的魅力本來是“肉體”的,但卻不要用“肉”的眼去描繪——這樣的審美意識,和魯迅的充滿危機的裸體描寫呈現出強烈的對照,同時和他對古典律詩的推崇,以及后來主張的格律詩理論是一脈相通的。“戴著腳鐐跳舞”, 美麗得橫暴的感情,也要用溫柔敦厚的態度表達出來。與格律詩運動同步的還有文藝和愛國必須密切聯系在一起的主張——這些都是聞一多的困境。聞一多的女性描述,是他想象的現代性,即“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主張和文學審美觀的流露,這些飽含著矛盾和沖突。而這些矛盾和沖突是聞一多個人的,同時也可以說是現代中國新詩普遍所具有的。
四、聞一多的困境:愛國和文藝的糾纏
聞一多對中國文化的強烈關心,產生在傳統文化的空白最顯著的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學校。17歲時他寫下《論振興國學》,表達了對古學日衰的危機感。1920以后開始發表新詩,同時研究律詩的特質,認為律詩才是“純粹的中國藝術底代表” (《律詩底研究》)。留美后寫下了不少具有濃厚的中國色彩的思念祖國的詩篇,并參加信奉國家主義的大江會。
1924年春天泰戈爾訪華,文學界掀起了一股泰戈爾及哲理詩的熱潮。遠在美國的聞一多卻表示了反對。他認為哲理詩所代表的泰戈爾文學的最大的缺憾,是沒有把捉到現實,泰戈爾筆下的“少女”“新婦”“老人”等都不是生活在現實里的真人,只不過是上帝的象征。泰戈爾的文學必然失敗,因為“文學的宮殿必須建立在現實的人生底基石上” (《泰果爾批評》)。值得注意的是,1922年聞一多在《〈冬夜〉評論》里批判俞平伯的詩的“感人向善”的作用和“民眾化”主張時,就表露了他崇尚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文學觀。一年之后強調文學的現實性是和他以往的觀點相矛盾的。
對泰戈爾的批判是大江會同人的共通主張。當時和聞一多同在科羅拉多大學留學的梁實秋,在《大江季刊》創刊號上發表《詩人與國家主義》一文,用風和琴的比喻論述詩人和愛國的關系,從而展開對泰戈爾的批判:“詩人的情感原似一架寂靜的弦琴,各種不同的風吹上去的時候,便自然的發出各種不同的聲音的波圈。只要琴是完美無缺的,只要風吹上去的時候就響,那么,無論發什么樣的樂聲都是好詩。詩人給他的情人的詩是詩,贊美上帝的詩是詩,欣賞自然的詩是詩,頌揚愛國的詩是詩,宣揚世界和平的詩也是詩——這其間并無高下真偽之可分。所以詩人之鼓吹愛國,正是極自然合理的事,如其詩人的環境是迫使他不能不愛國。誰能令琴弦過風而不響呢……這里我們便不能不對印度的太戈爾表示詫異了。太戈爾的人格與詩才姑不具論,但他能在印度亡國之后,而高唱世界聯合,這就如狂飆突起,吹到琴上,而竟奏出和緩的調來,不能不說是咄咄怪事。”
在英國殖民統治下以愛和同情歌唱世界和平的泰戈爾,對國家主義者梁實秋來說是一個“超人”了。梁實秋的“風與琴”的詩人形象,是對聞一多批判泰戈爾文學沒有把握現實的主張的一個補充和注釋。聞一多所批判的是無視印度亡國現實的泰戈爾。但是,梁實秋列舉多位英國文學史上的詩人來強調愛國感情的正當性之后,在篇尾這樣寫道:“詩的價值的平衡是在其自身的藝術的優美,所以我還是篤信‘藝術為藝術的主張,我論愛國詩的時候,是論詩里的愛國思想,與詩的優劣毫無關系。” 這表露了梁實秋的矛盾和擔心:愛國會否有損于文學的藝術性?這一點也是聞一多的課題:愛國和文藝該如何聯系在一起?
標志著新格律詩誕生的《晨報·詩鐫》(下文簡稱《詩鐫》)正好創刊于“三·一八”慘案之后,這一偶然對聞一多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在創刊號上發表《愛國和文藝——紀念三月十八》,比較愛爾蘭和中國,認為相對于愛國運動和文藝復興互為因果的愛爾蘭,中國的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雖同時發生卻沒有“攜手”:“愛爾蘭的前例和我們自己的事實已經告訴我們了:這兩種運動合起來便能互收效益,分開定要兩敗俱傷。所以《詩刊》的誕生剛剛在鐵獅子胡同大流血之后,本是碰巧的;我卻希望大家要當他不是碰巧的。”
聞一多參加大江會、北京國家主義各團體聯合會的各種政治活動,并一直努力嘗試“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國劇運動”,他所追求的,就是愛國和文藝緊密聯系的文學。他批判的新詩的“民眾化”主張、《女神》的歐化、泰戈爾的哲理詩,在他看來都是文藝與愛國分離的東西。在《詩鐫》上展開的新格律詩運動,應該是一場中國的真正的國民文學復興運動。“完美的形式是完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現”——徐志摩在《詩刊弁言》中如此代言他們的主張,同時宣言:“我們相信,我們的新文藝,正如我們的民族本身一樣,有一個偉大而美麗的將來。”《詩的格律》也發表在創刊號上,里面論述“格律”重要性的論據,和他清華時代的《律詩底研究》里論證律詩為最符合抒情原理的中國詩歌形式時所持的論據基本相同。清華時代對格律的關注和研究,終于成為現實的實踐。“國家主義”、“中華文化的國家主義”和“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雖然包含著矛盾,但在新格律詩運動里將被聯系在一起。
五、新格律詩的困境:橫暴和典雅的沖突
聞一多在發表第一首新詩《西岸》之前創作過一篇童話小詩《一個小囚犯》。“我”在四月雨后的園里追趕蝴蝶,跌了一交,“涂得滿身的污泥,手被花刺兒戟破了”,被媽媽幽禁在家,從而病了,半年后終于被允許推開窗子看外面,聽到了一陣如泣如訴的歌聲:“放我出來,把那腐銹渣滓,一齊刮掉/還有一顆明星,永作你黑夜長途底向導”。“我”喜歡這歌,四面尋找,卻看不到人,求媽媽道:如果有小孩陪我不捉蝴蝶不踏污泥,好好生生的玩耍,還唱嘹亮的歌兒,你也不放我出去嗎?媽媽說:可以放你,但到哪兒找到這樣一個伴兒呢?從此以后“我”便天天站在窗口喊:“唱歌的人兒,我們倆一塊兒出來吧!” 這是一篇不引人注目的作品,但從其中可以窺探到聞一多對“美”的追求的激情和對該如何“唱歌”的最初的焦慮。被囚禁的“我”渴望大自然的美麗、自由,卻又擔心大自然的橫暴(污泥和刺兒),要尋找和自己一起“好好生生的玩耍”(歌唱)的伙伴。這首詩并沒有發表,后被編入《真我集》。相反,可以說續寫了《一個小囚犯》的《美與愛》收入《紅燭》刊行。《美與愛》里,被囚禁的“心鳥”終于撞斷監牢的鐵檻尋找“無聲的天樂”,卻最終嗓子啞了,眼睛瞎了,心也灰了,為愛和美付出了代價。《美與愛》表達的是對唯美藝術的傾倒和激情,是年輕的聞一多的文學立場,但并未發表的《一個小囚犯》里述說的對美(精神)的橫暴的焦慮,是一個創作者的真實的焦慮——該如何寫,以什么形式?
1922年11月,聞一多在《〈冬夜〉評論》里批評俞平伯的詩的民眾化主張,認為幻想和情感是詩的最重要的成分,“《冬夜》里大部分的情感是用理智底方法強造的,所以是第二流的情感”。同時,他也批判俞平伯的言語的粗俗,認為作詩應該雍容沖雅“溫柔敦厚”。可見聞一多對感情和語言(形式)表達的要求的矛盾。聞一多自己是一個情感激烈的詩人,他在《愛國與文藝——紀念三月十八》里描述了和梁實秋“風與琴”相同的詩人形象:“詩人應該是一張留聲機的片子,鋼針一碰著他就響。” 但當如留聲機片子一碰就響的詩人朱湘脫離《詩鐫》時,聞一多氣憤地寫道:“孔子教小子,教伯魚的話,正如孔子的一切教訓,在這年頭,都是犯忌的。依孔子的見解,詩的靈魂是要‘溫柔敦厚的。但是在這年頭,這四個字千萬說不得,說出了,便證明你是一個弱者。當一個弱者是極寒磣的,特別是在這一個橫蠻的時代。在這時代里,連詩人也變橫蠻了,做詩不過是用比較斯文的方法來施行橫蠻的伎倆。”⑧
“溫柔敦厚”是《禮記》里孔子的話,清初被作為理想的詩的條件之一。沈德潛提倡“格調說”,一方面崇尚詩的風格和音調的典雅,一方面以“溫柔敦厚”為口號,主張詩的道德和政治的效用,力圖復活漢代儒家傳統詩觀。聞一多批判俞平伯的“令人感動引人向上”的民眾化藝術,他所意味的“溫柔敦厚”應該是指典雅的音調和語言以及柔和篤實的態度,這也是他所提倡的具有整齊的句法和調和的音節的格律詩的境地。
有研究者在分析《一個小囚犯》時指出:“聞一多在他的詩中始終擺脫不掉的冷靜、克制、精心修飾的一面。……形式在聞一多身上卻似乎成了一種先驗的本體,一種意志化了的力量……他在理智上一直追求一種優雅和諧的貴族化的古典美,而在情感和無意識之中卻更為企慕崇高的現代風格。”⑨ 這一分析十分恰當。1927年聞一多經歷了回國后中國現實的洗禮,對該如何把握和表達他一直熱衷的中國文化這樣質疑:“啊,橫暴的威靈,你降伏了我/……五千多年的記憶,你不要動/如今我只問怎樣抱得緊你……/你是那樣的蠻橫,那樣的美麗!”奔放的激情和對典雅的形式的追求最終陷入困境,聞一多停止寫詩,開始了對古典文化的長期的潛心研究。
注釋:
① 穆木天:《道上的話》,《洪水》1926年第18期。
② 周作人:《最初的印象》,《知堂回想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頁。
③ 伊藤虎丸:《問題としての創造社——日本文學との関係から》,《創造社資料別巻 創造社研究》,アジア出版社1979年版,第276頁。
④ 李歐梵:《郁達夫:自我的幻像》,《李歐梵自選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頁。
⑤ 魯迅:《故事新編》,《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346頁。
⑥ 葛紅兵:《身體政治:解讀20世紀中國文學》,臺北新銳文創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頁。
⑦ 中野美代子:《悪魔のいない文學 中國の小説と絵畫》,朝日新聞出版社1977年版,第149頁。
⑧ 聞一多:《詩人的橫蠻》,《聞一多全集》第2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頁。
⑨ 王富仁編:《聞一多名作欣賞》,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第456—457頁。
作者簡介:鄧捷,日本關東學院大學教授,日本橫濱,2368501。
(責任編輯 劉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