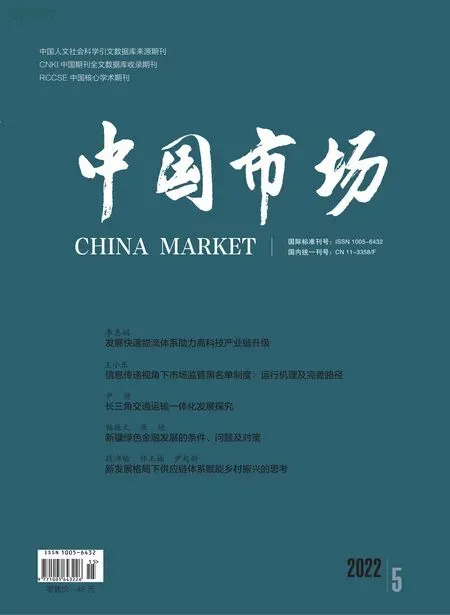我國與鄰國專屬經濟區漁業資源共同開發芻議
吳曉明+柳維睿
[摘 要]隨著“一帶一路”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海洋強國”戰略實踐的不斷深入,爭議區漁業資源的共同開發問題越發重要。在新的背景下,各國應當更加行之有效地處理專屬經濟區共同開發所涉及的法律問題,以達到互利共贏的效果,形成正和博弈的局面。
[關鍵詞]專屬經濟區;漁業資源;共同開發;漁業管理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5.014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海洋法公約》的制定,“專屬經濟區”的概念隨之產生,而且在全世界范圍內為廣大國家所迅速接受。《海洋法公約》中規定的200海里專屬經濟區的劃定標準,[1]隨著全球一百多個國家的不斷加入,漸漸成為全球范圍內各國進一步明確海洋權利的新標準,迄今為止已有一百多個國家先后設定專屬經濟區,并有十余個國家先后設立了本國的專屬漁區,為本國的漁業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制度基礎。
1996年5月,我國加入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隨之不久,于1998年我國制定了《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法》,針對《海洋法公約》中對專屬經濟區的規定,全面考量我國現實情況,對我國專屬經濟區內以捕魚權為代表的各項權利加以明確規定。我國的海上鄰國眾多,且大部分都同樣宣告了自己在本國200海里專屬經濟區的各項權利,包括東海附近相鄰的日本、韓國、朝鮮以及南海區域附近的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文萊、印度尼西亞等國家。由于海洋區域范圍形狀紛繁復雜,各國先后劃定200海里專屬經濟區的范圍也存在大大小小的重疊部分,故而原本我國與鄰國漁民“自由”捕魚的區域發生了變化。由于部分漁民存在文化水平低等問題,往往在捕魚過程中因不了解專屬經濟區的具體范圍或重疊范圍而與鄰國產生捕魚糾紛,同時我國與鄰國在捕魚權和海上執法權方面的制度欠缺,也導致諸多爭議的產生。
1 國家在專屬經濟區內的權利與義務
由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曾有過明確規定,“一國在其領海界線之外,既可選擇專屬經濟區的安排,也可選擇專屬漁區的安排。”[2]所以現實情況中我們經常看到,很多國家并沒有設定本國的專屬經濟區,但是設定了本國的專屬漁區。然而《海洋法公約》中也明確規定,一國在其專屬漁區內的權利范圍不得超越其在專屬經濟區內的權利范圍。
根據《海洋法公約》的規定,一國在專屬經濟區內享有包括勘探、開發海底及其上覆水域的生物及非生物資源的權利,與之相對應,也具有養護和管理的權利和義務。[3]漁業資源作為最主要的生物資源之一,即成為了各國紛紛開發利用的焦點。根據《海洋法公約》的相關要求,很多沿海國家紛紛制定相關法律,禁止或限制其他國家漁民在其專屬經濟區內捕撈魚類,并對別國在本國專屬經濟區內的可捕量、可捕魚類及漁網密度等具體問題進行了詳細規定。
2 我國與鄰國漁業資源共同開發現狀及存在的法律問題
縱觀歷史,我國與鄰國的漁業合作開始較早,于1980年前后就有過先例。迄今為止,也積累了相當多的理論實踐經驗。
關于“共同開發”理論的具體概念,一般是指國家間通過協議的方式,共同對本國與其他當事國之間有爭議區域內的資源進行合作開發的行為活動。鄧小平同志在1986年會見菲律賓副總統勞雷爾時,談及南沙問題曾說到,對于爭議性問題可以以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國家主席楊尚昆在1990年訪問印度尼西亞時也曾具體闡述過我國在南海問題上“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立場。[4]雖然“共同開發”制度在現實實踐中還存在很多問題,可供借鑒并適合我國現實國情的經驗也有限,然而這些并不妨礙我國為長遠發展和綜合利益考慮,不斷與鄰國在專屬經濟區內就共同開發問題上不斷展開嘗試并努力實踐。中國與越南于2000年訂立的北部灣協定就是漁業資源共同開發的典型成功案例,就此項協定的內容,中越雙方對北部灣漁業資源開展了廣泛的合作開發,取得了較為可觀的成效。
隨著共同開發活動的不斷開展和深入,我國與鄰國就專屬經濟區內漁業資源合作中所產生的問題也進行過反思,其中存在的法律問題主要包括兩方面,即雙邊協定本身的問題和漁業開發過程中的海上執法問題。
我國與鄰國現已訂立的雙邊漁業協議中目前存在著多方面的問題,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協議調整的對象只包括當事雙方國家,對于漁業開發中可能存在的第三方國家利益難以得到保障,其他國家對于該海域漁業權等相關權利的侵犯所引起的相關爭端也難以得到規制和解決。第二,協議調整的范圍和效力往往僅局限于兩國具有明確主權的海域范圍,對于專屬經濟區以外,兩國之間的爭議海域,協議中可能存在空白。第三,漁業共同開發的相關機制不夠完善,以雙方國家派代表和專家組建漁業管理委員會等形式居多,缺乏其他創新形式,遇到問題時往往只能通過協商等方式,缺乏其他創新模式。第四,雙邊協議中往往缺少對漁業合作中法律適用及管轄權的具體規定,相關的空白導致具體漁業共同開發實踐中新問題的不斷涌現。
在海上執法方面,我國主要以邊防海警、海關、海事、漁政、海監五大部門作為執法主體。但由于各部門之間的權力范圍存在重疊,劃分不清,執法的過程中也存在缺位的現象,導致我國海上執法中權屬不清的狀況時有發生。[4]在同鄰國進行漁業合作的過程中,執法工作應當為開發活動提供相關的安全保障,不但我國內部執法體系可能存在混亂,同時在與鄰國合作過程中可能也與鄰國法律所規定的海上執法權存在沖突,因而帶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為確保我國與鄰國在專屬經濟區內漁業合作的順利開展,有必要從規劃好我國內部海上執法體系方面入手,完善海上執法行為,為保障我國與鄰國漁民在合理開展捕撈活動時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3 解決我國與鄰國漁業合作中法律問題的相關對策
3.1 完善雙邊漁業合作協議
我國與鄰國在進行漁業合作之前,應當進行充分的磋商。磋商的方式可以以各國派出專家和代表組成“漁業委員會”的形式,也可以直接邀請第三方專業性的漁業組織一同磋商,以提高合作的專業度和合作效率。同時,在制定雙邊協議之時,也應當充分考慮不同海域的不同特點,包括其中分布鄰國的相關漁業法律制度,確定該海域上各國所主張管轄權的類型。在解決相關漁業爭議和共同開發中對于分別或綜合適用法律和協議存在效力的不同情況加以明確規定。不能忽視的是,針對存在主權爭議的海域,應當秉持“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原則,在漁業開發的過程中要保證不侵犯彼此主權,維護兩國國家和國民的安全。另外,當兩國相鄰海域除劃定的200海里專屬經濟區外,仍有其他爭議捕魚區時,應當充分考慮該地區現實漁權情況,是否有第三國已經主張并在此進行過周期性的捕魚活動,如果確定不存在相關糾紛,則應將該區域的規定空白進行填補,合理規劃兩國對該海域的具體合作捕魚活動。
3.2 完善我國海上執法體系并加強海上聯合執法
漁民的人身安全不僅是漁業開發順利進行的保障,也是一國理應保護本國國民的義務。面對當前形勢,我國與鄰國專屬經濟區及附近海域存在著諸多濫捕漁民,危害航道安全的現象,提高海上執法的執行力度,規范海上執法隊伍建設迫在眉睫。面對我國海上執法“五龍鬧海”的現存局面,可以合理整合相關人員,使邊防海警的執法方式更加趨于半軍事化,提高執法效率。對海關、海監、海事、漁政部門的管理,可以由上級部門派出領導小組進行統一規劃,安排相關執法行動。當威脅航道安全的行為出現時,應當健全及時報告的相關制度,提高海上執法的效率。我國與鄰國也可以在綜合考量雙方警力、物力等條件下,適當開展執法合作,共同保護相鄰爭議海域的航道安全,從而推動漁業合作的發展。
專屬經濟區海域漁業合作中所存在的相關法律問題還需要不斷探索并完善解決方式。相信隨著我國和鄰國漁業的不斷發展,可以更加規范、有序地開展更為廣泛的漁業合作。
參考文獻:
[1]郭文路,黃碩琳.南海爭端與南海漁業資源區域合作管理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7.
[2]范曉婷.對“共同開發”問題的現實思考[J].海洋開發,2015(5).
[3]葉超.南海漁業開發與合作管理研究綜述[C]//張曉東,2014年度上海市海洋湖沼學會年會暨學術年會論文集.上海市海洋湖沼學會,2014:2-8.
[4]佟岳男.淺析沿海國對專屬經濟區漁業資源的專屬權利[D].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