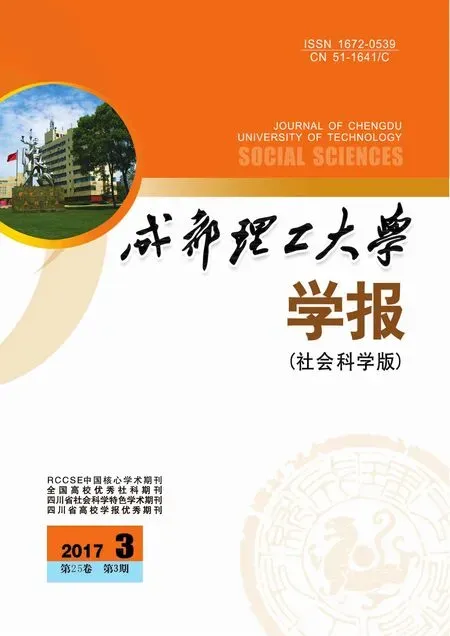實證視野下的不作為犯罪研究
金飛艷
(北京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871)
實證視野下的不作為犯罪研究
金飛艷
(北京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871)
從司法實踐來看,不作為犯的判決中,不純正不作為犯的數(shù)量居多。雖然在理論上,所有的犯罪都可以通過不作為實施,但司法實踐中對不作為犯的認定上缺乏等價性的考察,不當擴張了入罪范圍。在涉及多人的不作為犯判決中,認定為同時正犯和共同犯罪中主犯的情形居多,認定為從犯的情形較少,這是因為不作為共犯理論中,原則正犯說存在缺陷,導致實踐中不作為的共同犯罪一般認定為主犯。司法實踐中對不作為的未遂在認定上較為謹慎,一般要求不作為的成立以造成實害后果為前提,這樣的做法較為妥當。
實證;不作為;不純正不作為;共同犯罪;未遂
一、研究背景及方法
不作為是刑法理論中最混亂、最黑暗的迷思。從不作為犯的處罰依據(jù),到不作為犯的共犯問題,再到不作為犯的未完成形態(tài),均存在理論上的短兵相接。遺憾的是,針對不作為犯罪的現(xiàn)有文獻基本處于理論探討,卻與實務有所脫嵌。正如有學者對目的構(gòu)成教義學體系的描述:它是向外部開放的管道,經(jīng)由這一管道,來自體系之外的政策需求方面的信息得以反饋至體系內(nèi)部,為體系的要素所知悉,并按目的指向調(diào)整自身的結(jié)構(gòu)和功能。這樣的信息通過目的的管道傳遞至教義學體系的各個角落,驅(qū)使體系之內(nèi)的各個組成要素做出相應構(gòu)造上的調(diào)整[1]。斯言誠哉!理論中的銖量寸度應當對實踐有所陶染,實踐中的做法也應當成為理論可資利用的素材。本文從實證角度出發(fā),針對不作為犯的處罰依據(jù)、共犯地位、未完成形態(tài)等諸多問題提出一管之見。
為了探究司法實踐中對于不作為的處理,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wǎng)上隨機選取近10年以來全國各地43份不作為犯的判決。其中涉及多人犯罪17起,累犯或受過刑罰處罰的2起。在不作為犯的確定上,筆者采用形式和實質(zhì)的雙重標準。前者例如,判決書中提到被告人有作為義務而未履行的,成立不作為犯。后者例如,遺棄罪、拒不執(zhí)行判決、裁定罪只能由不作為構(gòu)成,因而成立不作為犯
二、不作為犯的類型
(一)不作為犯的樣本統(tǒng)計
筆者按照通說觀點,將不作為犯分為純正不作為犯與不純正不作為犯。前者是指分則明文規(guī)定了保證人與不作為內(nèi)容的不作為犯,后者是指分則并未明文規(guī)定保證人地位與不作為內(nèi)容,但行為人以不作為實施通常由作為實施的構(gòu)成要件的犯罪[2]。前者只能由不作為的形式構(gòu)成,例如遺棄罪、拒不執(zhí)行判決、裁定罪,后者既可以由不作為的形式構(gòu)成又可以通過作為的方式構(gòu)成,例如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筆者以此為依據(jù)劃分樣本進行分析(表1、圖1)。
表1 不作為犯罪類型統(tǒng)計表

不作為犯罪類型頻數(shù)/件頻率/%純正不作為犯1125.58不純正不作為犯3274.42

圖1 不作為犯罪類型統(tǒng)計圖
樣本中的純正不作為犯罪,包括遺棄罪、玩忽職守罪、丟失槍支不報罪(表2、圖2);不純正不作為犯包括故意殺人罪、強奸罪、非法拘禁罪、詐騙罪、盜竊罪、徇私枉法罪等,筆者樣本中的不純正不作為犯劃分為人身犯罪、財產(chǎn)犯罪、瀆職犯罪和其他犯罪四大類(表3、圖3)。

表2 純正不作為罪名統(tǒng)計表

圖2 純正不作為罪名統(tǒng)計圖

罪名頻數(shù)/件頻率/%人身犯罪1134.38財產(chǎn)犯罪721.88瀆職犯罪825.00其他犯罪618.75

圖3 不純正不作為罪名統(tǒng)計圖
由樣本可以大致推知,在司法實踐中,不作為犯罪的判決以不純正不作為為主,比例高達74.42%,純正不作為僅占25.58%,數(shù)量上僅為前者的三分之一。在純正不作為犯的判決中罪名較為單一,只有遺棄罪、玩忽職守罪、丟失槍支不報罪三類,其中玩忽職守罪所占比例約三分之二。相比而言,不純正不作為犯中認定罪名多樣,其中人身犯罪所占比例最高,達到34.88%;瀆職犯罪其次,比例為25%;財產(chǎn)犯罪再次,所占比例21.88%。在成立的不純正不作為罪名中,以故意犯罪為絕大多數(shù),僅有一例過失致人死亡罪屬于過失犯罪。
(二)不作為犯的處罰根據(jù)檢視
實證研究的結(jié)果表明,不僅純正不作為犯在不作為犯中占大多數(shù),而且在實踐中,幾乎所有可以通過作為實施的犯罪均可以通過不作為完成。但問題在于,與純正不作為不同的是,不純正不作為犯的處罰并非由《刑法》分則明文規(guī)定。正如有學者一語道破的:不真正不作為犯,不問古今東西,均是基于民眾樸素的法感情中所具有的經(jīng)驗的、刑事政策的要求[3]。
不純正不作為犯的處罰是否違反罪刑法定?德國學者阿明·考夫曼指出,處罰不純正不作為犯與罪刑法定原則相悖。他認為,規(guī)范分為禁止性規(guī)范和命令性規(guī)范,前者要求不實施一定行為,后者要求實施一定行為。構(gòu)成要件中只應當保護禁止性規(guī)范。因而將不作為的行為適用禁止性規(guī)范的條款,是類推解釋,違反了“法無明文不為罪”的原則[4]。例如,故意殺人罪的設置只是在于禁止故意殺人的行為,而非表明要求人們救助別人的命令性規(guī)范。在日本,也有學者支持這一看法。例如,金澤文雄指出,考慮到罪刑法定,應當否定對不真正不作為的處罰;香川達夫則認為,只有從正面肯定類推解釋,才能肯定對不真正不作為的處罰[5]。
然而從各國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來看,幾乎所有國家都對不純正不作為犯進行處罰,所不同的只是處罰的依據(jù)。雙重規(guī)范說認為,不作為犯既違反了命令規(guī)范,也違反了禁止規(guī)范。例如日高義博認定,刑法規(guī)范是審判規(guī)范和行為規(guī)范的復合體,不作為犯違反的是命令規(guī)范和行為規(guī)范,而實現(xiàn)的是作為裁判規(guī)范的作為犯的犯罪構(gòu)成要件[6]。等價性解釋論認為,不作為的違法內(nèi)容和責任內(nèi)容與作為等價,例如,有學者認為,不作為實施的犯罪和作為實施的犯罪具有等價的情況下,不真正不作為犯才能適用作為犯的犯罪構(gòu)成要件[7]。開放的構(gòu)成要件理論認為,從構(gòu)成要件的角度看,不真正不作為犯作為的義務并未規(guī)定,屬于立法者未能詳細描述的構(gòu)成要件要素,因此需要法官在適用時根據(jù)法律解釋原理予以填充,不作為犯在構(gòu)造上具有開放性[8]。
在筆者看來,“禁止殺人”背后保護的法益是人的生命,依評價規(guī)范角度,不論以作為抑或不作為的方式導致他人死亡,都可以認為侵犯生命法益,因而具有違法性[2]152。事實上,在構(gòu)成要件的理解上應當采用規(guī)范的視角,例如,剝奪他人生命的方法既可以是火燒、水淹,也可以說是刀砍、繩勒;既可以是作為,也可以是不作為;既可以是直接正犯,也可以是間接正犯。機械理解文義,認為構(gòu)成要件中僅包括作為的內(nèi)容,就可能陷入“白馬非馬”的困境之中。
(三)不作為犯的等價性考察
確定處罰不作為的合法性之后,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是否所有能夠以作為方式實施的犯罪均可以通過不作為完成。
例1:某日,被告人蔡某于自行車用品店選購一輛捷安特牌ATX 830系列的山地車,蔡某與老板伍某還價后商定4700元的價格,老板娘洪某正好回到店里。伍某對洪某說:“你給這位顧客開票,4700元,ATX 830。”伍某說罷開始忙著修車。洪某領蔡某進里屋開好發(fā)票后,以為伍某已經(jīng)收了款便沒有收款。蔡某覺察到了兩人的誤會,于是徑直將山地車騎走,伍某和洪某均未加阻攔[9]。本案中,有學者認為應當認定為不作為的詐騙罪[10],但筆者認為該觀點不當擴大了不作為的成立范圍。
《德國刑法典》13條規(guī)定了不作為與作為的等價性[11]。在筆者看來,在不作為犯的判斷上,必須將違反義務的行為與成立罪名的輕重相衡量,才能得出妥當?shù)慕Y(jié)論。再從邏輯上考察,所有的犯罪均可以由不作為的方式構(gòu)成。例如,婦女在黑夜中誤以為行為人系其夫與之發(fā)生性交,行為人不予制止的,成立不作為的強奸。再如,所有權(quán)人的寵物自發(fā)進入行為人家中,行為人不主動返還的,成立不作為的盜竊。但倘若如此認為所有的犯罪均可以由不作為構(gòu)成,便不當擴大了不作為犯的成立范圍。事實上,違反義務的行為必須與成立罪名的輕重相適應。例如,《消防法》44條規(guī)定了公民發(fā)現(xiàn)火災的報警義務,但公民發(fā)現(xiàn)火災并未報警的,不能認為成立不作為的放火罪,因為違反《消防法》義務的行為與放火罪之間并不等價。再如,消防人員有滅火的義務而不履行該義務的,并不必然成立放火罪,而可能成立玩忽職守罪或其他犯罪[5]161,因為消防人員違反義務的行為與放火罪之間不具有等價性。
據(jù)此,筆者不否認詐騙罪可以由不作為的方式構(gòu)成,但對等價性的考察必不可少。正如有學者所說,相對人知道真相即不會處分財產(chǎn)的情況下,具有告知義務的行為人不告知真相的不作為行為,是導致他人陷入或維持錯誤的原因力,當然屬于欺騙行為,當倘若認為所有的作為犯罪都可以通過不作為的樣態(tài)實現(xiàn),就不妥當了[12]。例如在例1中,行為人違反的是民事領域,即當交易對方陷入錯誤認識時,行為人沒有基于誠實信用原則履行告知實情的義務。顯然,基于誠實守信的告知義務具有道德義務的征表,與詐騙罪不具等價性。因此本案不宜認定為不作為的詐騙罪。
例2:被告人張某和李某兩人談戀愛一年之久,多次發(fā)生性關系,并未辦結(jié)婚登記。2002年8月,因家庭瑣事,張某向李某提出分手,李某傷心欲絕,手持毒藥到張某宿舍,聲稱如果張某要堅持分手就服藥自殺。張某說:“你想死就死吧,和我沒關系。”李某當即服下毒藥,張某見狀離開。公訴機關以故意殺人罪對被告人提起公訴,法院最終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告有期徒刑六年[13]。本案中,被告人與被害人之間并無扶養(yǎng)義務,被告人違反的僅是道德義務,與故意殺人罪的作為行為并不具有等價性。因此筆者認為,法院將被告人認定為故意殺人罪的判決值得商榷。
綜上所述,從實證結(jié)果來看,司法實踐中不純正不作為犯的認定在不作為犯中占大部分;加之對等價性考察的缺位,使得不純正不作為犯的成立范圍過寬,罪刑法定的底線與陣地被鯨吞蠶食。正如有學者所述,不作為犯是“無行為則無犯罪”原則的一個后門,而實踐中對其的看守并不嚴格[14]。因此,將理論中的等價性考察應用于司法實踐之中,是避免司法專斷的重要方面。
三、不作為犯的共犯地位
(一)相關樣本統(tǒng)計
筆者將樣本分為單獨犯、同時犯、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共同犯罪中的從犯四種類型,進行分析(表4、圖4)。
表4 不作為犯罪人數(shù)及地位

犯罪類型頻數(shù)/件頻率/%單獨犯2660.47同時犯818.60主犯613.95從犯36.98

圖4 不作為犯罪人數(shù)及地位
由樣本可以大致推知,在司法實踐中,不作為犯判決以單獨犯為主,所占比例高達60.47%;同時犯的情形其次,占18.6%;成立共同犯罪中主犯的情形占全部不作為犯罪的13.95%;成立共同犯罪中從犯的情形在全部不作為犯罪中所占比例6.98%。
在涉及多人的不作為犯罪中,有兩個問題值得關注,一是不作為參與的犯罪成立同時犯,抑或共同犯罪?二是如果成立共同犯罪,各參與人在其中的地位與作用如何認定?
(二)不作為的共犯問題爭訟
針對第一個問題,德日刑法理論存在共犯說與同時犯說的爭議。共同犯罪說者,如德國學者瑪拉哈(Maunach)認為,在兩親使孩子餓死的場合,構(gòu)成不作為的共同正犯。我國學者也認為,在此場合下,每個行為人要達成既遂必須依賴于對方的不作為,只有全部行為人共同的不作為才能完成犯罪[15]。“同時犯說”的支持者從另一條進路將不作為的行為入罪,如日本學者神山敏雄認為,復數(shù)的保證人共同決定不防止一定結(jié)果發(fā)生時,如果個人能夠單獨阻止結(jié)果的發(fā)生,則共同意志下的不作為也不能等價于共犯條件,因此,按照同時犯處理,沒有必要認定為共同正犯[16]。
針對第二個問題,更是存在多種理論的聚訟。以目的行為論為代表的純粹存在論者認為,與作為不同,不作為不是行為,與結(jié)果之間也不存在因果關系,對結(jié)果也不存在對目的的操縱[17]。因此,不作為無法改變外部世界。否則在不作為行為和結(jié)果之間介入了他人的作為犯罪時成立共犯,而在介入的是自然力的情況下卻是正犯,這樣的結(jié)論并不妥當[18]。因此,目的行為論的框架之下,不作為原則上均是正犯。正如考夫曼指出的,通過不作為對不作為的參與并不存在,不作為之間即不存在共同實行的意思,也不存在共同實行的事實,不能成立共同正犯[19]。羅克辛教授雖然并非純粹存在論的衛(wèi)道士,但在不作為犯的問題上也主張原則正犯說。他認為,不作為犯和作為犯中同樣意義上的犯罪支配無法被確定,因而什么都沒做的人不可能支配事件經(jīng)過,對事件經(jīng)過的控制性駕馭,以積極行為為前提,而不作為犯恰好是欠缺的。因此,需要通過義務犯的概念將不作為犯認定為正犯[20]。
與純粹的存在論相反的是純粹規(guī)范論的觀點。Jakobs認為,作為與不作為的區(qū)分不具意義,重要的是支配犯與義務犯的劃界。根據(jù)Jakobs的看法,支配犯是由于對組織領域有管轄的所有人,組織了一個犯罪。在組織領域內(nèi),基本的組織行為就是犯罪支配[21]。與支配犯不同,義務犯是基于制度管轄的犯罪,因而具有一身專屬性,包括夫妻關系、親子關系等,義務犯的參與者通常被評價為正犯[22]。例如,眼看女兒被強奸而不予救助的父親成立強奸罪的正犯而非共犯。
處于純粹存在論與純粹規(guī)范論之間的觀點對不作為共犯地位的劃分上也是言人人殊,主要理論有機能二分說、重要作用說和結(jié)果原因支配說。
機能二分說由考夫曼為了解決義務來源的問題提出,德國學者Schr?der首次將其應用于不作為正犯與共犯的區(qū)分上,而后得到了Herzberg等學者的發(fā)揚[23]。機能二分說將作為義務分為兩類:保護保證人的作為義務是指對被保護者實施一定作為行為以保護其法益不受侵害的義務,例如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扶養(yǎng)義務;而監(jiān)督保證人的作為義務是指監(jiān)督特定危險源不對他人造成侵害的義務,例如飼主對飼養(yǎng)動物有監(jiān)督其不侵害他人的義務[24]。違反保護保證人的作為義務成立正犯,而違反監(jiān)督保證人的作為義務成立共犯。
重要作用說認為,不作為犯的共犯地位應當根據(jù)作用力的大小加以區(qū)分。例如,在母親殺害小孩時父親不予阻止的場合,因為男性與女性力量上的懸殊,父親以正犯論,母親以共犯論。在父親殺害小孩時母親不予阻止的場合,結(jié)論也應當一致[25]。
許乃曼教授的結(jié)果原因支配說為作為犯與不作為犯創(chuàng)設了共同的“支配”概念。作為犯中的支配包括羅克辛所說的直接正犯的行為支配、間接正犯的意志支配、共同正犯的功能性支配;不作為犯中的保證人支配包括保護支配與監(jiān)督支配。保護支配是對法益無助性的支配,包括基于生活共同體、危險共同體和對無助法益的支配,例如保姆對看顧對象的義務。監(jiān)督支配是對一項重要的結(jié)果肇因的支配,包括對危險物、危險人、危險工作的支配,如飼主對動物傷害他人的制止義務[26]。形成保護支配的不作為犯是正犯;而形成監(jiān)督支配的不作為犯是共犯。
(三)實務中的“原則共犯說”與共犯理論相抵牾
筆者認為,不論如何界分不作為的共犯抑或正犯地位,將不作為犯一律視為共犯值得商榷。純粹的存在論忽視了刑法規(guī)范的評價,對不作為的地位確立起決定作用的不是承認所謂因果力有無這樣的結(jié)構(gòu)差異,而是超越作為與不作為存在結(jié)構(gòu)的規(guī)范性正犯原理[27]。并且,將不作為一律認定為正犯會造成體系上的不協(xié)調(diào)。例如,A正在被甲殺害,A的父親袖手旁觀,A的母親為甲遞刀。如果按照原則正犯說的觀點,A的父親系不作為的正犯,A的母親系作為的幫助犯。如此一來,什么都沒做的人處罰更重,這顯然不合適。
我國的判決中并不區(qū)分正犯與共犯,但從主犯與從犯地位的劃定上可以看出司法實踐的態(tài)度。實踐中將不作為認定為從犯的情形比例不高;而認定為同時正犯抑或共同犯罪中主犯,以主犯處罰的情形占大多數(shù)。但這樣的做法值得商榷。
例3:2009年12月31日凌晨,被告人李文凱駕駛出租車,載同村人李文臣,在溫州火車站附近攬客。被害人上車后,遭李文臣強暴。在此期間,被害人多次向被告人李文凱求救,要求其停車。被告人李文凱出言勸阻,但遭李文臣威脅。李文凱便按李文臣要求繞道行駛,本來10分鐘的路程開了30分鐘,使李文臣犯罪得逞。2011年5月20日,溫州鹿城法院認為,李文凱的行為客觀上為李文臣的犯罪行為提供便利,判處被告人成立強奸罪的脅從犯,有期徒刑2年[28]。
本案中,被告人李文凱基于對法益的危險發(fā)生領域的支配產(chǎn)生的阻止義務成立不作為犯[2]159。但在共犯地位上看,應當認定為不作為的幫助犯。如果根據(jù)“機能二分說”,被告人李文凱違反的是監(jiān)督保證人的作為義務,因而成立幫助犯。如果根據(jù)“重要說”,被告人李文凱在整個強奸犯罪的實施中并未起到重要作用,不宜認定為正犯。如果根據(jù)“結(jié)果原因支配說”,被告人李文凱既不具有對法益無助性的支配義務,也不具備結(jié)果肇因的支配義務,因而只能成立幫助犯。可見,根據(jù)區(qū)分不作為正犯與共犯的觀點,此類案件都應當作為不作為的幫助犯加以處理,倘若一律認定為正犯,便是不當擴大了處罰的范圍與法定刑的適用。
事實上,基于不作為共犯理論的龐雜,德國與日本的司法實踐中對此問題的解決也并未涇渭分明。例如,同樣是不救助他人自殺,如果認為有處罰必要,聯(lián)邦最高法院就會判決成立不作為殺人罪的正犯;如果認為沒有處罰的必要,就會判決不成立犯罪[29]。而我國司法實踐中,理論更為混亂,所以一般對不作為的犯罪就作為正犯處理,但這樣的處理方式值得商榷。事實上,不作為犯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必須綜合考量行為人所起作用、作為義務的大小、罪名的輕重加以確定。
四、不作為犯的未完成形態(tài)
不作為犯是否存在未完成形態(tài)?從筆者選取的43個樣本來看,不作為的行為均造成了實害結(jié)果。人身犯罪中,11個樣本均造成了被害人死亡或其他的后果;7個樣本財產(chǎn)犯罪中,均造成了財產(chǎn)損失;瀆職犯罪中,8個樣本均造成了損害結(jié)果;其他類型的犯罪亦是如此(表5)。
表5 不純正不作為罪名統(tǒng)計表

罪名頻數(shù)(件)既遂/件既遂所占比例/%人身犯罪1111100財產(chǎn)犯罪77100瀆職犯罪88100其他犯罪66100
德國的刑事立法中承認不作為的行為犯[31]。所謂“不作為的行為犯”,是指“法律對不作為做出了規(guī)定,要么依據(jù)沒有制止其發(fā)生的結(jié)果,要么是對不作為的行為本身做出了詳盡的規(guī)定”[30]。但是,正如有學者所言,不作為犯的未完成形態(tài)在認定上具有極大的延展性[32]。例如,母親打算不給孩子喂奶使其餓死,而后又放棄該念頭的,能否成立不作為故意殺人罪的中止犯?筆者認為,問題的結(jié)論與不作為著手時間的認定密不可分,關于著手的時間點可以大致分為主觀說與客觀說兩種。
主觀說認為,在行為人具有作為可能性的最初階段,即可以認定著手。按照該觀點,母親首次不給嬰兒喂奶,即是故意殺人罪的著手,之后放棄犯罪的,也成立故意殺人罪的中止。這種觀點顯然不當提前了不作為犯的認定時間[2]320。目前占主流的觀點是客觀說。該說以危險程度認定不作為的著手:若存在結(jié)果發(fā)生的危險,只要保證人放棄阻止結(jié)果的最初機會,便成立未遂;倘若危險不直接,則當保證人盡管面臨嚴重危險而保持無所作為,或者放棄實施救助干預或聽任時態(tài)發(fā)展,著手才算開始[33]。所以,當法益面臨緊迫并具體的危險時,行為人仍然不作為導致危險可能發(fā)生的,就是不真正不作為犯的著手[34]。質(zhì)言之,不履行作為義務同時導致被害法益面臨現(xiàn)實危險的時點,就是不作為的著手[35]。例如,母親決意不扶養(yǎng)嬰兒使其死亡,后放棄該念頭的,不必然成立不作為故意殺人罪的中止,只有當不扶養(yǎng)的行為造成現(xiàn)實、緊迫危險時才能認定不作為的成立。
根據(jù)實證結(jié)果來看,司法實踐中不純正不作為在認定上往往比較謹慎。在選取的樣本中,均以造成危害結(jié)果為不作為犯成立的必要條件。事實上,不作為立法的增多與風險社會的形成密不可分。正如有學者所說,風險社會帶來了行為范疇的拓展:刑法中的行為以作為為原型,例外地包括一些不作為,還出現(xiàn)“持有”這種特殊的行為樣態(tài)[36]。可以說,不作為犯的立法與否更多是出于形勢政策因素的考量。因此,在不作為場合的著手認定上應當有所寬緩,尤其在不作為的現(xiàn)實危險性并不如作為犯緊迫的場合。
五、結(jié)語:不作為犯認定上應當謙抑
作為刑法理論中最混亂、最黑暗的迷思,在不作為犯的認定上,應當遵守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從司法實踐來看,不作為犯的判決中,不純正不作為犯的數(shù)量居多。雖然在理論上,所有的犯罪都可以通過不作為實施,但司法實踐中對不作為犯的認定上缺乏等價性的考察,不當擴張了入罪范圍。在涉及多人的不作為犯判決中,認定為同時正犯和共同犯罪中主犯的情形居多,認定為從犯的情形較少。這是因為不作為共犯理論中,原則正犯說存在缺陷,導致實踐中不作為的共同犯罪一般認定為主犯。司法實踐中對不作為的未遂在認定上較為謹慎,一般要求不作為的成立以造成實害后果為前提,這樣的做法較為妥當。
對不作為犯的研究理論繁冗艱深,但在實踐中的做法往往與理論脫節(jié)。筆者認為,理論中的銖量寸度應當對實踐有所陶染,實踐中的做法也應當成為理論可資利用的素材。只有將成文法的完善與現(xiàn)實相勾連,社會實效的衡量與法律寬嚴相濟的考慮相結(jié)合,才能得到妥當?shù)幕卮稹9P者堅信,理性的思考只能通過理性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理性的法律應當引導人們理性地向前看。
[1]勞東燕.風險社會與變動中的刑法理論[J].中外法學,2014,(1):91.
[2]張明楷.刑法學[M].第四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51.
[3]黎宏.不作為犯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107.
[4]Vgl.,Armin Kaufmann,Die Dogmatik der Unterlassungsdelikte,Verlag Otto Schwarts 1959,S.239ff.
[5]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M].第二版.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95.
[6][日]日高義博.不作為犯的理論[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2:90.
[7]黎宏.不作為犯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97.
[8]劉艷紅.論不真正不作為犯的構(gòu)成要件類型及其適用[J].法商研究,2002,(3):52.
[9]李方政,張理恒.不作為詐騙罪的認定[N].人民法院報,2011-12-29(3).
[10]馮玉情,孫毅恒.論不作為詐騙罪的成立[J].西部學刊,2013,(6):53.
[11]徐久生,莊敬華.德國刑法典[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9.
[12]張明楷.論詐騙罪的欺騙行為[J].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5,(3):67.
[13]王鋼,唐婷,從一則案例看不純正不作為犯的等價性——兼談不作為的義務來源[J].湖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0,(2):84.
[14]白建軍.論不作為犯的法定性與相似性[J].中國法學,2012,(2):109.
[15]吳振興.犯罪形態(tài)研究精要Ⅱ[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547.
[16]陳家林.共同正犯研究[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264.
[17][日]西原春夫.犯罪實行行為論[M].戴波,江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80.
[18]Vgl. Armin Kaufmann,Die Dogmatik der Unterlassungsdelikte,1959,S.296 ff.
[19][日]大塚仁.犯罪論的基本問題[M].馮軍,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270.
[20]Vgl. Roxin, “hatcrschaft and ”hathcrrschaft, 8, Aufl. 2006, S. 463.
[21]Vgl. Jakobs,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2. Aufl. ,I993,21/1 ff.
[22][日]平山幹子.「義務犯」について(一):不作為と共犯に関する前提的考察[J].立命館法學,2000,(2):112.
[23][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刑法總論(第7卷)[M].王世洲,主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509.
[24]Vgl. Armin Kaufmann,Die Dogmatik der Unterlassungsdelikte,1959,S.282 ff.
[25][日]內(nèi)田文昭.不真正不作為犯における正犯と共犯[J].神奈川法學.2001,(34):3.
[26][德]許乃曼.論不真正不作為犯的保證人地位[M].陳晰,譯.李曉明.刑法與刑事司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690.
[27][日]平山幹子.不作為犯と正犯原理[M].東京:成文堂,2005:80.
[28]李文凱的哥坐視少女車內(nèi)遭強暴被判強奸罪 法官詳解為何以強奸罪來定刑[EB/OL].(2011-07-13)[2015-03-10].http://www.scxsls.com/a/20110701/49624.html
[29][德]克勞斯·羅克辛.德國最高法院判例刑法總論[M].何慶仁,蔡桂生,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230.
[30][德]漢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學教科書[M].徐久生,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770.
[31][德]岡特·施特拉騰韋特.刑法總論Ⅰ——犯罪論[M].楊萌,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75.
[32][日]山口厚.刑法學總論[M].第二版.付立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116.
[33][德]烏爾斯·金德霍伊澤爾.刑法總論教科書[M].第六版.蔡桂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372.
[34][韓]李在詳.韓國刑法總論[M].韓相敦,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325.
[35]周光權(quán).刑法總論[M].第二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188.
[36]勞東燕.公共政策與風險社會的刑法[J].中國社會科學,2007,(3):131.
編輯:黃航
The Empirical Study of Omission
JIN Feiyan
(School of Law,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The pure omission is the most judical decision of omission in juridical practice.Although each crime can be met by omission in theory, but the affirm of omission in juridical practice lacks the consideration of equivalence property and enlarge the scale the omission. In the judical decisions of omission which involve several people, he affirm of principle is more than accessory.In the theory of omission,’principle offender in principle’has problems, which lesds to the affirm of accessory is limited. The affirm of abortive of omission in juridical practic is limited,which requies the loss. This conduct is reasonable.
empirical study;omossion;pure omission;joint offence;abortive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3.002
2016-07-15
金飛艷(1990-),女,江蘇淮安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刑事法理論以及司法改革研究。
D916
A
1672-0539(2017)03-0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