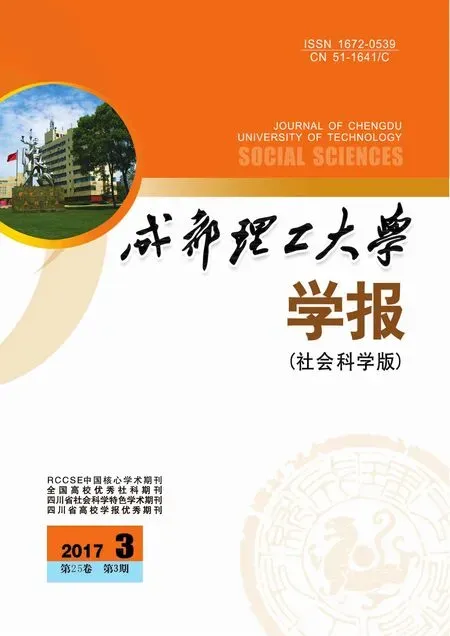網絡游戲畫面的作品定性及相關著作權問題研究
李旭穎
(華東政法大學 知識產權學院,上海 200042)
網絡游戲畫面的作品定性及相關著作權問題研究
李旭穎
(華東政法大學 知識產權學院,上海 200042)
網絡游戲與傳統電影在表現效果和創作過程上都高度相似, 經過獨創性標準檢驗的網絡游戲整體畫面可被定性為類似攝制電影方法創作的作品,其著作權歸屬于游戲開發商,在對涉案網絡游戲畫面侵權判定中,就其是否構成“實質性相似”判定時,可以借鑒“抽象—過濾—比較”的方法將網絡游戲畫面中的表達提取出來并一一比對,從而做出是否侵權的認定。
網絡游戲畫面;電影作品;實質性相似;“抽象—過濾—比較”
2016年,我國游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達1655.7億元,同比增長17.7%,網絡游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達504.6億元,占比30.5%。其中中國客戶端電競游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達333.2億元,中國移動電競游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達171.4%億元;中國客戶端游戲用戶數達到1.56億,網頁游戲用戶數達到2.75億,移動游戲用戶數達到5.28億,中國游戲直播用戶規模突破1億(1)。在“互聯網+”的大背景之下,網絡游戲產業迅猛發展,圍繞網絡游戲是否構成作品、構成何種作品及如何認定游戲畫面構成實質性相似的爭論也隨之而來,但在我國涉及網絡游戲畫面是否構成作品及構成何種作品的認定規則卻付之闕如,相關判例寥寥可數,其實質性相似的認定標準更是存在研究空白。
對此,本文將分析網絡游戲畫面,做出作品類別上的定性,探討其著作權歸屬問題,并總結司法實踐中其他類電作品實質性相似的認定標準,重點就如何判斷不同的網絡游戲畫面是否構成實質性相似進行詳細闡述,以期為日后司法裁判中判定類似案件提供一定參考。
一、理論與實踐中對于網絡游戲畫面保護的分歧
網絡游戲是由計算機軟件設定的,可以由游戲者控制的,顯示在計算機屏幕上的卡通形象和相應的聲音(2)。其就是一種由人物、場景、地圖等多種元素共同構成的載體,對其保護也應綜合各要素間的相互搭配協調關系及其之于網絡游戲畫面的重要性等綜合考量。無論是他人未經許可直播或轉播網絡游戲畫面,抑或是開發與在先游戲具有相同或類似名稱、人物、場景、情節等元素的游戲,都涉及到對于網絡游戲節目畫面究竟構成作品與否的判斷。若網絡游戲畫面構成作品,那么開發者(或玩家)(3)即為作者,他人未經許可對該游戲畫面的轉播、直播或者制作與在先游戲畫面構成實質性相似的游戲則可能侵犯作者的廣播權、放映權復制權或改編權;若網絡游戲畫面僅為錄像制品,那么開發者(或玩家)僅為鄰接權人而無法阻止他人的廣播、放映等行為,其所享有的保護范圍也將被大大的限縮。
網絡游戲的核心內容可以分為兩部分,即游戲引擎和游戲資源庫。游戲引擎是指由指令序列組成的單純的計算機程序,程序本身是由原代碼、目標代碼以及一些其他要素,如模數結構、參數、宏指令等共同組成,因而其屬于一種計算機軟件。他人未經許可直接復制該游戲軟件代碼則構成侵權,可依據《計算機軟件保護條例》進行保護。游戲資源庫是指網絡游戲軟件中各種素材片段組成的資源庫,表現為玩家可以通過肉眼直接感受到的網絡游戲畫面。對游戲畫面的保護,有觀點認為游戲畫面來源于游戲作品本身,為直接呈現在計算機屏幕上的、具有可感知性和可復制性的連續畫面、網絡游戲畫面應當構成作品(4)。也有觀點認為,游戲畫面作為游戲結果的呈現過程,因為游戲結果有不確定性,游戲過程具有隨機性和不可復制性,而且玩家的交互性操作使得網絡游戲本身并不構成作品,所以游戲畫面不屬于著作權法規定的作品(5)。對于第二個觀點,有學者提出,在游戲中由于具有統一的故事線索和主線任務,實質部分的故事情節、人物角色、游戲畫面、音樂等都是重復出現的,即使不同玩家的畫面顯示有個別差別也都是網絡游戲開發人員預先設計和安排好的,無論玩家如何操作都不會對游戲整體畫面的內容起到任何增添或修改作用,因此交互性操作并不會對網絡游戲整體畫面的獨創性認定產生實質性的影響[1]。
根據我國以往的司法實踐,往往都是將網絡游戲進行拆分保護,例如“爐石傳說”案、《我叫MT》案等,法院根據網絡游戲的各個要素的獨創性標準將網絡游戲畫面分別構成文字作品、音樂作品、美術作品等進行保護,這種保護模式需要將網絡游戲畫面分隔成若干單獨作品,并進行一一比對,這種方法便捷了法官認定侵權的程序,但可能會帶來保護不足的問題。例如,在后游戲開發者是完全比照在先游戲中人物進行制作,只是將其性別和部分服裝進行了變更。那么,由于后者人物造型符合獨創性且不構成對前者造型的改編,故而根據單獨保護的方法是很難認定其源自于前者并判定侵權事實成立的。這樣會間接限縮對網絡游戲的保護范圍,也不符合《著作權法》鼓勵作者創新的立法原則。與以往司法實踐中分解游戲畫面要素保護的案例不同,上海浦東新區法院判決的“《奇跡MU》訴《奇跡神話》案”(6)更是全國首例將網絡游戲整體畫面認定為“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下文簡稱“類電作品”)并判定被告侵權成立的案件。在該判決中,網絡游戲畫面作為一個特殊的多種作品結合體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這一判決引發了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廣泛關注,也凸顯出當前網絡游戲整體畫面的保護存在著定性模糊和認定困難的問題。
二、具備獨創性的網絡游戲畫面可以構成類電作品
電影是由上下相關的一系列畫面所構成,再通過機器設備進行播放時能夠給觀眾以畫面中的人或事物在運動的感覺,也正因如此,電影也被稱為“活動圖片”(motion pictures)[2]。而網絡游戲畫面呈現在屏幕上的是文字、圖片、聲音等原元素,這些元素可以單獨構成作品,也可組合成“連續動態的圖像”,進而給予玩家身臨其境般的視聽享受,與電影的含義及創作過程都高度相似。所以,對于網絡游戲畫面保護的方式選擇可參照電影獲得著作權保護方式。
根據《著作權法實施條例》規定,電影作品和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是指攝制在一定介質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無伴音的畫面組成,借助適當裝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傳播的作品。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電影作品和錄像制品之間的區別在于是否具有獨創性,獨創性程度較高的電影為“電影或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給予其著作權的保護;獨創性較低則為“錄像制品”,給予其錄制者鄰接權的保護。例如德國《著作權法》就將錄影分為“電影作品”和“活動圖像”兩類,分別給予其狹義著作權(第88-94條)和鄰接權(第95條)的保護[3]。基于“電影作品”和“錄像制品”的差別,判斷網絡游戲畫面的獨創性高低便是決定其可獲得何種保護的關鍵所在。
判斷一個智力成果是否滿足著作權法中的獨創性要求,需要從兩個層面進行考量。首先,作品需要滿足“獨”的要求。所謂“獨”即是成果源自本人,是獨立創作的結果,而非抄襲品。具體到某一智力成果如果要滿足“獨”的要求,則可以表現為下列兩種方式:其一,成果系創造者從無到有獨立創造而來;其二,成果系創造者在他人作品基礎上添加可以被外界識別的表達所形成的新的成果[2]20。對于網絡游戲畫面而言,其中的人物、場景、地圖、情節等毫無疑問均系游戲開發者智力成果的體現,完全符合“獨”的要求。其次,作品還須滿足“創”的要求。所謂“創”即是成果體現作者獨特的判斷和選擇,達到一定程度的智力創造水準。具體表現為作品需要有一定的智力創造性,能夠反映作者獨特的智力選擇并展示其個性。需要明確的是,著作權法獨創性中的“創”不要求勞動成果比現有成果先進,因此不同于專利法上的創造性。同時,獨創性中的“創”也并不要求成果具備高度的文學藝術美感,一個智力成果并不會因其在藝術價值上乏善可陳而自動失去著作權法對其獨創性的認可。對于網絡游戲畫面來講,畫面中通常會出現多種造型各異的人物形象、波瀾起伏的地形構造、復雜縝密的游戲地圖等多種元素,連接各元素的介質便是環環相扣的故事情節或角色任務。同時玩家為了操作需要,也可以通過切換不同的視角來完成對角色的指揮。毫無疑問,現在多數競技類網絡游戲的畫面早已不是如“俄羅斯方塊”、“貪吃蛇”等的單一、平面化影像,而更多的呈現為一種復合、立體的形式,完全符合獨創性中“創”的要求。因此,滿足獨創性要求的網絡游戲畫面屬于類電作品。
對此,理論界也有觀點認為,從電影作品與制品的分野出發,當一個網絡游戲開發者主張網絡游戲構成電影作品時,他必須證明自己的網絡游戲開發投資較大,綜合了角色、劇本、美工、音樂、服裝設計、道具等多個創作手段,具有風富情節和創作者獨特的思想個性、作品風格,可以構成作品。否則網絡游戲就只能通過音像制品去主張權利[4]。而司法實踐中,法院曾就判斷音樂電視(MTV)究竟構成類電作品抑或錄像制品列舉過較為詳細考量因素,所列舉的詳細因素與上述觀點有諸多相似之處,對我們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在“音著協訴至尊娛樂案”(7)中,法院指出“鑒于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方法創作的作品屬于復合作品,由不同種類的作品結合而成,其對獨創性要求較高,一般可以從下列幾個方面判斷:(1)體現電影制片者和電影導演鮮明個性化的創作特征;(2)在攝制技術上以分鏡頭劇本為藍本,采用蒙太奇等剪輯手法;(3)包括演員、劇本、攝影、剪輯、服裝設計、配樂、插曲、燈光、化妝、美工等多部分合作的綜合性藝術;(4)投資成本較大……音樂電視(MTV)如果具備下列特征的,一般應認定為錄音錄像制品:(1)沒有故事情節、沒有導演和制片者的個性化創作,主要是對歌星演唱及群眾演員配合表演的再現;(2)拍攝目的主要在于卡拉OK演唱而非影院、電視臺放映;(3)歌詞、歌曲在其中起主導作用,詞曲作者的貢獻占主要部分;(4)投資成本較小。”筆者將各因素進行歸納為圖1所示:

圖1 獨創性考量因素
我們看到,對于類電作品與錄像制品的獨創性,法院首先認為作為獨創性程度較高的電影作品及類電作品,其應當是導演和制片人獨立選擇安排與個性活動的體現,單純再現表演的場景所給予攝影師智力創作的空間過于狹窄,即便在某些微小的細節上也會涉及到攝影師的個人選擇,例如鏡頭的拉伸、拍攝的角度等,但很難滿足大陸法系國家對于作品獨創性的要求。同樣地,網絡游戲畫面中包含復雜的人物關系、故事情節以及逼真的游戲效果都來源于游戲開發者的前期制作和后期剪輯,是其智力成果的表達。并且,不同玩家會根據游戲進程以及完成任務的需要不時調整觀察視角和操作方式,所以呈現在觀眾眼中的游戲畫面也大異其趣。其次,電影及類電作品區別于錄像制品的原因在于其是集攝影、劇本、燈光、音效等多種藝術表達于一身的復合體,是一個故事性的表達。而錄像制品缺乏一種連貫銜接的敘述模式,更多的像是詞曲作者的個人獨白。反觀網絡游戲畫面,音樂、動畫、場景、地圖、任務攻略等元素完全被包含在其中并被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玩家所選擇的游戲角色在游戲中遭遇挑戰并克服困難,最終成功完成游戲任務的過程很大程度上即是一種故事性的表達。因此,網絡游戲畫面完全符合該項要求。最后,法院認為通常情況下電影作品及類電作品的耗資是大于錄像制品的,因此其也被作為一項判斷獨創性的依據。因為作為作品核心的獨創性長久以來都是一個極為模糊的概念,法官通常只能對其進行個案衡量。因此,借助投資成本這一具體數值來量化抽象概念的外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法官做出的無奈的明智之舉。反觀網絡游戲,我們發現市面出現的不少網絡游戲同樣也耗資不菲。例如,《最終幻想12》的開發費用為4800萬美元,《合金裝備4:愛國者之槍》的開發費用為6000萬美元,而《星球大戰:舊共和國》的開發成本更是達到了讓人咋舌的2億美元[5]。毫不夸張地說,部分游戲的投資已經趕上并超過電影的投資,因此如今互聯網時代的游戲已遠非單機游戲可比。綜上所述,網絡游戲畫面是完全有可能符合獨創性并構成類電作品的。
有人指出,根據《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4條第11項(8)對電影作品及類電作品的定義,“攝制”應當為電影作品及類電作品的構成要件,而這里的“攝制”應當是指用攝像裝置進行拍攝錄制。但對于網絡游戲畫面來說,其均系游戲開發者在電腦上繪制而來,并非由攝像裝置拍攝所得,那么其很難被認定為是一種類電作品。筆者認為,此種觀點雖然嚴格遵循法律規定,體現了法律工作者應有的嚴謹,但卻難謂自洽。因為無論是傳統電影抑或經計算機制作的電影,其表現形式均為“由一系列有伴音或無伴音的畫面組成”,而且這些畫面上下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一旦放映就會給人以活動的感覺,如果僅僅是由于制作技術不同就將其認定為不同作品實屬牽強。同時這種劃分方式也將使得網絡時代許多僅靠電腦制作而未經攝像機攝制的新類型電影作品在我國現行《著作權法》中難以尋覓到自己的位置[2]107,如科幻電影、網絡動漫等。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編寫的《伯爾尼公約指南》指出:對此類作品的定義并不考慮制作它的“工藝方法”,“無論在哪種情況下,屏幕上所顯示的都應當受到同樣的保護”(9)。可見作為我國《著作權法》立法參考的《伯爾尼公約》并非是將“攝制”作為類電作品的構成要件。而縱觀世界各國的立法,也很少有國家會將“攝制”作為構成電影作品的要件之一。《英國版權法》第5條規定:“‘影片’指(固定)在任何介質上的,可借助任何方式從中再現出移動影像的錄制品。”《日本著作權法》第2條規定:“‘電影作品’包括產生類似電影中視覺或視聽效果的方法表現的,并且固定于物質載體的作品。”上述對電影作品的定義均未要求“攝制”要件,故而有學者主張將刪去《著作權法實施條例》釋義中的“攝制在一定介質上”的限定[6],還有學者主張對“攝制”一詞進行適當的擴張解釋,以涵蓋通過非攝制方式制作的影視作品[7]。上述兩種解決方式孰優孰劣筆者不敢妄下結論,但網絡游戲畫面這種非通過攝制方式被固定在一定載體之上的智力成果是完全可以構成類電作品并受到著作權法保護的。
三、網絡游戲畫面著作權歸屬問題
網絡游戲是玩家根據游戲規則,調用事先設置的道具、場景、情節等完成的,這使得人們往往認為玩家是創作出網絡游戲畫面的作者,從而得出網絡游戲畫面著作權歸屬于玩家的結論。如前所述,具有獨創性的網絡游戲畫面可以作為類電作品受到著作權法保護,那么其著作權歸屬問題便也可參照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方法創作的作品(下稱電影作品)的著作權歸屬思路。首先,電影作品是一類特殊的演繹作品,其突破了演繹作品“雙重權利、雙重許可”規則,對電影作品的利用需要經過雙重許可,利用電影作品自身(也即排除將其改編成其他網絡文藝形式的利用方式)的權利完全屬于制片者。對電影的復制、發行、放映等,只需經過電影作品的制片人許可即可;其次,電影作品作為一種特殊的合作作品,我國《著作權法》第15條第1款將電影作品的著作權賦予制片者,編劇、導演、攝影、作詞、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權。這主要是考慮到制片者(10)相對于其他人,投入的成本巨大,也即以投資為標準劃定著作權享有者。同樣,對于網絡游戲來說,相對于網絡游戲公司制作游戲的巨大成本而言,玩家為網絡游戲支付的成本極低,如果玩家享有游戲畫面的著作權,并可以以此制止網絡游戲開發者利用相同的畫面,則會造成網絡游戲開發者和游戲玩家之間權利義務的嚴重不平等性,不利于網絡游戲產業的發展。最后,網絡游戲的玩家即使有超高的游戲技巧,也無法擺脫網絡游戲程序設計的千萬種結果。玩家在玩游戲時,網絡游戲的程序設計者并沒有給予其個性表達的空間,玩家只能在程序設計預設的范圍內進行活動,其表現的是各種游戲玩法的可能性,并不存在符合作品創作的要素。也即玩家玩游戲的行為是在遵循游戲設計者預設的游戲規則和可能的結果的前提下調用游戲設計元素和場景,并以動態畫面呈現出來,其玩游戲過程并不是著作權法意義上創作作品的過程,玩游戲的行為也不是創作作品的行為,游戲玩家的作用是將靜態的游戲數據指令調取出來,所以玩家不能稱為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者[8]。筆者以為,考慮到網絡游戲開發與電影創作的相似性,網絡游戲畫面著作權歸屬可以借鑒電影作品的規定,即游戲開發者享有對游戲整體的著作權,玩家并不享有游戲畫面的著作權。
四、網絡游戲畫面實質性相似的判斷規則
在“《奇跡MU》訴《奇跡神話》案”中,法院根據大陸法系著作權侵權認定“接觸+實質性相似”的判斷標準,通過比對兩款游戲中的情節、人物、場景等相關素材來認定游戲畫面是否達到實質性相似的程度。此種判斷方法雖在網絡游戲畫面侵權認定中尚屬首例,但在視頻、影視劇等相關類電作品中卻并不鮮見。
在“帝王潔具訴徐浩杰侵犯著作權案”(11)中,原告帝王潔具公司起訴被告抄襲其制作的廣告宣傳視頻,法院分別從主題與框架、表現手法、技術層面等角度對比兩視頻(見表1),并最終做出二者構成實質性相似的結論。
表1 兩視頻的對比

原告被告相同點主題與框架二者在主題選擇、故事大綱、題材運用、場景安排等方面完全相同表現手法被告作品完整使用了原告作品以《Whatawonderfulworld》歌曲營造氛圍,突出情節,場景轉換配合歌詞大意,輕敘事、重意會的手法技術層面被告作品與原告作品一樣選擇歐美設計師為主角,諸多鏡頭如二人邂逅花海與長草、愛情甜蜜的女主角仰臥、男主角跪地凝視、嬰兒的出生與成長、家庭幸福的沐浴、事業成功的設計師仰望蒼天等也相同或極為近似再現文字表達被告作品的創意與整體表達完整地展現了原告作品中文字部分所要表達的全部內容與要素不同點完成時間只是一個樣片已經拍攝完成呈現的整體色調被告作品在鏡頭和畫面的具體安排與組合上與原告作品多有不同,其呈現出的整體色調也有不同
法官在對比兩作品時采取了剝離的方法,即將被告作品與原告作品中相同的所有元素予以剝離,看剩下的情節或場景是否足以構成與原告作品完全無關的另一部作品。若構成,則只能說明被告在原有作品基礎上制作了符合獨創性的新作品,但依然不可排除其對原告作品侵權的可能;若不構成,則被告與原告作品構成實質性相似。在本案中運用剝離的方法使得認定作品構成實質性相似變得簡便而直觀。但運用剝離的方法是否需要遵循一定的順序、是否需要考慮一般消費者對兩作品的整體認識、該方法與判斷文字作品實質性相似的方法有何異同等問題并不能從法院判決書中看出,故而筆者在下文將運用比較法探尋網絡游戲畫面實質性相似認定的標準。
(一)屬于“非字面相似”
當兩部作品具有實質性相似時,可能會存在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是“字面相似性”(literal similarity),這種情形表現為被告原封不動地復制了原告的作品,或者在文字、音樂、戲劇等作品中逐字逐句地大量抄襲了原告的作品,法院一般是從復制或抄襲的數量或質量進行判斷的;第二種情形是“非字面相似性”(nonliteral similarity),在該情形中被告并非原封不動地照搬原告的作品,而是對其進行轉換變更。例如在文學作品中,被告僅僅是使用了與原告作品中相似的人物、場景和情節等要素,但仔細比較又并非是完全相同。“非字面相似性”存在有著重要的意義,否則侵權者只要通過非實質性或者細微的改動就可以輕易地回避著作權人的權利,即通過若干細微處、形式上、非實質性的改寫來達到規避著作權之侵權責任的目的(12)。在對此情形進行判斷時,法官通常會框定一定的范圍,若被告對原告作品的改變或對原告作品中某些因素的使用在該范圍內,則被告構成侵權;若超過該范圍,則不僅不構成侵權反而可能構成一種新的創作[9]。毫無疑問,在網絡游戲畫面的侵權案件中很少出現當事人制作與游戲開發者全部或部分相同的游戲。多數情況下,行為人都是在對原游戲中部分要素進行轉化后的再行使用,那么此時這種相似即屬于“非字面相似性”。
在“非字面相似性”方面,漢德法官曾經在1930年的“Nichols”案(13)中提出了一種“摘要層次”測試法(“levels of abstract” test),其在判決書中寫道:“……在涉及戲劇作品時,抄襲者可以是割走了一個場景,或者可以是挪用了一部分對話。然而問題在于,這拿走的部分是否構成‘實質性’,因而不是對于享有版權作品的‘合理使用’……就任何一部作品,尤其是就戲劇作品來說,隨著越來越遠離情節,會有一系列越來越具普遍性的模式與之相應。最后一個模式可能就是該戲劇是有關什么的最一般的陳述,有時可能只包括它的名稱。”在上述引文中,漢德法官提出著名的“摘要層次”法主要便是針對非文字性占用,如果兩者的相似或一致是在高層次的思想觀念上,就不存在實質性相似或侵權;如果兩者的相似或一致是在低層次的表達上,則會有實質性相似或侵權發生。而受保護的表達與不受保護的思想觀念之間的臨界點,又必須依據作品的種類、性質、特點等做出個案處理[9]368。
(二)借鑒計算機軟件侵權認定的“抽象—過濾—比較”法
“摘要層次”法雖然簡單易懂,但多被用于文字作品。同時,由于思想與表達二分法的臨界點從來都不明確,上述判斷方法過于籠統,在無形中增加了法官司法判斷的難度。美國第二巡回上訴法院曾在判斷計算機軟件“非實質性要素”構成實質性相似時提出過“三要件”標準,即“抽象—過濾—比較”。步驟分為三步:
首先是“抽象”。法院應首先將原告的軟件(或者被侵權的軟件)分解,將其中的每一個抽象層次分離出來,從很一般到非常具體,例如主要的目的、程序結構、功能模塊、算法、數據結構、源代碼。質言之,司法實踐的“抽象”過程是將爭議雙方的程序進行分解,從源代碼層次開始,逐步、逐級往上抽象建構出各個子程序或結構的“思想”,此抽象步驟將直到最上位主程序的總思想。隨著層次的上升,會有越來越多的“思想”被剝離開來,剩余的就是可受保護的“表達”。
其次是“過濾”。當法院確定原告軟件的抽象層次之后,就將可保護的表達與不可受保護的材料分離開來,審查每一抽象層次上的結構性因素,以確定:(1)是否屬于由效率的考慮所支配的因素。在計算機軟件的編寫過程中,編程者基于對高效率的追求會采取最簡潔的邏輯方式或計算方式,那么就可能發生思想與表達的混同,此時版權法為了維護更高的法秩序利益并不對其進行保護;(2)是否屬于由軟件的外部要素所決定的因素。作者在撰寫某一特定時代的歷史作品或文學作品時,必然會使用某些特定的情境或標準的文字要素。例如,在描述美國西部牛仔這一話題時通常都會搭配有酒吧、手槍、駿馬等景物,此即所謂的“情景原則”。同樣地在很多情況下,當編程者在編寫具有某一特定功能的計算機軟件時,也不得不使用某些標準的技術或要素,思想與表達再次發生混同,版權法同樣不對其提供保護;(3)是否屬于來自于公有領域的因素。公有領域的材料不受任何人壟斷,是全人類共有的財富,因此他人無論怎樣使用公有領域的素材,作者均無權依據版權法禁止其使用。
最后是“比較”。當法院從被侵權的軟件中過濾了思想、效率所決定的因素以及來自公有領域的材料之后,剩下的就是一個可以受保護的表達的核心。此時法院判斷的焦點就是被告是否從這一受保護的表達中進行了抄襲,以及被抄襲部分在原告軟件中所具有的重要性。
(三)網絡游戲畫面實質性相似判斷標準
將上述“抽象—過濾—比對”的方法運用于網絡游戲畫面實質性相似比較中,可以遵循以下步驟:首先對涉案網絡游戲畫面進行抽象,從具體的人物形象、游戲故事情節著手,并且逐漸進行抽象概括直到將提取為普通的思想為止,例如對“紅色警戒”這款游戲則可以將其概括為“一種玩家通過制造現代化軍隊擊敗別的玩家并獲得戰斗勝利的游戲”;接著,將涉案原告網絡游戲畫面中涉及的效率因素、“情景原則”要素以及公有領域素材因素逐一剔除,例如在吸血鬼游戲中,原告就不得主張自己游戲畫面中的蝙蝠和古堡系其獨有而禁止被告使用,因該元素實際屬于“情景原則”的要素。最后,網絡游戲畫面中剩下的部分就是涉案雙方需要進行重點比較之處。如果發現被告的網絡游戲畫面與原告幾乎一樣或者其實質是對原告畫面的“同義替換”,那么被告的網絡游戲畫面與原告就構成實質性相似,原告可以請求法院判定被告侵權。
五、結語
隨著游戲產業的日益發展,對網絡游戲進行簡單拆分以尋求保護的方式已經無法適應我國目前游戲產業的發展現狀了。網絡游戲本就是一種由人物、場景、地圖等多種元素共同構成的載體,對其保護也應綜合考量各要素間的相互搭配協調關系及其之于網絡游戲畫面的重要性等情況。基于此,將網絡游戲的整體畫面視為一個特殊的多種作品結合體來進行保護更具妥適性,在判斷兩款網絡游戲畫面是否構成實質性相似時可以依據“抽象—過濾—比較”的方法將網絡游戲畫面進行拆分,并就構成表達的部分進行比對,以期得出行為人侵權與否的結論,從而更好地維護游戲市場正常、和諧的法律秩序。
注釋:
(1)參見中國音數協游戲工委、CNC中新游戲研究(伽馬數據)、國際數據公司(IDC):《2016中國游戲產業報告:摘要版》,中國書籍出版社2016年12月第1版,第11-55頁。
(2)Stern Electronics, Inc. v. Kaufman, 669 F2d 852 (2d Cir. 1982).
(3)對于網絡游戲畫面的作者究竟為游戲程序的開發者還是游戲玩家,理論界和實務界均存在不同看法,因其并非本文討論的重點,故而筆者在此處不做過多贅述。
(4)參見歐修平、孫明飛、吳東亮:《皰解中國網絡游戲直播第一案:權利屬性及責任歸屬》, http://zhichanli.baijia.baidu.com/article/189052,2016年12月23日第一次訪問。
(5)參見(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529號民事判決書。
(6)作為我國首例將網絡游戲畫面認定為類電作品的案件,其對于我們的研究有重要意義:《奇跡MU》是由韓國Webzen公司創作的一款網絡游戲,2012年原告上海壯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壯游公司)取得其著作權授權和國內獨家運營權。而被告廣州碩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碩星公司)成立于2013年,主要從事網絡游戲研發,《奇跡神話》即是該公司推出的一款網絡游戲產品,后授權廣州維動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維動公司)進行推廣運營。2014年壯游公司發現,《奇跡神話》抄襲了《奇跡MU》,在作品名稱、故事情節、地圖場景、角色、技能、怪物、裝備等的名稱、造型等多個方面與《奇跡MU》相似,遂于2014年6月向法院提起訴訟。原告壯游公司認為,從用戶感知的角度看,網游是攝制在一定介質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無伴音的畫面組成,借助適當裝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傳播的,包含了特定人物、場景和故事情節的類電影作品。同時,與傳統的類電影作品相比,網絡游戲有一定的互動性,不同玩家玩同一款游戲可能會呈現出略有差別的觀感,但這些細微差別都由開發者事先設計的有限情節發展線索所確定,其主線任務和整體發展是固定的,不同玩家所呈現出的類電影作品的表現形式,無實質性的差別。但被告碩星公司認為,電影的播放是單向性的,而網絡游戲是雙向互動性的,不同玩家操控游戲或同一玩家以不同玩法操控游戲,均會得到不同的“有伴音或無伴音的畫面”。同時,其也認為網絡游戲的性質更趨向于游戲工具的數據庫,而玩家則是所呈現出來的一系列聲音畫面的作者。因此,不能將《奇跡MU》這一網絡游戲的屬性界定為類電影作品。
(7)(2011)粵高法民三終字第470號。
(8)《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4條第11項:電影作品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是指攝制在一定介質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無伴音的畫面組成,并且借助適當裝置放映或者以其他方式傳播的作品。
(9)劉波林譯.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1971年巴黎版本)指南(附英文文本)[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 :15,轉引自:王遷.著作權法[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107.
(10)通常情況下“制片者”并非電影字幕中所顯示的作為自然人的“制片人”或“制片”,而是組織拍攝電影的機構,如電影公司。
(11)(2014)成知民初字第369號。
(12)Nichols v. Universal Pictures Corporation,45 F.2d 119 ( 2d Cir. 1930).
(13)Nichols v. Universal Pictures Crop. ,45 F. 2d 119,7 USPQ 84 (2d Cir. 1930).
[1]王遷,袁鋒.論網絡游戲整體畫面的作品定性[J].中國版權,2016,(4):19-24.
[2]王遷.著作權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5 :106.
[3]雷炳德.著作權法(一)[M]. 張恩民,譯.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530.
[4]張學軍.網絡游戲與著作權保護相關問題探討[J].中國版權,2016,(5):52-56.
[5]鳳凰網.制作成本最高的十款游戲:GTA5耗資達1.37億[EB/OL].(2013-08-28)[2016-6-10].http://games.ifeng.com/pcgame/news/detail_2013_08/28/29098269_1.shtml
[6]劉春田.知識產權法[M].第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65.
[7]崔國斌.著作權法——原理與案例[M].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 :153.
[8]馮曉青.網絡游戲直播畫面的作品屬性及其相關著作權問題研究[J].知識產權,2017,(1):3-13.
[9]李明德.美國知識產權法[M].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4 :366.
[10]鄧恒.我國計算機軟件著作權侵權判定之“實質性近似”再審視——以美國司法判例演變為研究對象[J].法學雜志, 2014,(9):124-132.
編輯:黃航
Research on the Nature of the Online Game Screen and Related Issues
LI Xuying
(Schoo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China)
The network game and the traditional film are highly similar in performance and the creation process, online game screen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a work created by virtue of the analogous method of film production after the originality judgment, the copyright belongs to the game developers. Judging whether electronic game screen is a “substantial similarity”, we can extract the expression of the video game screen and one by one comparison with the “Abstract -Filtration-Comparison” method , so a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infringement was established.
online game screen; cinematographic works;Substantial similarity; Abstract-Filtering-Comparison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3.003
2016-07-15
李旭穎(1992-),女,浙江臺州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知識產權法學研究。
D923.41
A
1672-0539(2017)03-0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