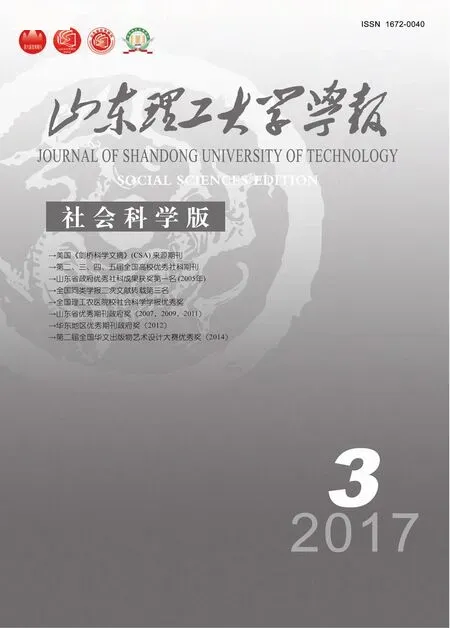中等收入背景下山東農業生產率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公茂剛, 王學真(.山東理工大學商學院,山東淄博55000;.山東理工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山東淄博55000)
中等收入背景下山東農業生產率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公茂剛1, 王學真2
(1.山東理工大學商學院,山東淄博255000;2.山東理工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山東淄博255000)
利用1991-2014年山東省17地市面板數據,分析中等收入背景下農業生產率影響因素,得出的主要結論:經濟增長和工業化水平變化對山東農業生產率變動都具有顯著正向效應,而且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前后該效應一直為正,不具有明顯差別,兩者對山東農業生產率變動的影響效應也是最大的;農村居民收入、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城鎮化率和財政支農的變動對山東農業生產率變動的效應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由負轉正;農業固定資產變動對山東農業生產率變動的影響在中等收入水平前后都始終為正,但影響程度明顯降低;農業產業結構變動對山東農業生產率變動的影響在中等收入水平前后都不顯著。
農業生產率;經濟增長;工業化;基礎設施
一、引言
農業生產率變化的影響因素很多,國內外學者也做過大量理論與實證分析,總結起來主要包括經濟發展水平、農業研發、基礎設施、教育培訓、技術推廣、農民收入、人力資本等。比如,Hayami & Ruttan(1969)認為,國家間農業生產率的差異源于不同的資源積累、技術投入和人力資本[1]895-911。Yee et al(2002)研究了1960—1993年間農業公共研發、技術推廣和公路基礎設施對美國農業生產率的影響,結果表明農業公共研發和公路基礎設施對農業生產率有正效應,而技術推廣的作用則與各州的經濟基礎條件有關[2]5331。Dias Avila et al(2010)分析了拉美和加勒比地區農業生產率及其決定因素,突出了農業研發、農業推廣、學校教育、收入改善和減貧的重要性[3]3713-3768。Camelia(2012)認為農業人力資本是羅馬尼亞地區農業生產率增長的重要決定因素[4]217-225。石慧等(2011)的研究發現,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能夠顯著促進農業生產率水平提高,人力資本的作用在不同樣本時期有差別,對外開放、市場化程度和農業科研投入的作用不明顯[5]59-73。潘丹(2012)認為我國農業生產率受到地理因素、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和農業結構的影響[6]144。李谷成等(2015)認為公路設施能夠顯著促進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而農電設施的影響不顯著,灌溉設施的影響為負[7]141-147。通過對已有文獻的回顧發現,對我國農業生產率影響因素的分析并沒有以中等收入為背景進行分析,對山東省農業生產率影響因素的分析也是如此。根據山東統計年鑒數據,山東省從1997年開始已經達到了中等收入水平,當年山東省人均GDP為7461元,按照當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8.2898折算約900美元,已經超過當年世界銀行中等收入標準786美元。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經濟社會發展中會出現一些新情況,比如人口紅利消失、農民工的用工荒;工業開始反哺農業;加速城鎮化等。那么在這些新情況下,農業生產率的發展變化會不會受到影響呢?本文將以中等收入為背景,實證分析山東省農業生產率的影響因素。
二、理論分析
下面主要從理論上分析農業生產增長會受哪些因素的影響以及是如何影響的。
經濟發展水平對農業生產率的影響顯而易見,經濟發展水平越高,農業生產率也越高;反之則越低。但經濟發展水平是如何影響農業生產率變動的呢?經濟發展既有量的增加又有質的提高,量的增加即為經濟增長,質的提高則主要表現為結構變化。因此,經濟發展對農業生產率提高的影響主要通過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優化升級來實現。經濟增長體現為國民收入或人均國民收入增加,當國民收入增加時,就會有更多的資金用于科研支出,從而促進科技進步,而山東省農業生產率的提高主要依賴技術進步。人均國民收入提高和經濟質量提升也對農業生產率提高具有反作用。隨著經濟結構提升和人均國民收入增加,無論是農產品加工工業還是居民消費都對農產品數量和品質有更高要求,而要增加農產品數量和提高農產質量都需要提高農業生產率。
農業產業結構變化是經濟結構變化的重要內容,農業產業結構變化更是農業生產率變動的重要影響因素。由于農業內部各產業的生產率存在高低差異,而當生產要素從生產率低的部門或者生產率增長慢的部門轉移到生產率高的或者增長快的部門能夠促進整個農業生產率提高。而且農業各部門的要素使用密集度不同,比如水果種植業相對于糧食種植業更偏向于勞動密集型,畜牧業相對于種植業更偏向于資本密集型。由于不同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原因等并不一致,因此當不同要素密集型產業生產率發生變化時,農業生產率變化的程度并不一致。因此,農業產業結構的變化會影響農業生產率的變化。
農村居民收入也是體現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因此其對農業生產率變動會產生影響。農民收入的高低與農業生產方式、農業資源利用方式的選擇、農業科技推廣與應用、農業生產率的變動具有緊密聯系。農民收入水平較低時,由于其沒有足夠的資金采用先進生產技術以及在經濟利益驅使下追求更高的產量,農民必然采取粗放的生產方式,通過對土地和水資源的掠奪性使用來獲取更多農產品,從而導致農業生產率較低以及自然資源的破壞。農民收入水平提高時,經濟利益的趨勢會降低,而且其有更多資金可以采用先進的生產技術,從而可以使用集約生產方式保護農業自然資源,進而促進農業生產率提高。
農村基礎設施和農業固定資產投資對農業生產率增長具有重要影響。農村基礎設施主要包括農田水利、交通通訊、能源電力等的基礎設施投資,農業固定資產投資主要指對農業生產機械的投資。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和農業固定資產投資通過降低農業生產成本,增強農業技術推廣與應用,擴大農業經營規模等影響農業生產率。農村基礎設施投資通過改善農田土地質量、自然資源環境,提供更好灌溉條件和排水排澇設施,方便農業生產資料運輸和使用等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從而提高農業生產率。農業固定資產投資則增加了農業生產資料數量,提高了農業生產資料的質量,進而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農業生產率。
工業化和城鎮化對農業生產率變動也有重要影響。工業化特別是新型工業化的發展為農業生產方式轉變提供了物質基礎。新興工業化道路是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工業化促進信息化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科學技術快速發展,經濟效益逐步提高,資源環境得到可持續利用和保護,人力資源得到更有效配置。很明顯以科技進步和創新為動力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具有巨大的外部效應。首先,新型工業化的產品為農業生產提供先進優良的生產工具和設備,提高生產效率;其次,新型工業化的技術和知識溢出,為農業生產方式向依靠科技的集約型轉變提供了條件;最后,新型工業化過程中的知識溢出會普遍提高勞動力素質,農業勞動力素質的提高自然也會促進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城鎮化伴隨著工業化而進行,伴隨著城鎮化的加快,大量農村人口會逐漸轉移到城鎮,農業勞動力會進一步減少,這便反作用于農業生產率,要求農業生產率的提高。
財政支農投入也影響農業生產率變動。財政支農是國家財政對農業、農村、農民的支持,包括基本建設支出、事業費、科技三項支出及支援農村發展生產資金。財政支農投入一部分直接支持農業生產,進行良田和水利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補貼農民購置農機設備和良種等,此外財政支農投入還通過支持農業科技研發與推廣、農業科技人員培訓等方式間接支持農業生產。據前文分析,無論支持農業基礎設施還是農業科技研發推廣與人員培訓都會促進農業生產率提高。
農村人力資本變化影響農業生產率變動。農村人力資本體現在農村科技人員以及具有較高學歷的人口比重。農村人力資本越高,表明農民的科技知識水平越高,從而能夠更有效地利用各類先進農業生產工具和設備,采用更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理念,并能進一步驅動技術創新和知識發展。掌握較高的人力資本,還能夠提高農民合理配置和管理生產要素的能力,并能更加有效地獲取和理解市場信息,從而能從千變萬化的市場經濟中獲得商機,促進農業生產。較高的人力資本還會提高人們環境保護意識和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理念,使用環境友好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保護農業資源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這些都將促進農業生產率的增長。
三、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取與數據描述
該部分將在以上理論分析和資料搜集基礎上建立山東省農業生產率影響因素計量經濟模型,利用面板數據分析各相關變量對農業生產率增長的影響程度。首先進行變量的選取和數據的說明。被解釋的變量是農業生產率的變動,采用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指數(NP)表示。本文采用經過Caves et. al.(1982)[8]1393-1414和Fare et. al.(1994)等人[9]66-83發展的基于DEA方法的非參數Malmqusit指數法對山東農業生產率進行了測算。非參數Malmqusit指數法在計算時,不需要事先設定生產函數,因此不需要進行參數估計,它采用的是線性規劃方法構造生產前沿面。由于計算Malmqusit指數時需要面板數據,因此本文選用了山東省17個地市作為截面,即決策單元,1990—2014年作為時序。之所以采用1990—2014年的數據是因為之前的數據收集比較困難,而且有的地市也存在缺失或沒有統計,比如日照市是1989年6月才成立,因此之前是沒有統計數據的。本文選用的農業產出數據為第一產業增加值,數據來源于《山東統計年鑒》(1991—2015)。選用資本和勞動力作為投入,此處沒有選擇種植面積、有效灌溉面積、施肥量、農業機械總動力等,原因在于本文選的農業產出數據是第一產業增加值,不僅包括種植業,還有牧副漁等,而上述投入只是在種植業領域的投入,因此不夠全面。其中資本的數據為第一產業的資本存量,勞動力數據為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數據來源于《山東統計年鑒》(1991—2015))。由于第一產業資本存量數據沒有相關統計,因此需要計算,計算公式為Kt=(1-δ)Kt-1+It,該公式表示當期的資本存量等于上一期資本存量減去折舊再加上當期的固定資產投資,第一產業固定資產投資數據來源于各地市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1990—2014)。δ的取值參照Hall & Jones(1999)的做法[10]83-116,令其為6%。基期資本存量參照Young(2003)的做法[11]1220-1261,用各地區1990年第一產業固定資本形成額除以10%作為該地區1990年的農業初始資本存量。
據前文理論分析,影響農業生產率變動因素包括經濟增長、農業產業結構、農民收入、農業基礎設施、農業固定資產、工業化率、城鎮化率、財政支農、農村人力資本等。由于農村人力資本的數據統計缺失,因此我們選用了前8個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經濟增長采用各地市的GDP來表示;農業產業結構用農業產值占農林牧副漁產值之比計算得到,用NYJG表示;農民收入使用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SHR)表示;農業基礎設施主要是指農田水利投入形成的資產,由于相關統計不可得,我們采用有效灌溉面積(GG)來代替,因為農田水利投入最終將會通過有效灌溉面積的增減表現出來;農業固定資產主要體現在農業機械的投入,因此采用農業機械總動力(JX)表示;工業化率用第二產業總產值占GDP的比重計算得到,用GYH 表示;城鎮化率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計算得到,用CHZH表示;財政支農用支援農村生產支出、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的事業費、科技三項支出等加總計算得到,用CZH表示。表1給出了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數據均據《山東統計年鑒》(1991—2015)的數據計算得到。
(二)模型檢驗與建立
首先建立了以山東省17地市為截面、1991—2014年為時序的面板數據計量經濟模型來分析山東省1991—2014年的農業生產率影響因素。在建模過程中,我們將所有變量都進行了取對數處理,得到了一個雙對數模型。根據面板數據模型理論,模型應該采用何種形式需要進行F檢驗、BP檢驗和Hausman檢驗。用F檢驗來確定采用混合OLS模型還是固定效應模型,其原假設為采用混合OLS模型;用BP檢驗來確定采用混合OLS還是隨機效應模型,其原假設為采用混合OLS模型;使用Hausman檢驗來確定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還是隨機效應模型,其原假設為采用隨機效應模型。表2中的模型1給出了檢驗結果和回歸結果,從F檢驗的結果可以看出不應采用混合OLS模型,從BP檢驗結果也可以看出不應采用混合OLS模型,從Hausman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應該采用固定效應模型。表2模型1給出的是固定效應的結果。
表1 相關數據的描述性統計

NPGDP(億元)SHR(元)NYJG(%)JX(千瓦)GG(千公頃)GYH(%)CHZH(%)CZH(萬元)均值1.0861126.124518.6956.234763515289.4552.8633.6699764.33中位數1.072642.133531.3257.66354278282.1651.6532.4327213最大值4.9798692.11746174.3015228871628.0589.1172.34874532最小值0.1689.13625.762.7736789135.8219.635.32475標準差0.2491242.373376.4311.553262751149.6611.7313.37153276.81樣本數408408408408408408408408408
表2 模型回歸結果

模型1:ln(NP)模型2:ln(NP)C2.7149???(5.0924)0.2391(0.4497)ln(GDP)0.1409???(5.5863)0.1185???(5.224)ln(SHR)-0.1206???(-3.1919)-0.1814???(-3.5477)ln(NYJG)-0.017(-0.5592)-0.0119(-0.3384)ln(JX)-0.146???(-3.28)0.1964???(3.9432)ln(GG)-0.1591??(2.1923)-0.3722???(-5.267)ln(GYH)0.1849???(4.174)0.1092??(2.1015)ln(CHZH)-0.0532(-1.5072)-0.101??(-2.4079)ln(CZH)0.0022(0.2032)-0.0267??(-2.0863)D?ln(GDP)-0.036(-1.1077)D?ln(SHR)0.1873???(2.7663)D?ln(NYJG)-0.0037(-0.0876)D?ln(JX)-0.1876???(-4.9199)D?ln(GG)0.3865???(4.0178)D?ln(GYH)0.0067(0.114)D?ln(CHZH)0.1133??(2.2037)D?ln(CZH)0.0269??(2.006)F檢驗F(16,366)=2.18(p≈0.0056)F(16,358)=2.39(p≈0.0021)BP檢驗chi2(1)=22.64(p≈0.0000)chi2(1)=32.76(p≈0.0000)Hausman檢驗chi2(8)=34.34(p≈0.0000)chi2(16)=36.46(p≈0.0026)調整的R20.14950.4575F值3.8563(p≈0.0000)11.2761(p≈0.0000)
注:括號內為各系數所對應的t值,***、**、*分別表示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
(三)模型結果分析
模型1調整的R2雖然不是很高,但從F值來看,拒絕了所有變量聯合起來對被解釋變量無影響的假設,表明該模型的總體擬合效果較好,各解釋變量聯合起來對被解釋變量有顯著影響。從各解釋變量影響顯著性的t檢驗來看,除了農業結構、城鎮化率和財政支出的影響不顯著外,其他所用變量都在1%和5%的顯著性水平下對農業生產率變動具有顯著影響。前文曾經提到,農業生產率與經濟增長具有相互影響的辯證關系,其中農業生產率變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前面已經得到實證檢驗,而經濟增長對農業生產率的作用在此也得到了實證檢驗。由ln(GDP)前面的系數可知,當山東省GDP增長1%時,山東省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增長0.1409%,顯然經濟增長對農業生產率的增長具有明顯的正向影響。ln(GYH)前面的系數為0.1849,表明當工業化率增長1%時,山東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增長0.1849%,表明工業化水平的提高對農業生產率增長具有顯著正向影響。ln(JX)、ln(GG)和ln(SHR)前面的系數分別為-0.146、-0.1591和-0.1206,表明當農業機械總動力增長1%時,山東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增長-0.146%;有效灌溉面積增長1%,山東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增長-0.1591%;農村居民人均年純收入增長1%,山東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增長-0.1206%。這說明農業固定資產、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和農村居民收入水平都對山東農業生產率的增長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從具有顯著影響的這幾個因素的系數大小對比來看,工業化水平提高對山東農業生產率增長的作用最大。
盡管在以1991—2014年為時序的面板數據模型中,農業資產、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和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對山東省農業生產率的影響為負,但并不意味著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也會如此。為了檢驗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山東省農業生產率變動影響因素的作用是否會有明顯不同,我們引入了虛擬變量D,設1991—1996年間,D=0;1997—2014年間,D=1,虛擬變量仍以乘法方式引入模型。表2中模型2給出了檢驗結果和回歸結果,根據F檢驗,不應采用混合OLS模型;根據BP檢驗,也不應采用混合OLS模型;根據Hausman檢驗,應該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因此,表2中的模型2給出的是固定效應結果。模型2中調整的R2也不是較高,但從F值來看,所有解釋變量聯合起來對被解釋變量有顯著影響。下面從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前后來比較分析影響山東農業生產率變動因素的作用情況。
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虛擬變量D=0,因此各變量的效應不需要加上D與各變量相乘的部分。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前,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經濟增長對山東農業生產率變動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經濟增長這一變量的作用方向與1991—2014年整個時期的作用方向一致。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前,對山東農業生產率有顯著正向影響的還有工業化水平和農業資產的變動,兩者分別在5%和1%的水平下通過了t檢驗,與模型1不同的是,農業固定資產變動的效應此時為正。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農村居民收入、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城鎮化率和財政支農對山東農業生產率變動都具有顯著負向影響。與模型1相比,農村居民收入和農田水利設施變動的效應方向一致,但城鎮化率和財政支農變動的效應由不明顯變為明顯。農村居民收入之所以為負效應,原因在于,農村居民收入的增加首先滿足其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其次才用來進行農業生產工具和技術的使用,但在達到中等收入之前,農民的收入還較低,不但不能進行先進技術的引入和采用,還會因為急于追求收入的增長而采取粗放的生產方式,破壞和掠奪土地和水資源,從而導致農業生產率較低。農田水利基礎設的效應之所以為負,原因有兩方面:一是用灌溉面積來代替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不夠全面;二是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只對種植業和林業生產率的提高起作用,對牧副漁業生產率的提高沒有直接影響;三是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由于收入較低,基礎設施投資建設的質量不高,因此導致對農業生產率的影響為負。城鎮化率對農業生產率變動的影響為負,其原因在于隨著經濟改革和發展,大量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但如果轉移速度過快,而工業化水平的提高還沒有帶來農業生產資料在量和質上的提高,則農業生產率會因為勞動力減少而替代投入的缺乏降低,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的情況可能正與此相同。財政支農投入變動對農業生產率的效應為負是因為在收入水平還較低時,由于重視工業發展的思想還較重,對農業的財政支持還較少,因此很難快速提高農業科研水平和生產能力,而且此時財政的支持還可能導致依賴思想,不思農業生產率提高,從而導致農業生產率下降。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農業產業結構調整的變化對農業生產率的影響不顯著,原因在于山東農業產業結構中種植業占農林牧副漁業的比重下降,而林牧漁業又具有勞動力密集使用性質,在收入水平較低時,農民沒有能力采用先進的生產工具代替勞動力,因此林牧漁業比重的上升反而造成農業生產力下降。
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虛擬變量D=1,此時各變量對農業生產率的效應都需加上D與各變量相乘的部分。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經濟增長對農業生產率的影響由于D*ln(GDP)前的系數不顯著,因此仍為0.1185,表明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經濟增長對山東農業生產率的變動仍與之前一樣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與此類似的是工業化率變動對農業生產率增長的效應也因為D*ln(GYH)前的系數不顯著而與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一致。這表明經濟的增長和工業化程度提高一直對山東農業生產率變動具有明顯正向效應。由于D*ln(SHR)前的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因此農村居民收入對農業生產率變動的效應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變為0.0059(-0.1814+0.1873),很明顯負效應轉變為正效應,這主要是因為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后,農民的收入水平也逐漸提高,從而除了消費外有更多的剩余資金來購買先進的農業生產工具和采用先進的生產技術,而且隨著收入增加,也不會急功近利地采取粗放的生產方式,從而保護了土地和水資源,提高了農業生產率。D*ln(JX)前的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因此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農業固定資產對農業生產率變動的影響為0.0088(0.1964-0.1876),與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降低,但仍為正向效應,效應之所以會降低是由于農業資產數量的增加逐漸趨于飽和狀態,因此邊際效應下降。D*ln(GG)前的系數在1%的顯著性水平顯著,因此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對農業生產率變動的效應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為0.0143(-0.3722+0.3865),由之前的負效應變為正效應,這表明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的水平和質量不斷提高,有力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率增長。D*ln(CHZH)前的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因此城鎮化率變化對農業生產率變動的影響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變為0.0123(-0.101+0.1133),也是由之前的負效應轉變為正效應,表明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隨著收入的增加,農業勞動力的減少逐漸由先進的農業生產設備彌補,提高了農業生產率。D*ln(CZH)前的系數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表明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財政支農對農業生產率的影響變為0.0002(-0.0267+0.0269),該效應雖然很小,但卻是正向影響。這說明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對農業生產和科技的支持效果逐漸轉化為生產力,提高了農業生產率。D*ln(NYJG)前的系數不顯著,而由于ln(NYJG)前的系數也不顯著,因此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農業產業結構對農業生產率變動的作用仍然不顯著。從系數大小的比較來看,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對山東農業生產率影響最大的因素是經濟增長和工業化程度提高;其次是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城鎮化水平、農業固定資產、農村居民收入和財政支農。
四、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的結論主要有:
第一,經濟增長和工業化水平的變化對山東農業生產率變動都具有顯著正向效應,而且無論是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還是之后,該效應一直為正,且不具有明顯差別,兩者對山東農業生產率變動的影響效應也是最大的。
第二,農村居民收入、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城鎮化率和財政支農的變動對山東農業生產率變動的效應由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的負向效用都轉變為之后的正向效應。
第三,農業固定資產變動對山東農業生產率變動影響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前后都始終為正,但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的正向效應明顯降低。
第四,農業產業結構變動對山東農業生產率變動的影響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前后都不顯著。
[1]Hayami Y. & Ruttan V. W.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Among Countri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60(5).
[2]Yee J., Huffman W. E., Ahearn M., Newson M. Sourc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at the State Level, 1960-1993[R]. Staff General Research Papers 5331, 2002.
[3]Dias Avila A. F., Romano, L., Garagorry, F.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nd Sources of Growth [J]. Handbook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0, (4).
[4]Camelia B. Determinants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Among Romanian Regions[J]. Annales Universitatis Apulensis Series Oeconomica, 2012, 14(1).
[5]石慧,吳方衛.中國農業生產率地區差異的影響因素研究——基于空間計量的分析[J].世界經濟文匯,2011,(3).
[6]潘丹.考慮資源環境因素的中國農業生產率研究[D].南京:南京農業大學,2012.
[7]李谷成,尹朝靜,吳清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與農業全要素生產率[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5,(1).
[8]Caves D. W., Christensen L. R., Diewert W. E. The Economic Theory of Index Number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Input, Output, and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1982, 50(6).
[9]Fare R., Shawna G., Norris M., Zhang Z. Productivity Growth, Technical Progress, and Efficienc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84(1).
[10]Hall R. E. & Jones C. I. Why Do Some Countries Produce So Much More Output per Worker than Other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9, 114(1).
[11]Young A. Gold into base metal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3, 111 (1).
(責任編輯 魯守博)
公茂剛,男,山東蒙陰人,山東理工大學商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經濟學博士;王學真,男,山東臨朐人,山東理工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2017-01-23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國際糧食價格形成機理及我國爭取國際糧食價格定價權的策略研究”(13CJY103);山東省軟科學項目“中等收入背景下山東省提高農業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的對策研究”(2014RKB01110)。
F323.5
A
1672-0040(2017)03-0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