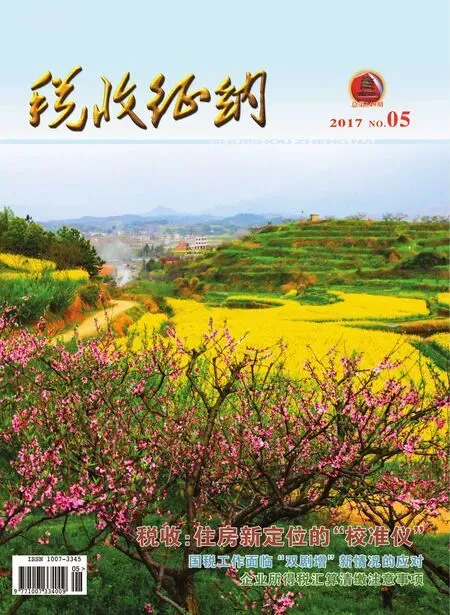下鄉收屠宰稅的那些日子
王國軍
(隨筆)
下鄉收屠宰稅的那些日子
王國軍
兒時,在我幼小的心靈里,深深地烙下了農村叔叔伯伯們的一句口頭禪,那就是“種地交皇糧國稅,殺豬先扯稅票”,包括我家里也是這樣,每年喂大一頭肥豬,先要在村會計那兒扯2.5元的稅票,有時國家統購,只能留下半邊肉,這是天經地義的原則,誰也不能違背。
這遺留下的規定持續了60年,在歷史的長河中也不過是短短的一瞬間,可是作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發起者”和突破口的稅制改革,恰恰就是在歷史的長河中以“大風起兮云飛揚”的浩蕩氣勢,讓我回想起了許許多多我親身經歷和在農村千家萬戶收屠宰稅的故事。
從青年到成熟,不知不覺從事稅務工作已經42年了。1971年初,我被分到家鄉羊尾區財稅所工作,當時黨中央提出:“三線建設要抓緊”,這是同帝國主義搶時間的口號,要修通襄渝鐵路的戰略意義不言而喻。沿線十幾萬人,為了這么多的人生活,僅羊尾一處,就專設出納雙人上崗,每天支付款30—50萬元以上,排隊取錢從上街排到下街,幾乎沒有上下班時間。沿漢江上下,不知還有多少個點在為三線建設服務。1973年財稅銀分家,我被分到稅務所當專管員,所里只有一位姓王的所長、一名會計,包括我在內共3人,管轄著7個小公社,38個村,固定納稅130余戶,臨時釀酒1100余戶,火紙廠28戶,其他行業340余戶,年稅收46萬元,還負責全區屠宰稅收的征收管理工作。
第一天下隊,我背著縣稅務局給我發的黃布挎包、軍用水壺和一把布雨傘,在會計那領了一本三聯稅票,這是我第一天下鄉,羅會計把我送到二十里外的老官廟村,河對岸是白河縣城,羅會計說,就從這里上山到聯盟大隊找張會計。我想,雖然是本地人,沒有到農村去過,也是人生地不熟,第一次下隊收稅,要麻煩大隊、小隊會計,于是,我到商店買了一條7元錢一條的山羊牌香煙裝到挎包里,煙是介紹信嘛,聯系工作方便。就這樣走小路上山,到大隊會計家有七、八里地,在他家的菜地里找到了張會計,我先介紹自己,是羊尾稅務所的,來聯系稅收工作。張會計說,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四回吃豆腐,都是本地人好說。
張會計很客氣地把我領到他家里,趕忙把媳婦叫回來做飯,晚飯菜不少,有鮮魚有臘肉,還熱了一壺柿子酒。我問他那有現成的鮮魚啊?他說,前兩天家里來客,我們在大河里炸的,一炮下去炸了好幾百斤,還是你的口福好,正趕上,我們倆邊說話,你一杯我一杯地喝著酒。因為天色已晚,我只有在會計家留宿一晚。
那個年代農村稅收主要是酒稅和屠宰稅,在冬臘月村民們殺豬的特別多,于是我和張會計一起到小隊了解每戶殺豬情況。就這樣,兩年多來,我翻山越嶺,爬山涉水,跑遍了羊尾所有的地方清理屠宰稅。有一天,我跟著東方村王會計,清理上一年的屠宰稅,30多里崎嶇的山路,用了2個多小時找到該生產二隊張隊長的家,張隊長熱情地接待了我們。
說明來意,張隊長很快搬來桌椅,墊上報紙,從里屋拿出賬本和屠宰稅票等的資料。在半個多小時,我們從上年度的年報和有關花名冊的統計,掌握了村民的數量,全隊只有131戶,報屠宰稅118頭;其中有7戶是獸醫站開出的證明,證明農戶飼養的豬因病溫而死;有5戶沒有喂養生豬,這7戶之中有群眾證明,每份證明上必須有當地群眾3戶的戶主簽字蓋章才有效,而有1戶的證明上只有2人簽字蓋章。我們追根到底問是什么原因,張隊長才說出真情,是他妻子的弟弟沒有報稅。
飯后,我們與張隊長走了2里多路,找到他的妻子弟弟小李。見到小李,小李說:“我今年沒有喂豬,我小哥可以證明,不信,你問他?”接著,王會計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說道:“征收屠宰稅是國家政策,不要欺上瞞下,要尊重事實,你說你沒有喂養,為何沒有3戶農戶給你簽字,你的山墻上掛的肉塊是哪來的?”此時,王會計看到一個大約4歲的小男孩從外邊玩耍回來。王會計立刻走到門外邊,抱起小男孩跟他說:“你剛才在哪玩?過新年你爸爸給你買的什么衣服?豬肉好吃嗎?去年殺豬沒有?”,小男孩說道:“過新年殺好大的豬喲”。小李的臉全紅了,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要求補辦屠宰稅票。當我們走時,張隊長和小李送我們1里多路,張隊長對小李說:“2.5元的屠宰稅,錢少事不小,“稅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生”,小孩的心靈無欺,將來要培養他們做一個誠實的公民,今后,你要支持你姐夫的工作”。那個時侯屠宰稅還是主體稅種之一,農民飼養生豬還必須在殺豬時,為國作出一份貢獻——繳納屠宰稅。
1991年,由于風調雨順,農作物大豐收,鄰居表姑家的年豬喂得肥又壯,眼看快要過年了,想殺豬還沒有扯到稅票。她對我說,她3次到大隊會計家沒有扯到稅票。我問是什么原因?她說:“過年要殺豬必須先繳清合同款(包括農業稅、特產稅、教育附加稅、以及各項集資和農村義務工)才能扯到稅票”。羊尾是貧困地區,許多農民為此事發愁,經常與大隊會計發生爭吵。聽到這個消息,我們上門找到本大隊的陳會計,對陳會計講稅收道理,屠宰稅不要與各項集資款混在一起,讓老百姓交“明白稅”,如果群眾有錢的話,可以先交單項,再逐項全部交清,這叫做“化整為零”收繳方式。你把各項集資款和稅款“捆綁”一起,老百姓哪有現錢呢?又不是拿工資的。
后來,陳會計按照我們的方法去辦,果然見效,率先完成了“合同款”。而其他大隊的老鄉們沒有自覺去報屠宰稅,大隊會計為了收齊“合同款”,經常與村民發生沖突。那時,各地征收屠宰稅都遭到收“合同款”的制約。農民過年殺一頭豬,首先要大隊里出證明、再到鄉里進行批復同意宰殺,然后到稅務部門扯稅票,再經過獸醫站檢疫蓋章,才能上市。
1994年的下半年,分稅制改革,我已調到縣國稅局城關分局辦稅廳分管發票工作,屠宰稅由地稅局征管。那個年代農村流行一句順口溜:“頭稅(農業稅)輕,二稅(提留統籌)重,三稅(集資攤派)是個無底洞”;而屠宰稅出現按‘人頭’攤派的情況,每戶按30元征收的事情,地方政府鼓勵農民多養豬,每年要求每戶出售生豬1頭,由出售者向買方征(稅負轉價)18元,每年每戶自己屠宰1頭豬,報屠宰稅2,5元,合計每戶必須要征收30元。針對這種情況,縣地稅局還為此專門下文明確指示各鄉鎮稅務所:“屠宰稅要依率計征,據實征收,不再由出售生豬的戶主代征,若遇到亂集資、亂攤派、亂收費,老百姓有權拒絕”。
農村屠宰稅的風波不斷涌起,甚至有令不止,依然“我行我素”。但是屠宰稅的故事沒有結束,持續到2006年上半年不再上演了。隨著國家稅收政策的調整,屠宰稅已成為了過去。取消屠宰稅后,如今我們已不必為那幾個小稅而花上那么多的心血去征收和管理了,養豬的農民也不要為只有微薄的利潤去繳納各種稅費。這樣的故事已經不可能再發生,而我在收屠宰稅中揮灑在農村青山綠水里的青春和汗水,則永久留在了我心里。
從改革開放到現在,30年彈指一揮間,中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稅費改革及農村綜合改革,再到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中國農村經歷了歷史性的變革。農村經濟實現了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的巨大轉變,中國農業從傳統農業邁向現代農業的新方向,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也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關注民生的呼聲越來越高,農民得到的政府優惠政策越來越多,得到的實惠越來越多,生活水平自然也越來越高。
國家的惠農政策逐步加大,農民享受的實惠越來越多。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以前農民交的“五稅”,過去,農民家里有輛自行車得交車船稅,殺口豬得交屠宰稅,種點來錢的經濟作物得交特產稅。現在農民不僅不交各種稅費,國家的各種補貼“名目繁多”,糧食直補、生產資料補貼、農機具補貼、沼氣補貼、政策性保險、合作醫療、教育‘兩免一補’等等,哪一項不是在往農民兜里塞錢。
近兩年,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每天想的就是如何讓農民生活得更好。“稅收取之于民、稅收用之于民”的屬性得到充分體現。農民的日子過得越來越甜密,金光大道的路越走越寬,在富民政策頃斜下,農民會勤奮努力發家致富,在不久的將來,會過上幸福小康之家的生活。
青海湖畔
作者:王永沛

光圈:13速度:1/160感光度: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