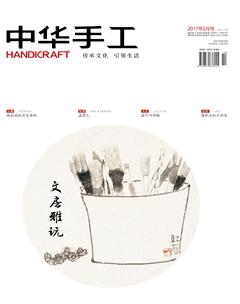石路石橋石頭村
青簡


石頭 泥土 草葉
勝坑村并不大,幾乎一眼就能看得盡。但那些石墻的角落、石塊的縫隙里,除了泥土草葉,藏了太多和時間有關的東西。想要看得仔細,怕是幾天也不夠。
在草宿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依舊陰沉,濃云不肯多漏一絲天光給這個山坳里的村子。深淺不一的石頭,赭、褐、灰、黃色都有,覆著深黛色的瓦,紛紛默立在蒼煙墨綠間。一條清溪縱貫全村,小溪兩岸,是久經滄桑的石頭房。嶙嶒的石頭,經過風雨的打磨,歲月的銷蝕,不再突兀,卻依舊保持著石頭本身的厚重,又顯露出了它們的圓潤。
溪水不深,很多處藏在叢生的蒹葭下。聽見潺潺聲,才知道是活水。鴨子們卻比誰都清楚,轉眼不知從哪里冒出來一群。也不怎么-怕人,等走近了,才慢悠悠地往前游一小段。遇見石頭擋道,就索性抖擻抖擻羽毛跳上去,搖搖擺擺挪上幾步。
村里人很少,偶爾所見都是垂暮老者。沒有太陽,石階上卻曬著長而細的草。村口有婆婆在編著草帽,饒有興致地看了半晌。“上次買了一頂,太淺了,根本戴不上,只是,改一下樣式她們就不會編了。”朋友說這種草還能做蠟燭芯,是村民在種地之外的一點小收入。
沿溪水往上游走去,路的盡頭有幾處田地,再往前就是竹林和群山。回程特意選了一條坡上的路,可以俯瞰大半個村子。遠遠望去,村子的墻是石頭的、地面是石頭的、臺階是石頭的,那種綿延不盡的石頭仿佛把人拉到了遙遠的異國。無論是斑駁的色彩,不斷重復的小塊面,還是簡潔的外部線條,都會讓人想到濃墨重彩的油畫,而非淡雅的中國寫意山水畫。石頭這最接地氣的建材,競打造出一個如此洋氣的村子。似乎暗合了沿海地區外向的性格,可再西化的墻體,也裝著窄小的門窗,又回歸到農村傳統的內部空間。
質樸土氣的材料、開放洋氣的村落、封閉內斂的房屋,似乎普通的石頭非得如此走一遭,才能實踐它完整的使命。
石頭是硬的,叫人想起魯迅先生所稱頌的“臺州式的硬氣”。然而,即便如此硬氣的村子,也沒法跟上城市化腳步。村里近一半的房子都已廢棄。來自大地的石頭,或許終將被時間消化,重歸大地。
民居 草宿 風景
不得不說,傳統的石構民居在居住上存在缺陷,這大概才是最終遭淘汰的原因吧。或許,用現代建筑和美學手段能將它們的缺陷改進。
我們人住的草宿,是輝哥和水草用老房子改造的一處民宿,在村子的最高處。租下房子的前半年,他們走訪村里的居民,觀察民居格局,聽取居住感受,請教有經驗的老匠人……準備充分后,才開始改造。
他們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建筑外立面,尊重建筑和空間的本質,就地取材,和整個大環境融合。歷經加固、防潮、隔音等挑戰,從設計到完成用了3年。草宿增加了一些現代設計元素,但是從整體上看,還是一幢石頭房子。和村子保持一定距離,但又融人其中。這種非侵略性的進入,使得整個村子變為草宿的大背景,而草宿,也成了勝坑村一道美麗的風景。
其實,好的建筑空間不但能帶來美感,更能激發功能,引起互動與共鳴。草宿便一直在努力,想要把民宿做成一個超越住宿的平臺。
勝坑村有原生態的自然環境、流動的人文氣息,非常適合藝術創作。輝哥和水草就以房間換作品的方式,定期邀請作家、藝術家和創意人士來住,用本地素材或吸取靈感進行對話和創作。村子里的留守老人有些會做草編,但是編出的草帽缺乏現代審美,價格也低廉。他們嘗試努力整合創意人員,就當地元索進行設計,培訓當地手藝人,想做出符合現代生活美學的草編產品。
美麗的建筑被廢棄,多數人會惋惜,重建又擔心會改變原貌。其實什么都不去改變,也會改變,自然的力量讓它倒塌消亡。如果任憑勝坑村自然發展,很難留住來客。與其交給村民們做成農家樂,不如由外來者做一些挑戰。譬如草宿,譬如莫干山那些民宿……
離開那日,早上太陽從云層里冒出,灑下了少許光芒。雖然稍縱即逝,頓時讓木葉生輝,石頭明亮。水草問我會不會再來,我說一定會的,哪怕等我老了。畢竟生命總長不過石頭,只要石頭還在,勝坑的美就不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