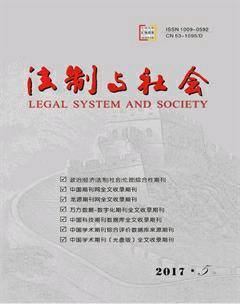婚姻暴力與家國同構淺議
摘 要 近年婚姻暴力仍明顯存在且程度嚴重。對此,本文主要以文獻研究方法,結合歷史與現狀,選取歷史發展中幾個代表性時期男性權力膨脹與女性權力萎縮的事實,嘗試從一新的視角,即家國同構,主要是男權社會中國家權力在家庭中的滲透及相應結果的角度,對家庭中丈夫對妻子的暴力行為進行一定層次探源。說明家國同構的歷史傳統及結果對婚姻暴力的深遠影響,據此探討受害婦女及整個女性群體主體和參與意識。
關鍵詞 家國同構 婚姻暴力 自我覺醒
作者簡介:原偉霞,浙江樹人大學人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行政管理學和社會學。
中圖分類號:C913.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5.367
一、引論
人類社會有史以來即存在三大沖突,其中產生最早,涉及面廣,消亡地最慢的沖突就是性別沖突。其明顯而持久的體現即性別歧視,對社會中女性的歧視。雖然,我國婦女群體的健康、就業、教育等方面都得到了一定提高,但可喜的數字下面卻掩蓋著古老得易被遺忘的事實:婚姻暴力。
根據學者定義,婚姻暴力指的是婚姻當事人對配偶實施身體的傷害行為,其中主要是男性憑借體力和社會資源的優勢各種等對妻子的生命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的現實和潛在暴力行為。 天津某區法院100個離婚案件中有52例是由丈夫施暴引起的;遼寧女性犯罪由家庭暴力所致的高達80%;武漢市婦聯接待的上訪婦女中,1/3因為家庭暴力前來投訴。據抽樣的基層法院起訴離婚案中30%是丈夫毆打而導致離婚。
1975年《墨西哥宣言》特別對男女平等做出界定:男女人格尊嚴和價值的平等,以及男女權利、機會和責任平等。四十多年后的中國,《反家庭暴力法》才終于出臺,專家們還在期待其可操作性的加強。家庭中的婦女連基本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更別說人的尊嚴和價值了。在中國女性主義“反對家庭領域對婦女的暴力”的呼吁中,政府遲遲才做出反響。相關學者曾疑問:是中國的人權意識需要強化嗎?是性別的覺醒還不夠嗎?問題的背后是更為深層的原因,即家國同構的影響。
二、家國同構對婚姻暴力的影響
(一)家國同構
筆者著重時空邊界共生性,模糊國家階級屬性,從政的層面解釋國家內涵。家國同構,則著重家國共進的歷史進程及在這個進程中,男權社會的國家權力在家庭領域的投射和最終的滲透。強調自古至今,家與國在統治權力上的統一,即家國在領導體制上的同構。
隨著氏族社會向階級社會轉變,國家概念開始起源,當國家作為一個固定詞語出現,家庭便也開始作為國的基本單位被定義,成為國家統一的保證,同時,宗法政治以“家”的主從關系構建“國”的政治關系。國家最初借鑒了家庭的治理關系,但投射回家庭的卻是異化之后的統治關系。當以家庭為基礎的國家成為整個社會的統治力量之后,家與國在從屬的體制下同時存在了二者并行的同構過程。這一過程同時也是男性壟斷配置性資源和權威性資源的過程。
(二)家國同構的歷史與現實
以下幾個歷史片段說明女性由社會跌落回家庭,最終將自己固化在婚姻關系中的過程。這個過程由男性主導,女性逐漸同意參與為主要特征。
周代:國家出現——婦女退居家庭(經濟)。兩周建制,完全實行了男女公私內外分工制度。男性在同自然的斗爭中日益顯示強于女性的力量,節節敗退的婦女以退卻求生存,退回家庭發揮自然功能。這種分工模式給兩性帶來巨大影響,從根本上改變了性別平等關系和關于性別的價值觀和道德觀,造就了男性對權勢、武功和財富的崇拜,形成了男性獲得資源的廣泛社會基礎,失敗者在家庭中保有擁有妻婦和奴隸的權力。退回家庭的婦女不得不屈從于男人設就的生活規范和既定角色,從而開始形成婦女無權和隱忍的經歷,形成了婦女是無能的短視的偏見,婦女本身也就開始淪為歷史沉默群體。發軔了婦女的階級身份的家庭地位是以男性的身份地位決定的性別制度基礎。同時,婦女的經濟資本在未充分獲得的條件下卻面臨喪失。
漢代:獨尊儒術——貴陽賤陰(文化)。董仲舒利用國家統治力量將改造后的儒學提升到主流社會意識高度。用“天道貴陽賤陰”論證妻子應服從丈夫。國家層面上的陽性思維的廣為蔓延鞏固了父權、男權文化,使已經退回家庭的婦女進一步喪失女性話語的權利。漢代文化資本的剝奪則使婦女在以夫妻關系為主的家庭中不得不面臨服從的境況。
宋代:強化專制——父權制(政治)。自宋代起,家庭已成為決定中國人生活的社會、政治形式的縮影。在國家的統治階級強化了封建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和建立了等級森嚴的社會的同時,家庭也日益成為父權制社會的典范,男人在擁有全部家產的同時也掌握著女人的生死大權。這種夫與妻的關系,具有超越一般君臣關系的特點,不需要經過嚴格的法律程序,只需要以丈夫的意志為基礎,從而使丈夫打妻子成為天經地義的事情。
清末:改良——無法完全的脫離(婦女解放)。從戊戌到五四,先進知識分子對婦女解放的倡導,使男性成為婦女個性解放的倡導者、發起人。婦女解放的一切措施和綱領都成為整個社會革命和思想啟蒙的總綱領,使中國近代的婦女解放運動從思想基礎到組織形式都帶上了男性化色彩。及至中國的革命運動被納入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體系,性質模糊的婦女解放運動作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一部分納入國家目標之中。由于中國婦女的解放從一開始就沒有突出女人的主體地位,沒有突出性別之間的文化色彩,而始終借助超越性別的社會革命或運動來帶動促發,注定后來在“男女都一樣”的口號中失去女性自主發展的有效空間。意圖脫離家庭困境的女性卻在國家的控制之下被加以工具化的色彩。
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女性需要的湮滅(政權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后,所有通向權力的途徑,全部掌握在男人的手里;從國家政策來看,人們制定制度與原則時,主要是根據男性的思想和利益,繼承了男性強勢文化。這一切都沒能表達女性的需要。
(三)家國同構對婚姻暴力的影響
社會交換理論認為,資源占有的不平等是產生權力的根本原因。隨著女性經濟文化社會資本的失落,男性完成了國家公共權威和家庭局部權威的壟斷,并且完全按照男性意志來統治女性。在古代,男尊女卑、夫為妻綱的夫婦關系成為組成家庭結構的主導因素。家庭外以國家形式存在的社會、道德、法律,都要求已婚婦女無可避免地完全接受丈夫的性情,父權制在家庭中如魚得水。從這個角度講,針對女性的婚姻暴力理所當然地被認為是父權私人領域的事情,而限制了婦女介入的男人們所享受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權力,則構成了家庭之外的由男人壟斷的公共領域。兩個領域的劃分體現了家國同構的一致性和家國之間的妥協。
現代制度經濟學認為,一個社會集團力量的大小,并不取決于它的人數多少,而是取決于它的組織程度。由于既定資源的缺失和現存資源的缺乏,使廣大女性在以男性為主的龐大的國家權力之下,仍然處于權力的邊緣位置,不能進入權力的中心。既失去了競爭的優勢,又要爭取平等的地位,這本身就是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在這個尷尬的情境中,在歷史的慣性作用下,婦女對獲得生活必需品的來源的無把握的心理會造成它們對被剝奪生活必需品的恐懼,不敢冒險,自愿從屬于他人。反抗是一種能力,適應制度取得生存空間也是一種能力。婦女往往以退回家庭來逃避它們在家庭外所面臨的種種歧視。
但是,家庭權力和政治的一致性使男性在掌握國家權力的同時,也掌握著家庭內部的權力。婚姻從夫居和夫系繼承制的傳統使家長制在以戶為單位的分配制度中得到延續,使已經參加了社會生產的婦女并沒有獲得實際上的經濟獨立。同時由于家庭中生產資料的男性占有,使經濟上和精神上不獨立的女性依然無法擺脫依附男性的命運。她們只考慮到周圍人的需要,而忽視了自己的需要以及自己與一般公共生活的緊密聯系。在傳統的男權文化的統治下,女性是公認的婚姻關系中受剝奪的群體,女性對于婚姻的貢獻遠遠大于她們在婚姻中所獲得的利益。在根深蒂固的權力情結的支配下,男性依然努力維持他們在社會上的和家庭中的一家之主的傳統角色,他們要繼續迫使女性馴服于他們的領導。因而婚姻暴力繼續陷入家庭——私域的圈套。
既然家國同構與婚姻暴力之間存在如此緊密的聯系,那末是不是婚姻暴力的消亡也要取決于國家的消亡呢?這的確是國家努力的最高目標,而這種想法卻又將女性再一次置于最高目標之下。因而,筆者傾向于從現實出發,運用理論上十分傳統但實踐上有所欠缺的觀點來希望緩解這種狀況。
三、女性的自我覺醒和主動參與
吉登斯認為,權力是在支配結構之中生成的行動的普遍性質,所有的權力都是雙向分布的。對在家庭中深受傷害的女性來說,要想獲得操縱資源的方式,必須首先在個體意識上作自我表現肯定,認同自我表現主體性,即主體意識覺醒。
從女性自身發展的角度看,群體意識較強,個體意識較弱,自我發展的觀念相對較差。在國家的男權統治秩序下和家庭中夫權唯上的鉗制下,不平等的社會準則內化到女性的心理中,成為大多數女性價值系統的組成部分。受害婦女往往不輕易接受甚至并不認同本屬于她們的權利。因為那意味著她要改變那些植根與家庭、社區、國家中的傳統觀念,將自己視為獨立的個人,而不是因國家、家庭關系被定義的個人。
男女平等具有獨立于國家其他目標本身的重要意義。中國的男女平等將依賴于獨立的婦女心聲的發展,獨立的婦女心聲將表達中國婦女的多種選擇和不同觀念。理論上,應該讓女性有機會用她們自己的術語訴說婦女的生活和體驗,建立一種來自于婦女實際的經驗和話語的理論;實踐上,受虐婦女應首先爭取家庭的發言權,為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質、經濟地位積極參與,主動出擊,賦權自己。只有這樣,婦女才能有接受發展援助的被動者成為推動整個發展進程的一個積極能動的組成部分。
到此為止,本文從事實出發,繼而從價值判斷的角度論及女性問題的一個方面——婚姻暴力問題。這只是婦女權利受到壓抑的一個微小的方面。但就女性群體而言,實現了人的全面發展依然是一個遙遠的目標:它包括生活方式的再選擇,行為模式、角色模式、家庭模式的調適,以及跨越家庭的限制,參與全球行動與競爭的現代化性格的形塑。最后,需引起注意的是布勞的那句:社會沖突的根源在于社會中存在的不平等不被認可。注重社會現實是認清和解決婦女問題的基本起點。
參考文獻:
[1]孫紹先.英雄之死與美人遲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2]徐安琪.婚姻暴力的概念和現狀.社會.2001(2).
[3]姜鍵、姜蘭.婦女解放問題的現代詮釋.社會科學戰線.2001(5).
[4]李銀河.中國婚姻家庭及其變遷.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3.
[5]楊善華.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6]李小江、朱虹、董秀玉.批判與重建.上海:三聯出版社.2000.
[7]李小江、朱虹、董秀玉.性別與中國.上海:三聯出版社.1997.
[8]夏國美.時代的轉化:從解放婦女到解放婦女解放——新時期婦女工作的新理念.社會學.2001(3).
[9]馬元曦.社會性別與發展譯文集.北京: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10]張建波.從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婦女運動的理念轉型.社會.2001(7).
[11]李洪濤.構建家庭-暴力干預的理論體系與工作模式.社會工作(學術版).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