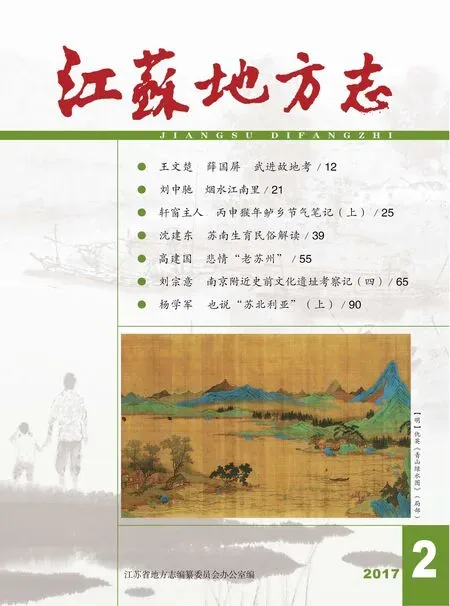武進故地考
◎ 王文楚 薛國屏
武進故地考
◎ 王文楚 薛國屏

常州市紅梅公園 陸志剛等航攝
“武進”一詞,所涉及的歷史沿革及其方域變遷是極其復雜的,這在全國縣級行政區域中是少有的。正因為其少有的特殊性,才引得眾多的歷史學家和地理學家的青睞。在武進歷史上,南朝齊梁兩代帝王的故居在此落戶。圍繞著齊梁故里所在地,武進、丹陽兩個近鄰為此發生了一些爭議。在2009年3月“中國·常州齊梁文化研討會”上,全國一百多位專家一致認為齊梁故里應在今常州市西北。但至今還有少數人對此爭議不休。現實的爭議,還是應由歷史來說話,這就是今日我們撰寫“武進故地考”的緣由。
先談武進縣
全國歷史上有四個武進縣:一是西漢置。治所在今內蒙古自治區林格爾縣東北。東漢末廢。二是三國吳嘉禾三年(234)改丹徒縣置。治所在今江蘇省鎮江市東南丹徒鎮。西晉太康二年(281)復名丹徒縣。三是西晉太康二年(281)分丹徒、曲阿二縣東部地置。治所在今常州市西北。四是唐萬歲通天二年(697)改帖夷縣置。治所在四川省南坪縣(今九寨溝縣)東南。神龍元年(705)復為帖夷縣。廣德后沒入吐蕃。
以上四個武進縣與本文直接有關的為西晉所置的武進縣,其治所在今常州市西北。與本文間接有關的為三國吳所置的武進縣,治今鎮江市丹徒區。有關武進縣的歷史問題,我們以下用歷史資料來撰述。
武進縣縣址考
武進之設縣,歷史悠久,溯源于丹徒縣之改置,早于秦代,已設丹徒縣。
《史記》卷三一《吳太伯世家》:齊相慶封“自齊來犇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為奉邑。”《集解》引《吳地記》曰:“朱方,秦改曰丹徒。”《宋書》卷三五《州郡志》一:丹徒縣,“古名朱方,后名谷陽,秦改曰丹徒。”《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潤州丹徒縣,本朱方地,后名谷陽,“秦以其地有王氣,始皇遣赭衣徒三千人鑿破長隴,故名丹徒。”
秦丹徒縣屬會稽郡,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西漢因之,載《漢書·地理志》上。東漢屬吳郡,載《后漢書·郡國志》上。
三國吳嘉禾三年(234)改丹徒縣為武進縣。《宋書·州郡志》:丹徒縣,“古名朱方,后名谷陽,秦改曰丹徒。孫權嘉禾三年改曰武進。”唐《元和郡縣圖志》卷二五常州武進縣:“吳大帝改丹徒為武進。”宋《輿地紀勝》卷六同。又宋《太平寰宇記》卷九二常州武進縣:“輿地志云吳大帝改丹陽為武進,屬毗陵郡。”“丹徒”作“丹陽”,考《三國志·吳志》卷二《孫權傳》:嘉禾三年,“詔復丹徒為武進。”據此,《太平寰宇記》所云“丹陽”之“陽”為“徒”字之訛。
據孔祥軍《三國政區地理研究》下:武進縣初屬吳郡西部都尉(相當于郡級屯田行政區長官),嘉禾末或赤烏初屬毗陵典農校尉。
這里說一下武進縣之得名。《三國志·吳書·吳主傳》云:“嘉禾三年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眾圍合肥新城。……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楊太守,討山越。……冬十一月……詔復曲阿為云陽,丹徒為武進。”劉熙《釋名》:“晉,進也。”武進取“以武而進”之意。
秦漢丹徒縣及三國吳武進縣治今鎮江市東南長江南岸丹徒鎮。
吳末廢武進縣,西晉太康二年(281)復置,梁武帝改為蘭陵縣。
《晉書·州縣志》:“武進令晉太康二年(281)分丹徒、曲阿立。”
《太平寰宇記》武進縣:“吳末并入晉陵縣。晉太康二年分丹徒、曲阿二邑地立武進縣。”《元和郡縣圖志》常州武進縣:“晉武帝別置武進縣于丹陽縣東五十里。梁武帝改武進為蘭陵,入晉陵。唐垂拱二年(686)又析晉陵西界立武進縣于州理。”據此,三國吳末廢武進縣(治今鎮江市東南丹徒鎮),西晉太康二年于后來唐代的丹陽縣(今丹陽市)東五十里別置武進縣。南宋《輿地紀勝》卷六引唐《元和郡縣圖志》同,可證西晉太康二年重置武進縣已非原址,而在唐丹陽縣東五十里。
但明清諸志都記載在武進縣(治今常州市)西北。明成化重修《毗陵志》卷六《縣治》武進縣:“晉太康二年析置縣在郡城(常州府城)西北八十里千秋鄉,今通江鄉。”《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常州府《公署考》同。清《嘉慶重修一統志》卷八七《常州府·古蹟》亦載:“武進故城,在武進縣西北七十里,晉太康二年置,“唐垂拱二年,復分晉陵西界置武進縣于州郭內,至今因之。”自唐垂拱二年(686)設置武進縣于常州郭內,明清因襲不改,為常州府治,即今常州市,而西晉設置的武進縣在明清武進縣(治今常州市)西北八十里(一說七十里),地名千秋鄉。而千秋鄉有萬歲鎮,明清時稱為阜通鎮。清《讀史方輿紀要》卷二五常州府武進縣:“府城西北六十里為千秋鄉之萬歲鎮,今名阜通鎮。”則西晉太康二年復置之武進縣當在千秋鄉之萬歲鎮,今常州市西北萬綏鎮是也,“歲”、“綏”音近。
這里要說明一下,唐《元和郡縣志》記載:“晉武帝別置武進縣于丹陽縣東五十里。”這在當時是不錯的,到了明清行政區劃變動了。《大清一統志》:“常州府建置:武進縣為常州附廓縣。東西51里,東北65里,東至陽湖縣界1里,西至鎮江府丹陽里50里,西北至丹陽縣界80里。”這時,故丹陽縣東五十里,其行政區域已在今常州市西北。在現今的政區圖上,丹陽離常州市境只有16公里(32里)。可以明顯看出,武進縣故址完全在今常州市西北境內。
《南齊書》卷一《高帝紀》載:齊高帝祖先“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于是為南蘭陵蘭陵人也。”考南宋《咸淳毗陵志》卷二七《古蹟》:武進縣,“蘭陵城,在縣北八十里千秋鄉萬歲鎮西南。齊四世祖淮陰令蕭整僑居之地。按:萬歲寺,舊有偽吳天祚中石刻云,寺西去蕭梁帝祖宅三十里。有無此石刻有待考證。東城寺,初名皇基,更名皇業,寺后百七十步即其城也。”明成化重修《毗陵志》卷三《鄉都》:武進縣十都:“城后,古蘭陵城也。”東城里是蕭齊高帝祖先寓居之地,是蕭氏南渡后發祥之地,故名皇基,又改名皇業,其地在萬歲寺后,萬歲寺在萬歲鎮,故東城即在萬歲鎮,亦是蘭陵縣城所在。
上引《南齊書·高帝紀》所云“東城”,乃指武進縣之東城,《讀史方輿紀要》亦載:蘭陵城,“常州府西北六十里。晉大興初始置南蘭陵郡及蘭陵縣于武進界內,宋因之。亦曰東城,以在武進東也。蕭道成高曾以下皆居武進之東城里,因為南蘭陵人。”顧祖禹之說東城是武進縣之東城,與《南齊書·高帝紀》記載蕭齊高帝四祖蕭整寓居武進縣之東城,即僑置之南蘭陵郡蘭陵縣正相符合。故顧氏確定蘭陵縣在萬歲鎮,之“府城西北六十里為千秋鄉之萬歲鎮,今名阜通鎮,有古青城,城南為圓壇,蓋蕭齊篡位后以蘭陵為其湯沐邑,因置此為郊祀之所。稍西南即蘭陵城也。”
西晉武進縣及東城里(即蘭陵縣城)二地相距甚近,故成化重修《毗陵志·縣治》載:“晉太康二年初置(武進)縣在郡城西北八十里千秋鄉”,《古蹟》載:“蘭陵城在武進縣(常州府附郭,治今常州市)北八十里千秋鄉。”是在同地。而《讀史方輿紀要》記載西晉太康初別置之武進縣在“常州府城西北七十里”,而東晉太興初僑置之南蘭陵郡及蘭陵縣在“常州府城西北六十里”,所記里數與上引《毗陵志》雖有些差別,但據此可知,武進在西,蘭陵在東,相距十里,為咫尺之地,后者為前者之東城。
或據《元和郡縣圖志》“晉武帝別置武進縣于丹陽縣(治今丹陽市)東五十里”之記錄,以謂西晉太康初復置之武進縣治在今丹陽市東五十里。考《太平寰宇記》卷九二常州武進縣:“去州八十里。”又:“晉太康二年分丹徒、曲阿二邑地立武進縣。梁武帝改為蘭陵縣。隋文帝廢。唐武德三年又置。貞觀元年并入晉陵。垂拱二年分割晉陵西三十六鄉又置。”據此,西晉太康初設在丹陽縣東五十里的武進縣及梁武帝改為蘭陵縣的境地,已于唐貞觀元年(627)并入常州治晉陵縣(治今常州市),上引《元和郡縣圖志》文“入晉陵”上缺脫“隋文帝廢,唐武德三年又置,貞觀元年并”共十六字。又《隋書》卷三一《地理志》下:江都郡曲阿縣(唐天寶元年改名丹陽縣,治今丹陽市)“有武進縣,梁改為蘭陵,開皇九年并入。”可見,隋文帝開皇九年,武進縣(梁改名蘭陵縣)境土曾并入曲阿縣,但時間很短,唐武德三年重置武進縣,至貞觀元年又并入常州晉陵縣,其境土已改屬常州,不再歸屬地丹陽縣。《太平寰宇記》記載武進縣“去常州八十里”,仍記載西晉武進縣、南朝梁蘭陵縣及唐武德年間的武進舊縣址(實際武進縣已于唐垂拱初移治常州城內,與晉陵縣分治,詳后),正與上引明清諸志記載在常州府西北八十里(或云七十里)是一致,而無記載在丹陽縣東者。
西晉武進縣屬毗陵郡,載《晉書》卷一五《地理志》下。
東晉武進縣屬晉陵郡,據胡阿祥《六朝疆域與政區》第十二章第二節。
南朝宋屬南東海郡,載《宋書》卷三五《州郡志》一。
南朝齊仍屬南東海郡,載《南齊書》卷一一四《州郡志》上。
南朝梁武帝天監元年(502)改武進縣為蘭陵縣,屬蘭陵郡。
《梁書》卷二《武帝紀》中:天監元年四月,“改南東海郡為蘭陵郡。”《隋書·地理志》下:江都郡曲阿縣,“有武進縣,梁改為蘭陵。”《元和郡縣圖志》:常州武進縣,“梁武帝改武進為蘭陵。”《太平寰記》同。《咸淳毗陵志》卷二《地理》二:“梁天監初,乃改南東海為蘭陵郡,武進為蘭陵。”
隋開皇九年(589)平陳,廢蘭陵縣。唐武德三年(620)重置武進縣于舊址,貞觀八年(634)并入晉陵縣。
《隋書·地理志》下:曲阿縣,“有武進縣,梁改為蘭陵,開皇九年并入。”《新唐書》卷四一《地理志》五:常州武進縣,“武德三年(620)以故蘭陵縣地置,貞觀八年(634)省入晉陵。”《輿地紀勝》卷六同。《太平寰宇記》:武進縣,隋文帝廢蘭陵縣,“唐武德三年又置,貞觀元年并入晉陵。”按此“元年”,當作“八年”為是。隋既廢蘭陵縣,故唐于其舊址重置武進縣,其址如上所述,在今常州市西北萬綏鎮。
其時武進縣屬常州,俱載《舊唐書·地理志》三、《新唐書·地理志》五。
唐垂拱二年(686)復置武進縣,移治于常州城內,與晉陵縣并治郭內。
《元和郡縣圖志》:常州郭下二縣,晉陵、武進。“垂拱二年又析晉陵西界立武進縣于州理。”《輿地廣記》:常州晉陵、武進二縣,武進縣,“唐垂拱二年復置于州城內與晉陵分治。”兩宋因之,晉陵與武進二縣并治常州郭下。《輿地紀勝》:常州晉陵縣倚郭;武進縣倚郭,“今與晉陵分治郭下。”
唐垂拱初復置之武進縣,為常州治,即今常州市。
《讀史方輿紀要》:常州府武進縣,附郭,“唐垂拱中晉陵與武進并為附郭縣,宋、元因之,明洪武初并晉陵縣入武進縣。”《嘉慶重修一統志·古蹟》:武進故城,“唐垂拱二年復分晉陵西界置武進縣于常州郭內,至今因之。”按明、清常州府治武進縣,即今常州市。
武進縣政區考
武進之政區,其名稱和方域,隨著時代的變遷,是有所不同的。以元末明初為界,西晉設置的武進縣,由古丹徒、曲阿二縣析置,其范圍較小,其方位呈東西向。明清時代的武進縣,原晉陵縣撤銷并入,其范較大,其方位呈南北向。正因為如此,有的讀者,以及部分專家,他們把武進故城說在今丹陽市內。前面講過,唐《元和郡縣圖志》所載:“晉武帝別置武進縣于丹陽縣東五十里。”這顯然與丹陽有別,但到了明清時武進故城,所有志書已明確載在今常州市西北。此事前面已專門講述,這里就不再贅述。

武進新貌 陸志剛等航攝
明清以前,在武進縣的范圍內,最早的行政區為延陵邑和延陵縣。《辭海》曰:“延陵,春秋吳邑,季札所居。故址即今江蘇常州市。”《史記·吳太伯世家》:王馀祭元年(前547),“季札封予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季札是吳王壽夢四公子,自幼聰慧,深得吳王深愛,欲傳位于他,他不從。季札曾三次讓位,深得國人敬愛。公元前547年(王馀祭元年)他受封于延陵。
關于延陵邑的位置問題。今有兩種說法,一是大都說在今常州,另一說在今丹陽市延陵鎮。《漢書·地理志》:毗陵縣“季札所居……舊延陵改之。”明確指出,毗陵縣(治今常州),為季札所居,即他封邑之地。
關于延陵邑范圍問題,亦有幾種說法,一說延陵邑以常武地區為中心,東涵今江陰,西涵今丹陽,南涵今宜興;一說延陵邑中心為今江陰暨陽地區;一說延陵邑的范圍遠及丹徒。鑒于延陵邑的治所在今常州,我們認為第一種說法是正確的。
關于延陵縣的設置問題。這個問題過去一直不明朗,連《辭海》過去也曾回避此事。然而隨著學術活動的深入研討,至今終于日益明確。《二十五史·漢書·地理志》中未收有延陵縣,而在毗陵縣中提到由“由延陵改之”。南宋王象之編著的《輿地紀勝·卷六·常州》:“秦并天下,置會稽郡,延陵等四等縣屬焉。西漢改舊延陵為毗陵縣。”延陵縣由延陵邑演變而來。延陵邑始于周靈王二十五年(前547),止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延陵縣始于秦王政二十五年,止于漢高祖五年(前202)。
在此有必要說一下丹陽的延陵縣,它與常州的延陵縣是兩碼事。時間上前后相差甚遠。《中國歷史大辭典》講得很明確:“延陵,古縣名。西晉太康二年(281)因而得名。”季札封地延陵,是在今常州。丹陽是季札封地所及,也就是說是指封地所及的范圍,但不是封地中心。常州延陵縣置于秦代,丹陽延陵縣置于西晉,兩者相距幾百年,不能混淆起來。
再說毗陵縣和晉陵縣,純屬常州市境。這兩縣歷史上爭議也少,這里則簡敘之。
毗陵縣,《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毗陵季札所居。揚州川莽曰毗壇。師古曰:舊延陵,漢改之。”毗陵縣始于漢高祖五年(前202年),止于西晉永嘉五年(311),治今常州。
晉陵縣,《宋書·地理志》:“晉陵會,本名延陵,漢改毗陵,后與郡俱改。”晉陵縣始于西晉永嘉五年(311),治今常州。唐垂拱二年(686)與武進縣同為常州治。元至元十四年(1277)為常州路治。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改晉陵縣為京臨縣,為長春府治。又改武進縣為永定縣,亦為常州府治。尋省京臨入永定縣。至正二十二年又改永定縣為武進縣。明清為常州府治。清雍正二年(1724)析武進縣東部為陽湖縣,二縣同治今常州市。1912年陽湖縣并入武進縣。1993年武進縣遷治今湖塘鎮。1995年改設武進市,2002年撤市改武進區(原市境北部析置新北區)。2015年戚墅堰區撤銷,并入武進區。以上,就是武進政區變動的情況。
總之,武進故地考留給我們的是一個豐富的歷史遺產,值得我們學習和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