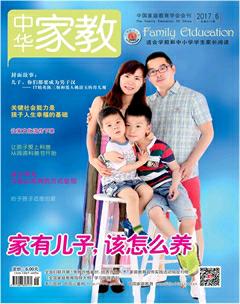做自然的孩子
雷虎
城市化的生活,應試化的教育,給我們帶來了諸多便利,也把我們磨成了螺絲釘。當個性化人格喪失殆盡,生活也就沒了想象空間。有這樣一群人,試圖反抗這種蓋棺定論的教育模式。從未振臂高呼“革命”,他們只想攜手同心、身體力行,溫和地做社會改良。
他們曾經帶著一群孩子,建造了兩座“會呼吸的建筑”,蟬聯2014、2015年底“世界建筑獎”。故事的主人公叫王晨峰:這些成果只是他帶領家長們,在自己孩子身上推行,“自然教育”實驗的冰山一角。
拉圖爾自然社區
“在德國出生的女兒和在國內出生的兒子,讓我認識到中德兩國在教育上的巨大差異。走上自然教育這條路,只是一個父親的自然選擇。”國外尊重孩子的天性,強調要孩子在自然中成長,國內卻是應試教育,一切都要為考分讓步!這讓身為父親的王晨峰很不爽。2008年,王晨峰在武漢成立“拉圖爾自然社區”,開始推行自然教育。
每一個社區的形成,共同的理念都是看不見的引力線,而“拉圖爾自然社區”的萬有引力,只有六個字:真實、真食、珍食。
真實,是真實不偽裝的社區關系;真食,是真材實料的食物;珍食,是珍惜土地的饋贈。
“一畝布飄流”
簡單生活,對城里人們來說卻可遇不可求。糧食已經從田間地頭的辛勤汗水,變成了超市中的貨幣交換。王晨峰決定帶孩子們去原野時,給他們帶去一畝布。一畝布在大地徐徐展開,只需一秒鐘就能讓孩子們認知,這承載五千年農耕文明和生命的基本單位。當一畝地產的糧食放在一畝布上時,孩子們會刻骨銘心;大人們也會重新用已經被遺忘的尺度去丈量世界。
王晨峰和拉圖爾自然社區的孩子們,帶著這一畝代表鄉村記憶的布,開始了穿越中國的四季奇幻漂流:春暖花開,小朋友們在布上畫上鮮花和秧苗;夏天炎炎,布匹上開始出現映日荷花;秋風漸起,畫布上涌動著金色的稻浪;冬日肅殺,萬物蕭條,但田園四時之景卻在畫布上永保留。
“一畝布飄流”,不僅僅是對孩子們的一次自然教育,更是對成人世界的一次自然洗禮。
孩子們在一畝布上作畫,在展示自己對自然的理解的同時,也喚醒了“久在樊籠中”的父母們,心中“復得返自然”的渴望。
自然教育,是帶著孩子體驗傳統婚禮,在隆重的婚禮中體會家庭的含義;自然教育,是讓孩子們和觸自然親密接觸,從小培養一顆敬畏自然的心。自然教育,是讓孩子們聽一場流傳千年的皮影,懂得文明的起源和流變……
拉圖爾創造社
僅在戶外讓孩子認知自然,在鄉村讓孩子繼承傳統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城市已經變成了人類生活的自然。自然教育最緊迫的,是在城市中設計出一種模型,讓父母和孩子互動,彼此教學相長。
現在的城市已經被鋼筋混凝土占據,王晨峰希望拉圖爾的孩子長大后,能夠創造一片天人合一,創造屬于自己的“天空之城”。他成立了“拉圖爾創造社”,開始用建造來開發孩子創造性。王晨峰說:“沒有建造的童年,是有缺陷的童年!”
孩子們天生親近自然,不拘泥于懂得鋼筋混凝土之外的建造方式,選擇了活竹作為原料。他們更不安于現實的世界,希望把建筑撐起來,遠離地面,創造了一個脫離現實的環境,完全屬于他們的世界……
36位孩子和他們的父母,決定用3個月時間一起來“澆灌”,把這座“天空之城”從夢想照進現實。建筑主體完全不用鋼筋混凝土,而是用的代表中國人風骨的竹。
2013年植樹節那天,竹子種下,“天空之城”開始筑城。用原竹作為建筑的主體結構,
建筑被拆分成8個3米×3米的原竹結構單元,通過3平方米的基礎面積獲得90平方米的建筑面積。底層倒金字塔形的結構,讓孩子們的房子懸浮在空中,兩個種植的建筑成為城市向上的空間原型。
20個3米×3米的房子,通過橫向構件固定在一起,作為空中露臺和兒童活動室,竹子也成為整個建筑最靈動的景觀。每個孩子都建造自己的小木屋,20個房子在一起,經營出帶有鄰里關系的城市空間形態。
“天空之城”以建筑為主題,通過讓孩子親自參與建造,讓孩子們更真切地了解,自然、工具、建造甚至生活本身。
“在我們30歲時,想嘗試用這樣的一次建造來探索建筑的邊界在何處。”年輕的設計師穆威一直希望,能設計一座“長在竹林”上的自然建筑。孩子們用他們天馬行空的想法,幫穆威完成了他的構想。“天空之城”打開了父母和孩子們的腦洞。
2014年,40個6-12歲的孩子和家庭,共同用鋼絲和49公里的白色麻繩建造了一個“綁在樹上的房子”——絲房。如果單純從建筑的實用性來講,無論是“天空之城”還是“絲房”,都不是一個好項目。它們花費了金錢和時間,卻不能住人。但在這過程中,孩子們得到了建筑學啟蒙體會到伙伴們一起分工協作的精神。整個過程是輕松愉快的,更重要的一點是:全程父母陪伴,上陣父子兵。
“天空之城”和“絲房”分別獲得2014年、2015年世界建筑中國建筑大獎。它們打破了建筑學的邊界,代表了社會對自然教育模式的認同。
從表面上看,是自然教育激發了孩子們的自然天性。其實,自然的孩子是來自自然的饋贈,讓固化的成人世界重新變得無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