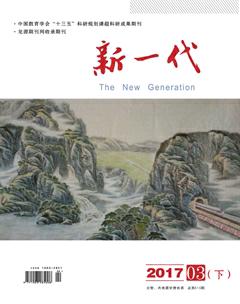淺論陶淵明詩歌中的玄學之美
李永章
摘 要:陶淵明生活在玄學風靡的哲學背景下,他的詩歌深深地鐫上了玄學的烙印,但他又有詩意的創新,將哲理與悠遠曠達的意象相結合,創造出了樸素自然、簡潔真誠的詩境。
關鍵詞:玄學;陶淵明;詩歌;文學;創作;化身
魏晉時期,玄學盛行,玄學是以綜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學說為主的哲學思潮,故通常也稱之為“魏晉玄學”。玄學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所謂“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就是總天地萬物一般規律的“道”,它體現了萬物無窮奧妙的變化作用。玄學作為一種本體之學,對魏晉六朝的文學觀念產生了頗為深遠的影響。玄學影響到魏晉士人的人生理想、價值取向、生活方式和審美情趣,進而影響著他們的文學創作。
陶淵明所生活的東晉是一個偏安的王朝,山河破碎,最高統治者以及士大夫們難以擺脫精神上的苦悶,而玄學的崇無清虛的要旨與社會的精神需要恰好吻合,故東晉一代,玄學大暢其風。玄學與文學多方位交互滲透,甚或達到水乳交融之境。在玄學思潮占主流的大背景下,陶淵明不可能不受玄學的影響,在他的詩文中,到處可以見到玄學影響的痕跡,但這種痕跡不像其他玄學家平典似道德論的說教,而是一種如水中之鹽、花中之蜜的別樣的玄學之美。陶詩語淡情深,與自然渾然天成,其中透露著玄學中的“自然”之思,處處與玄理暗合,相得益彰。陶淵明的作品是魏晉玄學滲入文學之中所結出的碩果。可以說陶淵明即是“自然”和“真”之玄學的化身,即所謂的“真人”。他的作品也以全新的方式詮釋了玄學的要義。
陶淵明詩歌大部分內容圍繞鄉村生活,充滿玄學之美和田園氣息。
陶詩所寫內容皆是最平常的鄉村之事,但在平常的景物中,卻包含著無限豐富的內涵,具有空靈的意境,充滿著田園氣息。如《飲酒》之五:“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詩人的住所雖然建在喧鬧的環境中,卻察覺不到車馬的喧嘩,這表明他的內心是恬忍隱退的。為什么會這樣呢?是因為“心遠地自偏”。“遠”是玄學中最常用的概念,這里體現了作者所強調的歸隱是心靈的歸隱而非身體的歸隱,以及對爭名奪利的世界的冷漠的態度。緊接著詩人采菊東籬,悠然自得,飛鳥呼朋引伴而歸,大自然的一切顯得那么有生機,此時詩人心境與大自然融為了一體。自然界與人的心界此刻達到了“和諧”之美,即所謂的“真意”。而對這種“真意”卻“欲辯已忘言”。從中可以看到陶淵明對玄學中“言意”之辨的態度,這正是老莊思想所說的“得意忘言”含義之體現。全詩清新自然,寫出了詩人與世無爭、怡然自得的感情。完美的畫面中蘊含著人生真諦:人既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應該具有自然的本性,在整個自然運動中完成其個體生命,這就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陶詩塑造了更加渾融的藝術境界,在思想上創造了更加“自然”的玄學境界。
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說:“田園景色在他筆下,不再是作為哲理思辯或徒供觀賞的對峙物,而成為詩人生活(參加了一定田園勞動)興趣的一部分。”如《歸園田居》一:“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念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這首詩所描寫的景物,既有田園的景物,又抒寫了胸中之意。“質而實綺,癯而實腴”準確描繪了陶淵明對村舍風光的感悟,也蘊含著他對人生哲理的思考。“性”、“虛”、“閑”等皆為玄學家經常言及的語詞。其中“自然”一詞,是魏晉玄學的一個核心概念。在陶淵明眼中,農村風景就是一幅畫,就是一首詩,他以詩人的心胸面對田園世界,田園世界亦培植了陶淵明心中的詩意。陶淵明在對詩畫境界的賞會與田園世界的詩意感悟的同時,已把玄學思想融入其中。
陶淵明性格是詩性浪漫的。他數次出仕,終歸田園,這源于他“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和“質性自然”的本性。回歸田園之后,他主要從事農事勞作。但他與普通的農夫有著本質的不同,他的農事生活只不過是一種生命回歸自然本真的狀態。《歸園田居五首》之三:“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這首詩描寫的內容,是純粹的鄉村勞作暮歸之景,是極普通的農家生活,沒有渲染,沒有藻飾,只有淡淡的敘述和平靜的對農家生活的真實描摹,其形跡與普通農夫無異。但陶淵明詩歌的不同之處就在于他能夠在這種極普通的田園生活描寫中做深層次的體悟,在普通的農事生活中實現其人生的價值。詩中雖然沒有玄學的概念,但卻充溢著一種名士風度和由玄學人生觀所蘊含著的生命情調。
陶淵明身處東晉玄學風靡的哲學大背景下,在極普通的田園自然描寫中,用樸素簡潔,洗凈鉛華的語言,將哲理和悠遠、曠達的意象結合在詩歌中,創作出了渾融無間,意味雋永的天籟一般的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