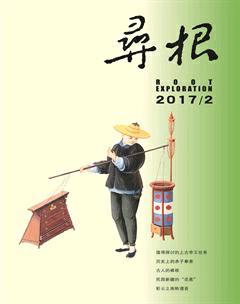“戲子”流年考略
顧炳興
作為表演才藝的職業戲曲演員——“戲子”,在中國古代被貼上特殊標簽,其身份地位下賤,被世人輕薄貶損。多少年來,“戲子”被壓在社會階層的最下層,只能強顏歡笑地掙扎在舞臺上,供權貴們取樂。
“戲子”一詞,據《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舊時稱職業的戲曲演員(含輕視意)。”查《辭海》語詞與藝術分冊均未收錄此條目。《辭源》雖無“戲子”條目,卻有“戲文子弟”一條。據《辭源》解釋,“戲文子弟”即“戲曲演員”,語出“明陸容《菽園雜記》卷十:‘嘉興之海鹽,紹興之余姚,寧波之慈溪,臺州之皆有習位倡優者,名曰為戲文子弟”。
“戲子”沿革
歌與舞的組合,是“戲”最原始的表現形式。其表演者現代稱為演員或文藝工作者,但在古代稱為“優”,又稱“倡優”。“倡優”者除能歌善舞外,還具有機智靈活、滑稽幽默的演技才能,又稱“俳優”。“俳”乃指詼諧滑稽。此外,古時還有“優伶”之稱。不過,“優”與“伶”的釋義不同。據《康熙字典》曰:“伶人,樂工也。伶倫古樂師,世掌樂官,故號樂官為伶官。”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記載:“古之俳優,但以歌舞及戲謔為事。自漢以后則間演故事,而和歌舞以演一事者,實始于北齊。”
“伎”的名稱,古代指以歌舞為業的女子。《隋書》載述:“煬帝時伎戲,其歌舞者亦多婦人之服也。”隋唐時期的宮廷生活,燈紅酒綠,歌舞升平。按唐樂部分坐部伎、雅樂部,而坐部伎最為高選。《通典》曰:“坐部伎即燕樂,以琵琶為主,故謂之琵琶曲。”
將戲曲演員稱為“戲子”,資料表明始于明清之際,可在明末馮夢龍的《醒世恒言》覓見蹤跡。如在第二十卷《張廷秀逃生救父》中敘述:“張廷秀父親因被人陷害在牢,同弟弟張文秀一起去鎮江告狀,途中被潘忠規勸以演戲糊口,遂成為一名戲子:‘那孫府戲子,原是有名的。一到京中,便有人叫去扮演。”在此故事中,戲子身份極為低賤。這可從張廷秀在南京唱戲遇見邵承恩時二人的對話中看出,“張廷秀,我看你相貌魁梧,決非下流之人。你且實說:‘是何處人氏?今年幾歲了?為甚習此下賤之事?細細說來,我自有處。廷秀見問,向前細訴前后始末根由,又道:‘小的年紀十八,如今扮戲,實出無奈,非是甘心為此。邵承恩嗟嘆良久,乃道:‘原來你抱此大冤。今苦流為戲子,哪有出頭之日!”這里令人感到戲子的職業前途渺茫堪憂。
另在曹雪芹的《紅樓夢》中也有描述。第二十二回:“林黛玉笑道:‘問的我倒好,我也不知為什么原故。我原是給你們取笑的——拿著我比戲子,給眾人取笑。”像這類例子在明清筆記小說中更是屢見不鮮。
清末民初,歌舞戲曲已風靡流行。以戲曲為生的職業演員在社會上形成一股不可小覷的群體,卻被當時的達官權貴們視為下賤的“戲子”,地位更趨冷落。
“戲子”厄運
自秦漢的“倡優”,到唐宋元的“俳、伶、伎”以及明清時期的“戲子”,“戲子”在歷史長河中悠然徜徉,大致可分為產生、興起、輝煌、衰敗,直至貶棄幾個歷史階段。
唐玄宗是位在歷史上對戲曲的發展具有卓越貢獻的人物。由于他酷愛音律歌舞,而使“俳優、伶人”受到許多寵幸與恩惠。元代可算是戲曲發展的鼎盛時期,女性伶人博得文人與貴族的青睞,確定了舞臺表演的地位。
清朝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頒發上諭說:“外官養戲殊非好事,朕深知其弊,非倚仗勢力擾害平民,則送與屬員鄉紳,打秋風,討賞賜,甚至借此交往,夤緣生事。二三十人,一年所費不止數千金。”他指出:“府、道以上有司官員,事務繁多,日日皆當辦理,何暇看戲?家中養有戲子者,即非好官。”雍正帝諭令,各省督、撫、提、鎮和蕃、臬二司,直至道、府官員,日后要嚴查屬員家中是否養有戲子,倘有私自養留者,準密折參奏。如果該諭頒布后,督、撫等大員并不細心訪察,其下屬仍有偷養戲子者,一旦發現,將該上司照徇隱不報例一并治罪。雍正帝的諭旨頒發后,各省督、撫大員立即嚴飭屬員禁養戲子。
民國初年,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志開展了一場“就舊戲廢除、改良還是與話劇平分秋色”的學術討論活動。從1917年3月到1919年3月,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胡適、陳獨秀、傅斯年、歐陽予倩、齊如山、張厚載等文化名人紛紛發表各自觀點,形成革命、保守與改良三個主要派別。革命派對中國舊戲進行了猛烈抨擊。陳獨秀認為:“舊劇助長淫殺心理于稠人廣眾之中,誠世界所獨有。”胡適認為:“傳統戲曲中的臉譜、嗓子、臺步、武把子一類的東西,就像男人的乳房,是戲劇的‘遺形物,這種‘遺形物不掃除干凈,中國戲劇家遠沒有完全革新的希望。”周作人認為:“中國舊戲沒有存在的價值,第一是它野蠻,第二是它有害于‘世界人心。”錢玄同更為激進:“要中國有真戲,非把中國現在的戲館全數封閉不可。”
傳統舊戲是魯迅批判封建文化的一個方面。1922年,《社戲》的發表拉開了魯迅批判舊戲的帷幕,此后十幾年不妥協。魯迅對待舊戲及戲子的態度不僅始終沒有改變過,在他的創作后期,對此的批判還愈演愈烈,并以梅蘭芳為主要對象。在文藝大眾化運動期間,人們發現,他對梅蘭芳的批判劈頭蓋臉、直指要害、不留余地。這讓許多人不解其味,且成為學界反復爭論的焦點。國內外眾多研究者往往從魯迅對“戲曲”與“戲子”兩個方面的批判來研究或揣度他對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
戲曲和小說的關系本來很密切,許多傳統劇目都來自古典小說。魯迅是研究中國小說史的,他在研究過程中一定會接觸到許多有關戲曲的文獻資料。這說明魯迅懂戲。也沒有任何史料表明魯、梅二人之間存在過個人交惡的情況。那么,梅蘭芳是否以一個文化符號的方式進入了魯迅的文藝批判視野?抑或梅蘭芳與文藝大眾化時期的魯迅在思想上有沖突?
魯迅在《略論梅蘭芳及其他》一文中敘述:“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傳統。辛亥革命后,伶人的品格提高了,這崇拜也干凈起來……梅蘭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寵兒,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奪取民間的東西的,將竹枝詞改成文言,將‘小家碧玉作為姨太太,但一沾著他們的手,這東西也就是跟著他們滅亡。他們將他從俗眾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來。教他用多數人聽不懂的話,緩緩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戲的,這時卻成了戲為他而做,凡有新編的劇本,都只為了梅蘭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蘭芳。雅是雅了,但多數人看不懂、不要看,還覺得自己不配看了。他未經士大夫幫忙時候所做的戲,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骯臟,但是潑辣,有生氣。待到化為‘天女,高貴了,然而從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憐。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數人是倒不如看一個漂亮活動的村女的,也和我們相近。”
“戲子”新生
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國家非常重視對文藝領域知識分子與藝人的思想改造。毛澤東早在1942年5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指明方向:“文藝工作者要學習社會,這就是說,要研究社會的各個階段,研究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只有把這些弄清楚了,我們的文藝才能有豐富的內容和正確的方向。”在這個原則的指引下,黨和國家挽救、改造了一大批舊社會唱戲的名伶藝人。例如被鴉片毒癮纏身的名武生高盛麟與名凈裘盛戎。他倆是富連盛科班盛字輩的師兄弟,后因被鴉片毒害以致貧窮潦倒淪為底包,在舞臺上演出只落得合穿一條彩褲的狼狽窘境。在新社會黨和政府的政策感召下,重新做人的典型例子還有著名四大老生之一馬連良。1948年年底,因內戰正酣,馬連良率團赴香港等地演出。時局動蕩,粵人對京劇興趣不濃,票房賣座欠佳,劇團欠下四萬多元港幣巨債,加上顧忌曾在偽滿時期赴東北巡演背上“漢奸”的歷史問題,弄得馬連良投奔無門、有家難歸之境地。周恩來、彭真等國家領導人及時伸出援手,安排其順利回到祖國懷抱,不僅替馬連良還掉四萬港幣的負債,還幫助他戒毒。周總理還指示:“馬連良赴東北偽滿演出,是藝人為了生計,并無政治目的。”于是,徹底打消了馬連良一切沉重的思想顧慮,放下包袱,振作精神重返舞臺。一次馬連良在國慶招待會上見到周總理時感激地說:“我來遲了。”周總理熱情地安慰他說:“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后嘛!”
歷史的變遷,昔日的“戲子”,而今已是文藝工作者與表演藝術家,受到廣大人民的尊敬和愛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