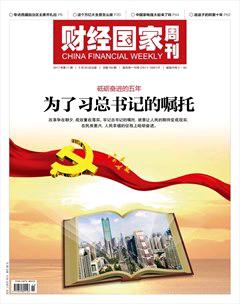深圳創新密碼
陳榮+陳少智
習近平同志上任總書記后的第一次離京考察,首站選在了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向世界發出了中國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創新無止境的時代信號。
時為2012年11月。回想起總書記前來騰訊大廈的情景,許多騰訊人記憶猶新。
是時,大廳屏幕顯示,QQ同時在線人數超過1.47億,是全球唯一的同時在線用戶過億的互聯網產品。
習近平說,人類已經進入互聯網時代,這是世界潮流。他希望騰訊保持創新優勢,為推動中國互聯網發展作更多貢獻。
如今,位于南山區科技園的騰訊大廈二樓展廳,成了各界人士參觀學習的地方。騰訊市值也超過3000億美元,躋身全球前十。
除了鮮明旗幟強調改革開放這條正確的道路“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開拓,要上新水平”外,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也是習近平在深圳調研的一個重點。騰訊由小到大的歷程表明,創新是企業發展的不竭動力。它進入總書記的視野,因為其正是深圳本土的創新型企業代表之一。
為走創新發展之路,習近平在考察深圳時還特別強調必須高度重視創新人才的聚集。他要求各級黨委、政府繼續完善凝聚人才、發揮人才作用的體制機制,進一步調動優秀人才創新創業的積極性。
經濟新常態下,由資源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將創新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首,大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近五年來越來越明確成為國家發展戰略轉型的方向。
正如騰訊為深圳創新發展的縮影一樣,深圳,這一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從基于特區政策的高速增長奇跡,再到“特區不特”的疑問,近年又華麗轉身為創新高地,以總書記的囑托為最強動力,為整個國家的創新驅動發展,演繹出新的傳奇。
創新源頭活水
習近平調研考察以來,深圳的發展成績有目共睹。
從數字上看,2016年,深圳市GDP達到1.95萬億元,同比增長9%,相比2012年,增幅超過50%,是2010年的兩倍多。
高增長的GDP數字和一些更為關鍵的數據背后,是深圳經濟發展從速度到質量的脈絡體現。
比如,先進制造業成為深圳發展的強勁新動能。過去四年,深圳先進制造業年均增長10.5%,2016年實現增加值約5600億元,占工業比例71%,比2012年提高8個百分點。這其中,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66.2%,5倍于全國。
再比如,科技創新已經成為深圳發展的主引擎。2016年,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增加值增長10.6%,高于全年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率1.7個百分點,占GDP比例超過4成。而過去6年來,深圳的戰略新興產業更是連續保持了20%以上的強勁增長。
創新要素驅動已成為深圳發展的突出特征。2016年,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強度4.1%,2倍于全國水平,居全國城市之首;深圳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占全國的50%,每萬人有效發明專利數80件,10倍于全國水平。
按照總書記的指示精神,不僅騰訊這樣的企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大力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深圳,也實現了創新發展的“蝶變”。
深圳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吳思康說,深圳的實踐表明,只要堅定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牽住科技創新這個牛鼻子,就能實現發展動力的轉換。
值得注意的是,談到在深圳“蝶變”過程中唱主角的創新主體時,除了華為、中興、騰訊等全球知名的科技企業,很多人還會推薦研究“新型科研機構”。
按照當地政府官員的說法,這些機構屬于“四不像”:具備企業、研究機構、事業單位、民辦非企業等特征,但又不完全屬于其中的任何一類。
這樣的“四不像”,有華大基因研究院、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太赫茲研究院、中科院先進技術研究院以及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等等,有近百家之多。
這些“四不像”的具體模式有些區別,比如華大、光啟和太赫茲研究院是“民辦公助”,中科院先進院和深圳清華研究院則屬于“國有新制”,但總體看,它們體制機制靈活,都在扮演科研成果產業化的“紅娘”。
華大基因董事長汪建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華大建院5年多時,科研實力就已躋身國內科研機構十強,在全球頂級科學刊物發表論文數量位列中國第四、世界第六,是全球規模和產值最大的基因測序及分析機構。
中科院先進院院長樊建平介紹說,該院旗下的育成中心,育成企業總計逾200家,持股91家,持股企業的年營業額17億元,資產規模逾80億元,并形成蛇口機器人、龍崗低成本健康、李朗云計算等產業園區,院地合作助力轉移轉化,聚集初創型高新企業抱團發展。
這些蔚然成風的新型科研機構,和華為、中興、騰訊等眾多科技企業一道,組建創新梯隊,成為了新時期特區創新發展的源頭活水。
為什么是深圳
深圳的土地、電力等生產要素有限,沒有全國最好的高校資源,也沒有科研大院大所,為何會扎堆出現華為、騰訊這樣具備全球影響力的科技企業?為何會培育出華大、光啟這樣靈活高效的科研機構?為何會成為全國創新發展的高地?
一些人說,深圳一是特區,政策有優勢,二有深交所,靠近香港,有資金優勢。給政策給錢給資源,這個別人比不了。
單一來看,確有合理之處,但都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深圳戰略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得以聚集,高新技術企業得以層出不窮,離不開當地在創新方面的“頂層設計”。
比如,從2008年進行全國首個創新型城市試點,到2014年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試點,深圳制定出臺了全國首部國家創新型城市總體規劃、促進科技創新的地方性法規,實施自主創新“33條”、創新驅動發展“1+10”文件、促進科技創新“62條”等系列政策。
尤其前海合作區、國際生物谷等一些重點區域和項目的開發建設上,深圳更是在財稅優惠、激勵機制、人才發展環境、土地管理、運營管理模式等多個方面給予了一系列先行先試的政策扶持。
這些不斷強化的規劃體系和政策體系,是深圳實現以創新驅動發展的基石。但如果橫向對比,對創新產業的特殊政策支持并非深圳獨有,深圳政策供給出成果的秘訣,又與政策制定者的戰略定力和前瞻性布局有關。
比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深圳還能堅持將創新驅動作為主體戰略,實屬不易。沒有這種意識和定力,恐怕深圳至今還在依靠土地財政和傳統產業來保GDP增長。而如今,深圳市土地對財政的貢獻已降低至不到一成,戰略性新興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達半壁江山。
在創新類政策體系的具體執行上,深圳也頗有章法。
比如推動企業成為創新主體,這是幾乎所有地方政府的創新政策都在強調的內容。深圳的做法,是針對不同的創新主體下不同的“菜單”:華為、中興、騰訊這樣的大型科技企業,政府放手,讓市場規則去配置資源;華大、光啟這樣的新銳民營企業,則重點幫他們解決與傳統體制機制的銜接難題,盡量用全新的配套政策體系去包容新主體;對于體制內的科研院所,則放手讓他們嫁接市場基因。
簡而言之,就是用政策和規劃營造一種寬松的政企關系,企業需要時政府和政策會及時出現,不需要時走遠一點。
如果跳出單一因素層面,從頂層設計到產業鏈結構,再到政企關系和深圳的企業家精神,整體看,深圳已經創造性生成了“政策引導產業,產業集聚人才,人才反哺產業,產業配套政策”的良性循環。
用不久前調任河北省長的深圳原市委書記、市長許勤的話說,按照中央提出的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和創新驅動發展相關要求,深圳正在構建“綜合創新生態體系”。
這個創新生態之中,包括政策生態、科研生態、人才生態、創新產業鏈生態、金融生態、全球化資源配置生態、創新文化生態等。
也就是說,企業要錢時有錢,要人時有人,要政策時有政策,幾方面互相支持,形成區域內、系統內、產業鏈內的共贏。
攻堅期和深水區
和整個國家的深化改革進程類似,深圳的改革和創新發展也并非一帆風順,同樣面臨一些曲折和“通病”。
比如人才問題。
過去數年的創新發展乃至數十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特區的魅力,中西方文化交匯,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冒險家”,把深圳作為尋夢的家園。
深圳市委市政府因勢利導,實施了引進高層次創新人才和團隊的“1+6”文件、“孔雀計劃”等系列政策措施,近年來累計引進國際一流創新團隊64個、“海歸”人才約6萬人,“十三五”期間還將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團隊100個、海外高層次人才2000人、新增技能人才110萬人。
隨著城市擴展和改革進程的深入,一些問題隨之而來。在降成本方面,深圳的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上升過快,尤其是地價、房價升幅過大,既給企業創新發展造成擠壓,也加大了年輕創業者的負擔。
在補短板方面,深圳公共服務供給也還存在需求缺口,優質教育、醫療等資源缺乏,給人們創新創業帶來一些后顧之憂。
為了留住人才,深圳出臺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從創新回報、知識產權保護、住房、家人安置、社會福利等方面,為高層次專業人才安心生活、稱心工作、專心發展、潛心提升營造適宜的環境。
不過,怎樣才能用得好留得住人才,仍然是深圳乃至所有現代創新型大城市面臨的一大現實挑戰。
另有一些挑戰,更具普遍意義。
比如,有當地研究人員認為,一方面,改革進入全面深化的深水區,每項改革都涉及到利益調整,不可避免會面臨很多新矛盾、新風險;另一方面,深圳憑借數十年積累的市場機制、環境、產業結構、體系、創新能力,實現了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一些干部開始出現自我滿足的情緒,改革創新的緊迫性和使命感有所淡化。
除了這些改革創新的“通病”,作為排頭兵,深圳也碰到過一些其他城市尚未遭遇的難題。
一家新型科研機構負責人說,他們機構的一些研究項目曾想與體制內的單位合作,一些新產品也曾想進入國企的采購體系,但由于其民營身份和“四不像”機制,與傳統體系“不夠兼容”,需要沖破的障礙不少。
汪建也介紹,華大基因的基因測序技術和測序儀產品,在深圳按照先行先試的辦法進入市場,卻因為技術太過超前,一度遭遇國家相關管理部門的政策限制,無法上市。
中科院先進院雖然是“國有新制”,在運營模式上實現了市場化運作,但在用人機制、資金使用、風險承擔等部分制度上,仍然擺脫不了傳統科研院所的框架,束縛住了進一步前進的手腳。
這些配套、銜接問題,具有全局性、普遍性,往往非深圳自身區域之力所能協調和解決,需要全國范圍內更深層次的體制改革和制度突破,需要中央部門和地方聯手,共同尋找發力點,才能將改革創新深化。
積極的信號在于,中央層面早已關注到改革先鋒在深水區面臨的挑戰。
2015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在對深圳工作的重要批示中指出,深圳市要牢記使命、勇于擔當,進一步開動腦筋、解放思想,特別是要鼓勵廣大干部群眾大膽探索、勇于創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中創造新業績,努力使經濟特區建設不斷增創新優勢、邁上新臺階。
這既是今后深圳改革開放和創新發展的奮斗目標和努力方向,又提出了更高的使命要求和責任擔當。
深圳當地人士對此亦有清醒的認識,一位政府部門負責人士表示,從“試驗田”到“示范區”再到“尖兵”,特區的特殊使命和功能定位,必然要求深圳在改革和創新的新階段,繼續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