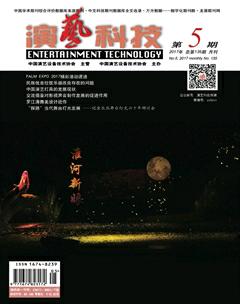基于語料庫的高職英語寫作詞匯發(fā)展的創(chuàng)新研究
摘 要:寫作是檢驗二語學習效果的試金石,而寫作的質量可以通過詞匯尤其是預制語塊的豐富性來加以提高,詞匯豐富性不僅體現了學習者運用詞匯的深度和廣度,而且反映了學習者整體的語言運用能力。理論上,隨著二語學習的不斷深入,學生寫作中的詞匯豐富性會有所發(fā)展,但這種詞匯能力的發(fā)展具體有何特征,以及詞匯發(fā)展與英語作文質量之間有何具體關聯,仍有待進一步的探索。文章基于高職學生寫作背景,通過自建語料庫的方式,對30名高職學生在大一至大三期間創(chuàng)作的120篇同題作文展開分析和研究,揭示英語學習過程中作文詞匯豐富性的發(fā)展規(guī)律,以期為英語詞匯教學提供借鑒和參考。
關鍵詞:高職英語寫作;語料庫;詞匯;預制語塊
作者簡介:徐國琴(1965-),女,江西鷹潭人,上饒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英語教育及應用語言學。
中圖分類號:G7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7)11-0076-05
英語寫作能力是學生英語水平的綜合體現,在英語教學中的重要作用毋容置疑。而詞匯則是寫作的基石。目前高職學生英語水平參差不齊,整體較低,學生的英語詞匯儲備極為有限,導致寫作句式缺乏連貫性、多樣性,語篇布局能力較弱,選詞與搭配錯誤。加之學生寫作缺乏互動和反饋,學生之間互評效果甚微,英語寫作效果欠佳。鑒于以上情況,反思傳統(tǒng)高職英語教學,新時代下有必要探討英語寫作的教學改革,以促進教與學的提高。詞匯、尤其是預制語塊與外語寫作教學的融合,有利于提高學生詞匯有效的輸出,不失為寫作教學的新途徑。
一、研究背景
眾所周知,詞匯在英語寫作過程中發(fā)揮著不可言喻的重要作用。近年來關于二語詞匯發(fā)展的研究也頗為豐富,特別是隨著詞匯測量分析軟件的廣泛應用,使得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對語料庫展開分析、處理和研究,大大提高了二語寫作研究的效率。然而,相關研究多數為橫斷研究,雖然也有少量的縱深研究,但為期較短[1]。同時,關于詞匯豐富性的研究主要圍繞詞匯變化性、詞匯復雜性、詞長、詞匯密度、詞頻分布、詞匯錯誤幾個方面,沒有針對詞匯中的預制語塊應用進行進一步的細化研究。因此,本文利用縱貫研究的方式,在傳統(tǒng)研究維度的基礎上,融入了預制詞塊應用這一新的研究視角,旨在探究二語寫作中詞匯豐富性的發(fā)展特征。
二、研究現狀
詞匯豐富性又被稱作詞匯多樣性,是反映二語寫作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也是二語寫作研究中備受關注的一個領域。國內外專家學者針對詞匯豐富性展開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例如,Laufer和Nation(1995)指出,詞匯豐富性主要由四個維度構成,分別是密度、變化性、復雜性以及新穎性[2]。Engber(1995)在前者的研究基礎上,將詞匯錯誤作為詞匯測量的另一個重要維度納入其中,指出詞匯豐富性的考察必須將有錯誤的詞匯變化性、無錯誤的詞匯變化性、錯詞比例等考慮在內[3]。Read(2000)指出,在二語學習背景下,Laufer和Nation的理論并不完全適用,尤其是詞匯新穎性并不適合作為二語學習者詞匯能力的評價指標,詞匯的豐富性主要體現在復雜性、變化性、密度以及較少的詞匯錯誤這四個方面[4]。
對于二語寫作中的詞匯豐富性,國外學者的研究主線有三條:一是研究二語寫作中與本族語寫作中的詞匯豐富性有何差異。如Linnarud(1986)對兩名同齡學習者(其中一名是二語學習者,另一名是英語本族語者)的英語作文進行比較,結果顯示英語本族語者的作文質量明顯強于二語學習者,主要差距體現在詞匯的變化性、新穎性、詞匯搭配、錯詞比例等方面[5]。二是研究二語寫作質量與詞匯發(fā)展之間的關聯。如Lu(2012)對詞匯豐富性與口述文質量之間的相關性展開研究,結果表明,詞匯變化性是口述文質量的重要相關因素,但與詞匯密度呈弱相關性,與詞匯復雜性不呈相關性[6]。三是研究二語寫作中的詞匯豐富性發(fā)展。如Lenko-Szymanska(2002)以波蘭某高校英語專業(yè)的100名大一學生和67名大四學生為研究對象,對其二語寫作中的詞匯豐富性進行研究,結果顯示高年級學生在詞頻分布及詞匯變化這兩個方面要顯著強于低年級學生[7]。
國內關于二語寫作詞匯豐富性的研究也比較豐富,如劉東虹(2003)選取了57名大二學生進行限時寫作測試,結果顯示詞匯量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二語寫作的水平[8]。秦曉晴、文秋芳(2007)對某高校英語專業(yè)學生在大學四年所寫的240篇英語作文進行歷時考察,發(fā)現學生的作文水平與詞匯的變化性、復雜性這兩項呈正相關,這與Engber(1995)的研究結論高度契合[9]。周祥(2011)對大連海事大學的30名非英語專業(yè)學生進行了為期一年的跟蹤研究,收集學生所寫的課后作文,通過定性、定量相結合的方式,研究詞匯豐富性發(fā)展與作文質量之間的相關性,結果顯示,隨著英語學習的不斷深入,學生在詞匯變化性、詞匯復雜性以及詞匯密度等方面的進步明顯,且上述三個維度與作文質量呈正相關[10]。
綜上,當前國內外關于二語詞匯發(fā)展的研究主要涉及詞匯變化性、詞匯密度、詞匯復雜性、詞頻分布、詞匯錯誤幾個維度,而關于預制語塊的研究多為單獨研究,很少放在詞匯豐富性發(fā)展的視角下進行整體研究。預制語塊作為一種多詞詞匯現象,是半固定、模式化的塊狀語言結構,其通過整體形式習得并保存于人腦記憶之中,在使用時無需進行復雜的語法生成,可以直接從記憶中調取。Nattinger(1992)提出,語言輸出的流利程度與是否精通語法規(guī)則或記憶單詞的數量無關,而是由學習者所掌握的詞組與短語數量來決定的。因此,在二語寫作詞匯發(fā)展的研究中,就很有必要將預制語塊的應用考慮在內,以提高研究結論的準確性、說服性和嚴謹性。
三、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解決兩方面的問題:一是非英語專業(yè)高職學生在二語寫作中的詞匯豐富性發(fā)展有何特征?二是詞匯豐富性發(fā)展及預制語塊的應用和英語寫作質量之間有何關聯?
(一)研究對象
本文選取某院校的30名2014級非英語專業(yè)高職學生為研究對象,年齡在17~23歲之間,其中男生8名,女生22名,他們在校學習之前均有6年以上的英語學習經歷。
(二)語料收集與處理
要求學生以“On Reading”為題目寫一篇200詞以上的議論文,限時45分鐘,寫作過程中不得參閱詞典或其他輔助資料。在語料收集的前一周,對同年級的其他學生進行同名作文試測,分析試測中出現的問題并予以改進,然后再進行正式測試。測試分四輪,共歷時二年,最終得到有效作文120篇,然后將其制成語料庫,語料總量(詞數)為26442個,其中,一年級7265個,二年級8866個,三年級10311個。
語料采集之后,還要進行一定的加工處理才能使用,這也是自建語料庫的重要步驟和要求。本文研究中主要關注的是產出性詞匯的發(fā)展特征,故在語料錄入時剔除了錯誤使用的詞匯。對于選詞無誤但拼寫錯誤的詞匯,為避免其對語料分析工具(Range 32)造成誤導,應對其進行修訂并添加標注。部分帶連字符的復合詞無法通過字典查詢到,Range 32會將其視作表外詞匯。復合詞的含義可藉由組成部分加以推斷,則其組成部分均屬表內詞匯;其他可在詞典中查到的復合詞不做額外處理。同時,通過文本合并軟件來分別處理各年級的作文,得到4個子語料庫,最后經詞性賦碼建成語料庫。
(三)數據分析
利用Wordsmith 5.0進行詞匯變化性的測量;利用Range 32進行詞匯復雜性以及詞頻分布的測量;利用AntConc進行詞匯密度測量;利用SPSS 16.0統(tǒng)計軟件對所得定量數據進行分析,具體包括相關性分析、單因素方差分析、多重事后比較。
在詞匯變化性的測量上,傳統(tǒng)方法是計算類符/形符比,但該測量方式會一定程度上受到文本長度的干擾,故其測量準確性尚存質疑。本文的研究中,使用了Wordsmith 5.0來計算標準化類符/形符比,其結果較傳統(tǒng)方法更為可靠,可比性更強;在詞匯密度測量上,本研究計算的是實義詞在作文總形符中的占比;在詞匯復雜性方面,本研究對2000高頻詞之外的正確類符進行了統(tǒng)計,計算其在總詞數中的占比。另外,預制語塊的處理分兩步進行,一是利用Wordsmith工具的詞表功能進行提取,分別設置多個詞叢。二是人工篩選,由于軟件提取的結果中包含較多噪音序列,因此需要進行人工篩選,僅保留正確序列。本研究中Range 32工具所采用的的基礎詞表,包括最常用1000詞、次常用1000詞、學術詞匯以及表外詞。
四、結果與討論
(一)詞匯變化性
通過對自建語料庫進行檢索分析,發(fā)現大一至大三年間的標準類符/形符比分別為60.29%、62.81%、61.89%,詳見表1:
分析表1可知,在大一至大二年間,詞匯變化性有所提升,但大二至大三年間又略有下降。同時,大三學生的作文長度顯著增加,基本不少于400詞,但類符增長速度卻跟不上形符增長速度,這導致其標準類符/形符比反而不如大二學生。該結果表明,大三學生的詞匯積累減緩,甚至有所下滑。為驗證相鄰年級學生的作文詞匯變化性是否具有統(tǒng)計學意義,本文采用方差齊性檢驗,結果發(fā)現:大一、大二之間p=0.05,差異顯著;大二、大三之間p=0.20,差異不明顯。
上述結果表明:學生的產出性詞匯能力在大一至大二年間出現了顯著提升,大三雖然提升不明顯,差異性不顯著。綜合作文質量和長度來看,大三學生的作文在流利程度上顯著優(yōu)于大二學生,但大三學生的詞匯積累較慢,據此推測大三學生的詞匯發(fā)展遭遇了高原瓶頸。其原因包括兩方面:一是語言輸入欠缺。眾所周知,大三學生的課堂出勤率較低,因為臨近畢業(yè)之際,大三學生的就業(yè)壓力加大,經常奔波于各招聘會之間,缺課次數較多而使其產出性詞匯能力的發(fā)展受到制約。二是課程安排不夠合理,本文的研究對象在大三上學期只接受了9周課堂教學,且未安排寫作課,而下學期,教學重心又移至課外實習及畢業(yè)論文設計上,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學生英語寫作詞匯的發(fā)展。
(二)詞匯密度
詞匯密度檢測表明,從大一到大三,學生寫作中的詞匯密度依次為59.05%、59.31%、59.69%,詳見表2:
由表2可知,從大一到大三,學生寫作中的詞匯密度整體呈上升趨勢,經方差齊性檢驗與單因素方差分析,發(fā)現相鄰年級的學生在作文詞匯密度上無顯著差異,p=0.86>0.05;但大一與大三之間具有顯著差異,p=0.01<0.05。
上述結果表明,學生詞匯變化性提升顯著但詞匯密度提升不顯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大量使用功能詞,比如人稱代詞I、you,情態(tài)動詞can、should等,這使得學生作文中的詞匯密度下降,且傳達的有效信息較少。根據Schmitt(2000)的研究結論,詞匯學習是一項循序漸進的活動,詞匯能力的獲取也分別在不同階段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效率,即產出性詞匯能力的發(fā)展是需要一個較長的學習過程。同時,研究還發(fā)現,詞匯密度不宜用來評價二語寫作的詞匯發(fā)展,這是由于詞匯密度反映的是實義詞在總詞數中的占比,而實義詞的頻率無法體現出詞匯發(fā)展的水平。
(三)詞匯復雜性
詞匯復雜性檢測顯示,從大一到大三,學生作文中2000高頻詞以外的詞匯在總形符中的占比分別為9.12%、10.17%、12.25%,詳見表3:
由表3可知,從大一到大三,學生寫作中的詞匯復雜性呈穩(wěn)定上升趨勢,為驗證相鄰年級學生的作文詞匯復雜性是否具有顯著差異,進行方差齊性檢驗與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F=10.09,p=0.00<0.05,差異顯著。經多重事后比較,發(fā)現大一、大二與大三之間都存在顯著差異。上述結果表明,學生寫作中的詞匯復雜性每年均有明顯進步,這與Laufer(1994)等人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雖然有研究表明,語言學習在經過一個顯著進步的階段之后,往往會陷入進步緩慢、發(fā)展停滯的高原瓶頸期,但從本文的檢測結果來看,學生寫作中的詞匯復雜性并未表現出發(fā)展停滯的情況,這意味著非英語專業(yè)高職學生在提升寫作的詞匯復雜性上擁有極高的潛力。
(四)詞頻分布
詞頻檢測表明,學生作文中大量使用了“最常用1000詞”,而“次常用詞”、“學術詞匯”及“表外詞”的使用較少。同時,從大一至大三的學習過程中,學生過度依賴高頻詞的情況有所改善,低頻詞的運用比例逐年增加,詳見表4:
分析表4數據,可知學生寫作時大多抱有求穩(wěn)心理,對于生僻詞匯的運用極少,這也是中國學生與英語本族語學生在寫作中的巨大差別。Cobb在一項研究中指出,英語本族語學生使用“最常用1000詞”的比例約為70%,顯著低于中國學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中國學生的詞匯積累不足,書面語輸出的訓練力度不足。通過對語料庫的進一步研究發(fā)展,中國學生經常出現重復使用某一高頻詞的問題,這反映了學生詞匯量匱乏,不能靈活運用同義詞來提升文章詞匯的變化性。同時還發(fā)現,功能詞是學生使用最多的一類高頻詞,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國二語教學的巨大缺陷。這與教師在二語寫作教學中往往過度強調語法的規(guī)范使用和語義的正確表達,而忽視了篇章的充實性、句型的復雜性以及選詞的新穎性有關,長此以往,將嚴重限制學生詞匯產出能力的發(fā)展。
(五)預制語塊應用
本文在考察預制語塊應用時,選取了“詞長及其頻數”和“以I引導的詞塊頻數”這兩方面,其中,“詞長及其頻數”的統(tǒng)計情況如表5:
由表5可知,高職學生寫作中的預制語塊應用呈以下規(guī)律:在標準頻數一定的條件下,語塊的詞數越多,應用的次數越少,即語塊的數量與長度呈反比。同時發(fā)現學生大量應用了同源詞塊,比如4詞、5詞等長詞塊的核心詞大多是一樣的,僅在前后的拓展詞上存在一定區(qū)別。結果表明,在學生的中介語發(fā)展中,過度依賴常見語塊的問題十分嚴重,主要是因為學生的中介語水平有限,積累的語塊不夠豐富。此外,學生從大一到大二應用預制語塊尤其是長詞塊的種類呈直線上升趨勢,這表明隨著學習的不斷深入,學生所積累的預制語塊數量不斷增多,運用起來更加得心應手。但從大二到大三,學生寫作中應用的預制語塊種類無明顯差異,是因大三學生進入了語塊學習的高原瓶頸期所致。
在二詞詞塊中,以第一人稱I引導的主動結構詞塊及其頻數如表6所示。
由表6不難發(fā)現,中國學生的語塊應用過度使用了第一人稱單數形式,這類以I引導的主動結構形式,并不符合英語本組語者的寫作習慣。這反映了學生在寫作中過度地強化讀者/作者顯現度,自我色彩非常濃厚,寫作呈口語化傾向嚴重。另外,從表6可以看出,非英語專業(yè)高職學生寫作中以第一人稱I引導的主動結構形式呈逐年減少的趨勢,高年級學生與低年級學生之間存在顯著性差異。這表明,隨著學習的不斷深入,學生開始有意識地隱藏讀者/作者標記,口語化傾向有明顯的改觀。
五、結論與啟示
藉由對30名非英語專業(yè)高職學生的歷時語料考察,發(fā)現英語寫作中的詞匯豐富性在各維度上有著不同的發(fā)展特點:①詞匯變化性呈非直線性上升趨勢,且詞匯變化性與學生的作文質量呈正相關性,但大三學生的詞匯學習陷入了高原瓶頸期;②詞匯密度的發(fā)展不明顯,盡管其與學生的作文水平呈正相關性,但不宜作為作文質量的評判標準;③詞匯復雜性的提升十分顯著,且相鄰年級的學生之間具有顯著差異;④詞頻分布方面,學生過度使用高頻詞的情況隨著年級的增加而呈現下降趨勢,而低頻詞的運用能力逐年提升;⑤在預制語塊應用上,隨著英語學習的不斷深入,學生應用預制語塊尤其是長詞塊的能力有所提升,口語化現象有所改觀。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教師在寫作教學中,要適當提高對詞匯能力發(fā)展的重視程度,讓學生認識到詞匯豐富在英語寫作中的重要性,鼓勵學生有意識地去應用低頻詞匯和書面語體,盡可能消除口語思維的影響。同時引導學生學以致用,積極將新詞運用到寫作之中。其次,教師要鼓勵學生制定學習計劃,強化學生在詞匯學習方面的自我責任感,也可以引入數據驅動學習模式,讓學生在語料庫的輔助下,自主挖掘真實的語言環(huán)境和語言現象,自行總結詞匯在不同語境中的應用方式及規(guī)律,逐漸提高詞匯運用水平[11]。再者,教師應將預制語塊教學滲透到寫作教學之中,比如給學生提供寫作的框架,讓學生通過課下搜集、上網查詢、頭腦風暴等形式,挖掘與作文話題相關的預制語塊,并大膽地將這些語塊應用到寫作練習之中,以此促進學生詞匯產出能力的不斷發(fā)展,從而提高學生的英語寫作質量。同時,受篇幅所限,本研究中未涉及詞長變化、詞匯錯誤等維度的研究,在今后應拓展這方面的研究。
參考文獻:
[1]王海華,周祥.非英語專業(yè)大學生寫作中詞匯豐富性變化的歷時研究[J].外語與外語教學,2012(2):40-44.
[2]Laufer, B.& Nation. P.. Vocabulary size and use: Lexical richness in L2 written production. Applied Linguistics, 1995(3):307-322.
[3]Engber, C. A.. The relationship of lexical proficiency to the quality of ESL compositions[J].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1995(2):139-155.
[4]Read, J.. Assessing vocabulary[M]. Cambridge: CUP,2000.
[5]Linnarud M,Lexis in Composition:A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Swedish Learners Written English [M]. Lund, Sweden: Gleerup,1986.
[6]Lu X. The relationship of lexical richness to the quality of ESL Learner oral narratives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12(2):190-208.
[7]Lenko-Szymanska A. How to trace the growth in learners active vocabulary? A corpus-based study [A]. In Kettemann B & Morko G(eds). Teaching and Learning by Doing Corpus Analysis [C]. Amsterdam:Rodopi,2002.
[8]劉東虹.詞匯量在英語寫作中的作用[J].現代外語,2003(2):180-187.
[9]秦曉晴,文秋芳.中國大學生英語寫作能力發(fā)展規(guī)律與特點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7.
[10]周祥.大學生英語寫作中詞匯豐富性跟蹤研究[D].大連海事大學,2011.
[11]韋莉萍.職業(yè)院校英語教師專業(yè)發(fā)展可行性途徑研究[J].職教論壇,2017(5):10-13.
責任編輯 時紅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