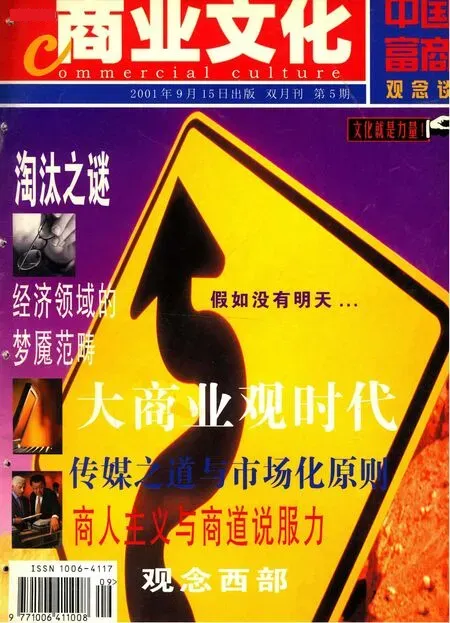藍偉光:人生愛拼才會贏
王世明+黃劍婷
無論在中國還是新加坡,在學界還是商界,藍偉光都是個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他生于中國福建,創業于獅城新加坡,興業于神州熱土,僅用20多年光景便寫就了屬于自己的傳奇人生——在商界,他是身家數億、榮登福布斯富豪榜的優秀企業家;在學界,他是功勛卓著、被譽為“中國生物膜技術教父”的科學家;生活中,他更像個江湖俠士,豪氣四溢,播善灑愛;工作中,他則是大家公認的“拼命三郎”,雖年過五十,仍奔波于世界各地。
藍偉光很忙。作為擁有近50家全資和控股子公司,擁有控股和參股兩家上市公司的新加坡三達國際集團的總裁,他的忙碌程度可想而知。2017年4月22日,應邀回福建參加廈門市2016年度專利獎頒獎盛典的藍偉光博士,于百忙中接受了《商業文化》雜志記者的專訪。
第一次創業以失敗告終
記者:藍博士您好,閩商自古以來就有著“敢為天下先,敢做領頭羊”的精神,不管天南海北,只要有市場,就會有閩商奔波的足跡。作為閩商中的杰出代表,請介紹一下您是怎樣走上經商之路的?
藍偉光:我出生在福建省武平縣的一個小山村,是個地地道道的客家人。上世紀80年代,武平還很貧窮與落后,讀書是鄉村孩子通向外界的唯一跳板。和許多鄉村孩子相比,我的求學之路是一帆風順的。從小學開始,我學習就十分用功,尤其擅長數學、化學,對數字特別敏感,記憶力也特別好,家長和老師都稱我是“活電話簿”。
通過努力,高考時,我以全省高考化學第二名的優異成績考進廈門大學化學系。大學畢業后,我又幸運地進入由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老先生親手創辦,迄今已有90多年歷史的集美大學,成為一名令人羨慕的大學教師。
也許是骨子里特有的閩商基因吧,參加教育工作后,我并不安于做一名大學教師。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下海經商的大潮剛剛在中國大地興起,我有些按捺不住,產生了躍躍欲試的想法。在兩位大學同事的“引誘”下,我很快承包了老家武平縣城一家瀕臨倒閉的面包廠,從此走上了經商之路。
記者:放棄穩定的大學教師工作,從一家瀕臨倒閉的面包廠開啟自己的商海之旅,別說在20多年前,就是在今天,也是需要勇氣的。您是在這里撈取了自己事業的第一桶金嗎?
藍偉光:呵呵,我當時是真的希望通過承包這個面包廠撈取事業的第一桶金,但沒有撈到。那時我是個沒有一點商海閱歷的“書呆子”,只會紙上談兵,雖然躊躇滿志,卻無法運籌帷幄,現實也很快給了我重重一擊。接手面包廠后沒多久,便出現資金不足、員工流失等諸多問題,面包銷量也隨之日益減少。我想方設法,勉強維持了半年后,這家面包廠還是在我的手中破產了。可以說,我人生的第一次創業以失敗告終,而且敗得很慘,幾乎讓我一無所有。
科研充電啟繪事業宏圖
記者:從大學教師轉道經商,從本質上說,您當時還是一個文弱書生,面包廠破產對您的打擊一定不小吧。重創之下您選擇了到新加坡讀博,當時的選擇是一種逃避嗎?
藍偉光:不是逃避。我不是個喜歡做白日夢的人,也不相信會隨隨便便成功。那時我才20多歲,正是熱血澎湃的年紀。盡管做好了失敗的心理準備,面包廠破產對我的打擊還是很大的。但打擊歸打擊,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破產的面包廠帶給我的收獲也是巨大的,甚至影響和改變了我的人生。面包廠的破產讓我認識到,做生意光有敢于打拼的膽識是遠遠不夠的,一定要有專業的本領和專注的精神。
從此以后,我開創的每一項事業,都與我的所學專業緊密相連。也正是為了提高和豐富自己的專業學識,1991年,我選擇了去新加坡國立大學化學系攻讀博士學位,繼續給自己的專業充電,以期在化學科研領域上求得更好的深造和突破。
在新加坡讀博士期間,我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學習上,僅用兩年多時間,就拿到了博士學位,這在國大當時是很少見的,并在國際著名的分析化學與生物化學雜志上發表了14篇論文,遠遠超出了一般博士的論文發表量,成為當時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生中發表科研論文最多的拔尖人才。
記者:確實了不起。那時您才三十出頭,就取得了如此不菲的科研成果,僅憑這些,您完全可以輕松地到新加坡或中國相關科研機構從事專業的科研工作。您當時想過這些嗎?是什么動力讓您在第一次創業失敗的情況下,依然選擇創業?
藍偉光:我沒有想過到科研機構從事專業的科研工作。雖然第一次創業失敗了,但創業的種子已經深植于我的心中。博士畢業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立足專業開始“二次創業”,這是骨子里的東西。但我知道自己當時缺少創業所必須的“實戰”經驗,為了補上這一課,我沒有急于求成、盲目創業,而是本著學習的心態,到新加坡一家水處理公司工作,出任該公司駐中國區的首席代表。任職期間,我與中國國內許多制藥、染料企業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
隨著專業技術的日臻成熟和客戶的越來越多,我決定利用專業所學,專門從事膜應用技術研發,由此開啟自己的“二次創業”。我曾和媒體朋友算過一筆賬,要想獲得100萬美元的諾貝爾化學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如果把自己掌握的知識用來創辦公司,將高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那么100萬美元的目標其實并不遙遠。1996年,根據中國龐大的市場需求,我在福建廈門火炬創業園創辦了自己的膜科技公司,白手起家,專業研發制造“中國膜”。
專業專注成就神奇“膜”法師
記者:我看過一些關于您的報道,記者朋友都喜歡稱您為“膜”法師、“膜”術師。對普通百姓來說,“膜”是個既熟悉又陌生、既直白又高深的字眼。您能給我們簡單地介紹一下“膜”的概念嗎?您所從事的膜應用技術研發又該如何解讀?
藍偉光:許多記者朋友都問到這個問題。膜是什么?膜是一種具有特殊選擇性分離功能的無機或高分子材料,能把流體分隔成不相通的兩部分,使其中一種或幾種物質透過,而將其他物質分離出來。目前,商品化的膜品種在生物制藥領域有抗生素、維生素等醫藥產品膜工藝。
膜技術是指以壓力為推動力,依靠膜的選擇進行分離、純化與濃縮。選擇適當的膜分離過程,可以代替傳統的蒸餾蒸發、真空過濾、濃縮抽提、離子交換等多種生產工藝。如今,膜技術在生物制藥領域應用眾多,如各種發酵液分離、過濾、抗生素的濃縮等。青霉素、頭孢菌素、大觀霉素、卡那霉素、泰樂霉素、利福霉素、德古霉素、紅霉素、頭孢派酮鈉、維生素C、維生素B12、異維生素C鈉等醫藥產品的生產過程,也都同膜有關。
我認為,膜分離技術是20世紀末到21世紀最有發展前途的技術,除了廣泛應用于生物制藥領域,也將在化工、石油、染料、紡織、電子、冶金、食品、飲料、環保資源再生利用等領域派上大用場。
記者:上世紀90年代初,幾乎很少有人聽說過“膜”的概念。在這樣一種科技相對落后和信息閉塞的背景下,想研發和推廣新生的膜工藝技術,其困難可想而知。最初的艱難您們是怎么度過來的?
藍偉光:當時沒幾個人相信膜技術,有的默默觀望,有的不屑一顧。膜是什么?沒人說得清楚。大家都勸我,不要去挑戰一個“不可能完成的科研課題”。所以說,最初的那段日子,我幾乎是一個人在孤軍作戰。中國有句老話叫“打虎親兄弟”,在我事業舉步維艱的時候,弟弟新光和春光毫不猶豫地辭去穩定的工作,跟我一起推廣膜工藝技術。
那是一段令人難忘的時光,我們三兄弟每天開著載重0.75噸的小皮卡汽車,裝著實驗裝置,主動到制藥廠免費幫人家做分離實驗,實驗成功了,就賣出去一套技術。就這樣,一輛小皮卡汽車載著我們走遍了全國,曾經不被認可的膜工藝技術也開始漸漸走進人們的視線。
隨著膜技術市場應用面的不斷拓寬,技術要求日益提高,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在挑戰面前,我們科學規劃,穩步前進。我始終認為,好的技術必須和市場需求完美結合,只有把市場難題作為科研的課題去一一攻克,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公司做大后,我們開始聽到銷售人員的抱怨了:對手無序壓低價格、胡亂承諾不擇手段爭取訂單等等。對此,我們的競爭哲理是:“把競爭對手漸漸變成自己的合作伙伴”。商海實踐告訴我,市場競爭沒有永遠的對手,也沒有永遠的伙伴,只有永遠的利益。凡以為有敵人的競爭者,最終大多是競爭中的失敗者。對于無序競爭,我們堅持用兩條準則應對:一是堅持技術上的創新,不斷提升技術競爭力,不斷拓展自身技術優勢領域,讓產品向上、下游延伸,永遠走在同行前面。因為技術一路領先的緣故,許多原來在某一層面、某一產品、項目的對手,最終成了三達膜或上游或下游產品的代理商、服務商或合作伙伴。
記者:三達膜科技目前在業界處于一種怎樣的領先地位?
藍偉光:業內人士都知道,誰掌握了“膜”技術,誰就掌握了化學工業的明天。一路走來,三達膜科技在“膜”技術行業獨占鰲頭,創下數個中國領先:領先在中國成功推廣發酵液過濾分離技術,如今每天有超過4萬噸的發酵液經過三達膜分離系統的處理;最早在中國創造“納濾”這一中文詞匯,并推廣應用納濾技術,被譽為“納濾之父”。目前已經銷售膜面積超過10萬平方米的納濾系統,廣泛應用于醫藥、食品、化工、中水回用等領域;領先將超濾、納濾、連續離交技術綜合應用于維生素C、青霉素、7—ACA的生產,實現了中國醫藥工業三大戰略產品生產技術領先全球的夢想;成功開發染料脫鹽技術,改寫了中國食品染料生產的國家行業標準,使中國食品染料工業占據全球75%的市場份額;領先設計出連續式發酵過濾、納濾濃縮膜分離系統,并獲得國家專利;領先成立膜清洗研究和生產部門,目前開發的專用膜清洗劑種類有幾十種。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三達開發創新出的一系列適合中國傳統工業分離純化升級改造的膜工藝過程,占領了全國維生素C和青霉素、抗生素、染料生產等領域膜應用市場的半壁江山,全中國的維生素、頭孢菌素、青霉素三大醫藥品種發酵液的分離技術都是三達做的,所有做VC的藥廠都用三達的膜法?生產工藝。
2003年6月,我創辦的新達科技集團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主板成功上市,開啟了三達國際事業發展的新篇章。同年12月,新達科技集團榮登德勤“亞太區高科技高成長500強”企業排名榜,名列第28位。如今,三達國際集團在全球擁有全資和控股子公司近50家,成為中國知名的膜科技公司之一,在國內外投建了近30個污水處理廠。三達科技團隊自主研發適合中國傳統工業分離的“膜”工藝近1000項,絕大部分為中國首創,有的達到國際先進水平。2015年10月,在以“輝煌二十載,成就大未來”為主題的中國膜工業協會20周年慶典上,三達膜環境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被評為“典范企業”;2017年3月,在2016年度第14屆中國水業企業頒獎典禮上,三達膜獲得了"工業及園區水處理領域領先企業"殊榮,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三達團隊過去多年來深耕膜法工業水處理技術,為工業園區提供基于膜技術的高污染、難治理的污廢水處理解決方案所做的工作,獲得了業界的認可與肯定。
從“膜”術師到水博士
記者:2008年,三達國際依托自主研發的納濾芯凈水技術進軍飲用水市場。當時三達的產業已經做得很大,您是怎么想到做這個項目的?
藍偉光:研發推出納濾芯凈水技術是偶然也是必然。說其偶然,是源于一次朋友間的笑談。當時一位與我合作的商業朋友笑著對我說:你藍偉光的名字在工業領域響當當,在尋常百姓中卻沒人知道,你能不能搞一個膜的家庭應用技術啊?聽了他的笑談,我首先想到了“膜”技術在飲用水上的應用。說其必然,是因為近20年來,我一直在新加坡和中國兩地從事與水質凈化與清潔生產相關的研發、應用與推廣工作,幾乎走遍了中國每一個大中城市。我所創辦的三達膜,為包括中國幾乎所有制藥巨頭在內的1000多家企業提供水質凈化與清潔生產技術與服務,我太了解中國的水質了。在我看來,研發納濾芯凈水技術,已經不單單是一個企業家事業發展的需求,而是一個企業家必須肩負的社會責任。
記者:據說當時國內飲用水兩大陣營正面臨著“礦泉水”和“純凈水”誰優誰劣的行業紛爭。在一片紛爭之中,三達“納濾芯凈水器”是何以橫空問世的?
藍偉光:應該說,當時的水污染問題已經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礦泉水”和“純凈水”兩大飲用水陣營之間的紛爭,也說明了人們對飲用水質量提出了高要求。當時的紛爭是:前者質疑后者過濾得太干凈,把一些礦物質都給過濾沒了,活水變成了死水;后者倒過頭來也在攻擊前者過濾未凈,保住礦物質的同時,化學微污染也給留下來了。現在看來,這場紛爭是科技創新過程中,必然產生的科技火花。
三達無疑是這場行業技術紛爭的受益者。我認識到,當時中國的飲用水市場正缺少一種既可以濾掉有害物質,又可以留住礦物質的水處理技術。這些,為我們隨后進行的納濾芯凈水技術研發提供了有益的思考。經過多年的研發,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三達“納濾芯凈水器”誕生了。這種“納濾芯凈水器”可以真正“達到安全、達到健康、達到環保”,與三達國際集團的名稱不謀而合。在推廣凈水新技術、建立凈水新標準,引領飲水新概念上,三達走在了科技時代的前列。如今,三達的“納濾芯凈水器”已經銷售到世界各地,成為三達膜技術產業未來重要的支柱產品。看似深奧的“納濾芯”、“膜”技術,通過一臺臺精美的三達“納濾芯凈水器”,飛入了尋常百姓家。2017年4月,由藍偉光博士率團隊研發的“一種涂層復合陶瓷濾芯的制備方法”在眾多參評專利中脫穎而出,榮獲2016年度廈門市專利獎唯一的一項特等獎。
采訪后記
有人說,藍偉光是企業家里最好的學者,又是學者里最好的企業家,這話一點兒也不為過。在學界,他是北京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等世界著名學府的兼職教授,是廈門大學水科技與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科學家、福建省膜分離工程技術中心主任;在商界,他是亞太海水淡化協會副會長、新加坡-中國科學技術促進會副會長、中國膜工業協會副理事長,登上了《亞洲周刊》“亞洲杰出華人青年企業家獎”榮譽榜,獲得了中國國務院僑辦頒發的“杰出創業獎”、中國技術市場協會頒發的“金橋獎”、中國膜工業協會頒發的“特殊貢獻人物獎”以及《水處理技術》“突出專家獎”、中國僑界貢獻獎之“創新人才獎”、“2017中國凈水年度人物”稱號等多項榮譽。
當今時代,像藍偉光這樣,集科學家的創新理念和企業家的商業頭腦于一身的人,并不多見。特別是他事業成功后對公益慈善事業和家鄉教育事業的大愛付出,讓人感受到了一個企業家沉甸甸的社會責任。2001年至今,藍偉光攜兩位胞弟捐出本金1000萬元,在家鄉創立了以父親名字命名的“藍啟林慈善教育基金會”;2002年以來,藍偉光在廈門大學設立三達獎學金,先后捐資1000余萬元支持母校教育事業;2015年1月,藍啟林慈善教育基金會聯合福建省僑辦,向23個省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捐贈了總價值1150萬元的凈水機……
快捷的語速,宏亮的聲音,慎密的思維,跳躍的情感——采訪中,藍偉光獨到的見解,奔涌的激情,一次次將記者的思想點燃。“在中國,有一首家喻戶曉的閩南歌曲叫《愛拼才會贏》,這首歌曲正是閩商‘愛拼敢贏的性格寫照。”采訪結束時,藍偉光告訴記者,“我事業的成功,也歸功于‘愛拼才會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