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樓記(短篇小說)
2017-06-16 07:43:42曹多勇
南方文學
2017年3期
曹多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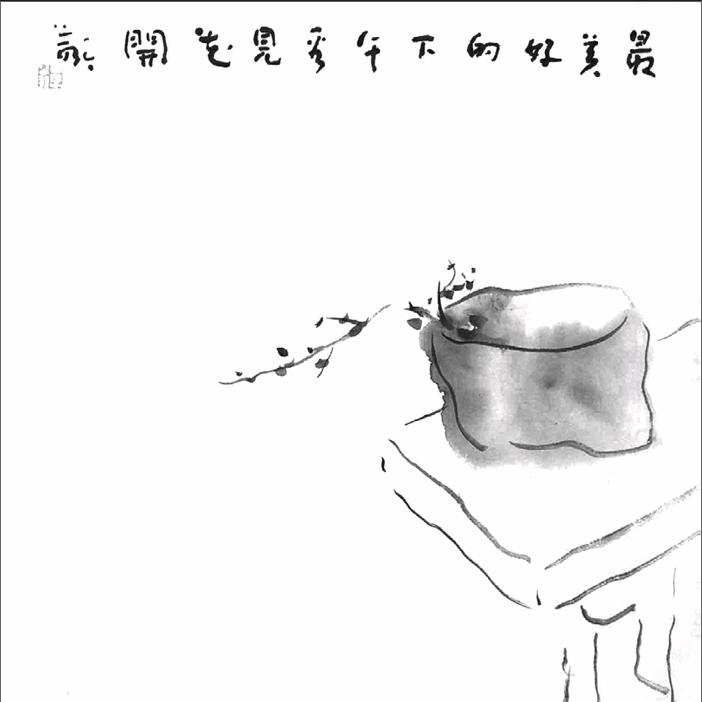
一
二月二,龍抬頭。我父親選擇這一天開工蓋樓。
一大早,村里瓦工走過來,準備放線挖地基。我父親買來一大盤炮仗,解開了,點著了,“噼里啪啦”,一陣子猛炸,響聲四散開來,藍煙四散開來,他手持一把鐵锨,要挖地基的頭一锨土。是一把嶄新的鐵锨,前兩天趕集新買的,順便買回頭的還有二尺紅洋布。紅洋布系在锨把子上,招展出一片紅彤彤的喜色。紅光映照在我父親臉上,同樣是一片紅彤彤的喜色。或許新锨不吃土,或許我父親年歲大力氣弱,“吭吭哧哧”一陣子猛踩猛挖猛使勁,锨頭就是吃不進泥土里。主家人挖頭一锨土,是習俗,是儀式,圖一份吉利。我父親怎么使勁都挖不下去,氣就粗喘了,臉就難堪了。我父親停下挖土,停下使勁,抬頭看一看四周村人。四周都是瓦工,想找一個家人替代都找不見。
我父親呼喘喘地扔下鐵锨,跟瓦工說:“你們挖吧,日奶奶的雜碎熊,我挖不動不挖了。”
瓦工走上前來,個個都是經常干這種活的村人,件件都是經常干這種活的工具,“叮叮當當”,刨的刨,挖的挖,攉的攉,一锨一锨土從基地翻開來。我父親站一旁看兩眼,難堪的臉色漸漸地緩過來,說我去毛蛋家安排晌午飯。開工管瓦工一頓酒,是規矩。我父親勾腰駝背甩手,一劃拉一劃拉,朝村里的十字路口去。毛蛋家在那里開飯店,我父親早早地打過招呼,再過去落實一下子,是放心,更是散心。我父親心里不舒暢,沒想到蓋樓開工這么一件大事,家里就他一個人,更是沒想到開工挖頭一锨土挖不出。……
登錄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