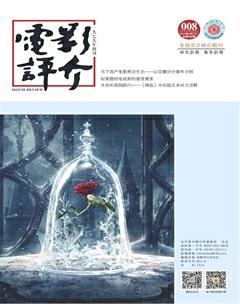歷史題材電影應準確體現歷史的核心文化精神
魏紅星
中國是一個歷史資源極為豐富、歷史意識極為濃厚的國家,隨著20多年來“國學熱”的持續升溫,經典的歷史故事更是不斷引起中國電影人的關注,根據經典歷史故事改編的電影也不時引發觀眾的興趣。縱觀近年來推出的歷史題材電影,雖然敘事方式、人物造型、美工道具、光影運用等諸多方面不乏亮點,但仍存在著一個普遍性的缺陷,就是電影工作者因為對歷史的核心文化精神往往缺乏深刻的理解和切實的尊重,所以無法將歷史的核心文化精神準確體現在電影中,從而最終影響到電影的藝術質量和市場前景。這一缺陷在戰國歷史題材電影中的表現比較典型,因此,筆者將以陳凱歌導演的《荊軻刺秦王》為例來具體分析戰國歷史題材電影中的這一缺陷。正確認識和有效避免這一缺陷,對于今后繼續制作以古代歷史為題材的中國電影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 準確體現歷史的核心文化精神是真實虛構歷史題材電影故事的前提
電影本質上是一門講故事的藝術,講故事必須進行藝術虛構。電影故事的藝術虛構可分為真實的虛構和虛假的虛構,二者的主要區別就在于虛構是否符合歷史的核心文化精神。歷史的核心文化精神是指一個時代有別于其他時代的帶有標志性特征的社會主流思潮。任何時代都有其核心文化精神,如魏晉時期的核心文化精神是魏晉風流,盛唐時期的核心文化精神是盛唐氣象,而戰國時期的核心文化精神就是“重利尚武”。
“重利”即重現實功利。與春秋之世不同,戰國是一個“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的社會[1],功利主義思想流行。士人階層為追求榮華富貴而長年周游列國,諸侯各國則紛紛變法以富國強兵。“尚武”即崇尚武力。戰國時期“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2],士人階層出現了推崇武力的傾向,各國統治者也動輒以武力相向。這種“重利尚武”的時代精神在秦國表現得最突出:“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3],“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4]
準確體現戰國歷史“重利尚武”的核心文化精神,是真實虛構戰國歷史題材電影故事的前提。以此為標準,能夠正確判斷戰國歷史題材電影的藝術虛構是真實虛構還是虛假虛構。電影《荊軻刺秦王》中貫穿全篇的最大虛構是重新設置了荊軻赴秦行刺故事發生的歷史背景:為了幫助秦王嬴政攻打燕國找到借口,趙女甘受黥刑去燕國尋求刺客來秦國行刺嬴政,最終荊軻在燕國被趙女發現……這一虛構直接決定了整個電影的情節走向、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感情基調,地位非常重要。但恰恰是這個事關全局的虛構,由于沒有準確體現出戰國社會“重利尚武”的核心文化精神而顯得荒謬不堪:嬴政想要攻打燕國,完全可以隨便找一個借口,甚至根本無需任何借口,他犯不著讓心愛的趙女去燕國冒險尋求刺客來刺殺自己,從而傻乎乎地上演一出自損君主尊嚴和秦國國家聲譽的鬧劇。可以說,這一自以為是的鬧劇化的虛構徹底解構了電影本應具有的悲壯氛圍,是整部影片最致命的失誤。至于其他的虛假虛構則不一而足,如荊軻向嬴政投擲匕首不中后準備拔劍刺殺,卻突然發現劍身早已被秦國接待官員偷偷斷去大半。試想,在戰國這樣一個尚武成風的時代,作為一個常年弄劍的武士,作為一個肩負刺殺重任的刺客,荊軻怎么可能不在秦國接待官員送還佩劍之后立即下意識地拔劍檢查呢?即便由于一時疏忽忘記檢查,他也能夠通過佩劍重量的明顯變化去感知劍的蹊蹺可疑。這一虛構顯然是編導有意設置的噱頭,但觀眾稍加推敲,便不難發現其虛假可笑之處。
“不是憑空虛構影片的戲劇性,而是從生活的原型中去發掘戲劇性沖突和情節。”[5]歷史的核心文化精神其實就是歷史“生活的原型”的本質表現,也是歷史題材電影的活的靈魂。歷史題材電影當然可以而且必須進行藝術虛構,但一定是要在準確體現歷史的核心文化精神的基礎之上,否則就會成為缺少藝術真實性和藝術感染力的“憑空虛構”。
二、 準確體現歷史的核心文化精神是合理滿足觀眾特殊欣賞心理的關鍵
中國觀眾濃厚的歷史意識造就了他們欣賞歷史題材電影的特殊心理:一是對電影所表達的歷史經典故事和經典人物形象的主體框架具有超穩定性的心理預期,二是希望電影能夠結合現代語境對這些歷史經典故事和經典人物形象進行新的合理闡釋。這種特殊欣賞心理的形成既是歷史的核心文化精神在觀眾內心長期潛移默化的結果,也是觀眾內心渴望其發生新變的產物。電影工作者雖不可一味迎合觀眾,但也需要主動了解并合理滿足觀眾欣賞歷史題材電影的特殊心理。
基本史料來源的高度穩定性以及解讀與傳播的極度頻繁,是觀眾對歷史經典故事和經典人物形象的主體框架具有超穩定性心理預期的重要原因。比如戰國歷史題材電影所依據的基本史料無非就是《史記》和《戰國策》,這兩本典籍所記載的戰國歷史經典故事和經典人物形象由于千百年來被反復解讀與傳播,早已內化為中國人心中融入了戰國歷史核心文化精神的集體記憶。“敘事是為了得到預期觀眾的理解而創作的……敘事并沒有教會我們什么新的東西,相反,它只是激發了我們已經擁有的道德和其他方面的知識和情感。”[6]觀眾欣賞戰國歷史題材電影,就是為了重溫這種集體記憶,從而激發自己對于這段過往歷史的“道德和其他方面的知識和情感”。這就要求編劇、導演在設計戰國歷史題材電影經典故事和經典人物形象的主體框架時,切切不可隨意背離這種集體記憶,否則就會讓觀眾產生強烈的違和感。電影《荊軻刺秦王》票房和市場口碑之所以不佳,正與觀眾欣賞時產生了強烈的違和感有關。首先,從故事主體框架的設計看,嬴政的主動誘導實際上是荊軻赴秦行刺的最大原因,沒有嬴政的誘導,趙女不可能赴燕,荊軻也無從出現。這一事關全局的設計固然新穎,但卻徹底背離了廣大觀眾對于荊軻刺秦王事件的集體記憶,自然會引發他們的不適與不滿。如此這般,觀眾還怎么能夠完全融入到電影之中呢?其次,從主要人物之一的荊軻的藝術形象塑造來看,電影里的荊軻已經不再是活在觀眾集體記憶里的那個輕生死重然諾的千古豪俠,而是搖身一變,成為最高統治者耍陰謀弄權術的對象,成為最高統治者玩弄于掌心的一個可笑又可憐的弱者。雖然電影后來增加了荊軻刺秦王是為了挽救天下孩子的橋段,但總體而言荊軻還是失去了他作為傳統英雄在觀眾集體記憶之中的那種感人至深的悲壯色彩。
歷史題材電影應該合理滿足觀眾對于歷史經典故事和經典人物形象主體框架的心理預期,導演必須在保持歷史經典故事和經典人物形象主體框架的前提下積極發揮自身的能動作用,對這些經典歷史故事和經典人物形象作出新的合理的現代性闡釋,以滿足觀眾希望進一步挖掘歷史的核心文化精神內涵的心理渴望,否則觀眾就不能得到收獲新知之后的快感。當然,電影《荊軻刺秦王》沒有機械地圖解史料,而是力圖用現代眼光來闡釋這段眾所周知的歷史,但結果卻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電影對故事和人物形象的現代性闡釋由于偏離了戰國歷史的核心文化精神而顯得混亂不堪,“無論是秦王還是荊軻,在導演以權欲/征服欲釋讀人物的現代性焦灼中失去了任何可資辨認的歷史依據,歷史人物由于導演過于強大的文化編碼,成為體現抽象人性的分類符號”。[7]
歷史題材電影如果要獲得藝術和票房的成功,就必須合理滿足觀眾特殊的欣賞心理,而做到這一點的關鍵,在于電影一定要準確體現歷史的核心文化精神。只有如此,歷史題材電影作品才可能達到既不墨守成規也不劍走偏鋒的理想境界。
三、 準確體現歷史的核心文化精神是積極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需要
電影作為重要的文化產品,客觀上擔負著積極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責任。為了履行這一責任,歷史題材電影必須做到準確體現歷史的核心文化精神,使國內外觀眾在歷史的回顧中真切認知中華民族的精神風貌,從而增強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增強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比如就戰國歷史題材電影而言,準確體現戰國時代“重利尚武”的核心文化精神,有助于國內外觀眾真切認知中華民族早期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戰國時代的明君賢臣、策士游俠以及諸子學派等社會主流群體大多關注現實,無論是進行社會實踐還是從事思想理論建設,都以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為出發點和歸宿,“重利”就是這個時代的主體精神風貌。“重利”的確存在功利主義的局限,但在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卻更多地表現出了戰國人物不尚空談、腳踏實地、銳意進取以改變個人和國家落后面貌的務實作風。而戰國時代“尚武”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一方面表現了生命個體的樸野剛健氣息,以及克服困難的勇氣和視死如歸的氣概,荊軻即是如此;另一方面也表現了盛行于諸侯國之間的那種勇于競爭、積極對外開拓的風氣,這一點秦國表現得最為鮮明。
戰國時代“重利尚武”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值得電影工作者去努力發掘和準確體現。但這又不是提倡主題先行,恰恰相反,這正是歷史真實對于歷史題材電影的迫切要求。然而在電影《荊軻刺秦王》中,嬴政的形象卻顯得陰鷙且神經質,荊軻的形象則顯得輕佻且魯莽,二者都嚴重違背了歷史的真實,也妨礙了國內外觀眾對戰國時代人物性格和文化心理的真切認知。其實,歷史上嬴政的所作所為,無論是被后世贊頌的還是被后世批判的,本質上都不是電影中所指出的他個人性格產生“病態”的結果,而是戰國時代“重利尚武”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發生作用的結果,否則嬴政也不可能成為給中華民族做出過杰出貢獻的一代天驕。荊軻答應太子丹刺秦之前也曾猶豫過,答應之后則開始恣意享受燕國提供的優厚待遇,易水送別時又明知赴死而義無反顧,這個形象才是歷史上真實的荊軻形象,也是荊軻長久被后人歌頌的原因所在。陳凱歌確實是一個充滿濃郁文化情懷的導演,他總是執著地在電影作品中表達自己對中國文化的深沉使命感:“對于我們這個有五千年歷史的中華民族,我們的感情是深摯而復雜的,難以用語言一絲一縷地表達清楚。”[8]如果這種深沉的使命感不能與對歷史的核心文化精神的準確體現結合起來,所謂的使命感就很可能成為有意或者無意歪曲歷史真實的內在驅動力。
歷史經典故事“蘊藏著一定時代、一定民族最彌足珍貴的精神資源,它們能夠跨越時間與空間,向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人們講述有關人性共通之處的動人故事”。[9]歷史題材電影必須準確體現歷史的核心文化精神,這對于克服歷史虛無主義,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可謂意義重大。
結語
歷史題材電影在中國的發展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和廣闊的市場。歷史題材電影必須準確體現歷史的核心文化精神,這既是真實虛構歷史題材電影故事的前提,也是合理滿足觀眾特殊欣賞心理的關鍵,同時還是積極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需要。歷史題材電影必須準確體現歷史的核心文化精神,這并不是倡導圖解歷史,更不是倡導主題先行,而是希望歷史題材電影能夠盡可能地還原歷史的真實。電影工作者只有深刻理解和切實尊重歷史的核心文化精神,并將這種歷史的核心文化精神準確體現在電影中,才可能創作出無愧于歷史、無愧于當代的歷史題材電影精品。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蘇秦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2009:428.
[2]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M].北京:中華書局,2009:455.
[3]朱熹.詩集傳[M].北京:中華書局,1958:79.
[4]班固.漢書·賈鄒枚路傳[M].北京:中華書局,2007:524.
[5]余琍萍,方一舟.影視文學[M].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2:35.
[6]諾埃爾·卡羅爾.超越美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450.
[7]陳林俠.從小說到電影——影視改編的綜合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142.
[8]話說《黃土地》[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6:264-265.
[9]趙明珠.外國經典小說的電影改編及其對中國電影“走出去”的借鑒意義——以《他們眼望上蒼》中的女性身體表達為例[J].
電影評介,2016(2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