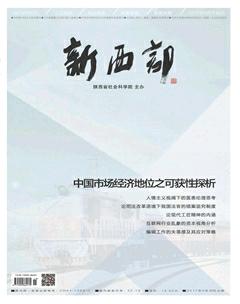試析貝恩·克拉德的抽象空間逃離
方靜
【摘 要】 本文解讀索爾·貝婁《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嘗試從空間角度分析主人公貝恩逃離抽象空間的原因。植物形態學教授貝恩·克拉德,備受抽象空間即高樓大廈、他人對金錢的貪婪以及人造植物的折磨:懼怕資本主義社會,因為“資本主義和新資本主義產生了抽象空間,它凝聚了世界商品、自身邏輯性和策略、金錢的力量和政治國家的力量”。資本主義的失敗者貝恩·克拉德被迫多次逃至絕對空間里的植物世界尋求庇護。
【關鍵詞】 絕對空間;抽象空間;婚姻;金錢;逃跑
一、引言
1915年10月,索爾·貝婁出生于加拿大蒙特利爾市郊的拉辛鎮,父母是來自俄國圣彼得堡的猶太移民。掌握流利的英語、希伯來語、意第緒語和法語的他,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猶太人。從第一部小說《晃來晃去的人》(1944),到最后一部《拉維爾斯坦》(2000),他名聞遐邇。他的小說常批判當代美國社會,明顯拒絕現代傳統的當屬小說《勿失良辰》(1956)。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1987)同樣“闡明了悲喜劇氣氛,現代社會以狂熱步伐阻礙個人試圖尋求精神超脫”,[1]展現了人類經受性關系和社交折磨的痛苦。“貝婁將他的主角(男性,通常為猶太人)拋進可怕的境況,這種境況部分由自身缺點和錯誤觀念引起,因身邊吵鬧的不忠愛人、貪婪的親戚或律師以及瘋狂的陰謀者加劇”[2],小說到處流露著一股焦慮。
國內關于索爾·貝婁的譯著研究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才開始出現。當貝婁1976年獲得諾貝爾獎時,國內沒有任何關于他的作品譯本。“據中文檢索,1979年至2011年9月間,中國期刊發表有關索爾·貝婁的評價文章和論文共三百余篇”。[3]在20世紀90年代,學術研究朝著多元化快速發展。近來,一些學者研究貝婁的荒原主題;一些分析他的猶太性,比如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喬國強教授;還有一些集中于小說的知識分子主題,比如廈門大學的劉文松教授。講師劉兮穎用馬丁·布伯的“對話”哲學分析《更多的人死于心碎》,展現了“猶太知識分子在當代美國社會面臨的倫理困惑和精神危機,以及傳統猶太倫理道德觀念在美國當代社會受到的沖擊”[4]。而籍曉紅則認為貝婁“對后工業社會里的消費主義文化現象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5]。
關于該小說的研究角度不一,然而很少學者從空間角度分析貝恩在愛情和社交上的失敗。空間并非空的容器,它是富含社會屬性的。在法國思想家、馬克思主義者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一書中,空間被分為六階段:絕對空間、神圣空間、歷史空間、抽象空間、矛盾性空間和差異性空間。絕對空間屬于自然狀態;抽象空間“是一個支配性的、征服性的、控制性的與權威性的空間(甚至包括野蠻的粗暴與暴力),一個壓迫性的空間。進而言之,抽象的空間是一個權力工具”[6]。資本主義社會就是一個典型的抽象空間。在植物學取得極具洞察力成就的貝恩,被很多女性視為愛人或丈夫的第一選擇。被她們所傷,他逃至陌生地方以隱藏自己的無能。嚴重依賴外甥肯尼思,貝恩不知如何與周邊人相處。在抽象空間里被兩性關系和資本主義生產折磨的貝恩只能尋求植物所生存的絕對空間的庇護。他遭受心碎愛情和失敗社交,認為“比起核輻射污染來,傷心更讓人致命”[7]。
二、抽象空間的心碎愛情
貝恩·克拉德是植物形態學的教授,有著俄羅斯猶太血統。寫了大量的書籍和文章后,他獲得了很高榮譽。他常去草木繁榮的世界各地,比如中國山川、印度森林、巴西叢林和遙遠南極。這些地方屬于自然狀態,于他有著特殊意義,特別是南極地帶“給人品嘗到永恒的滋味:人的靈魂必須離開溫暖的肌體;在南極你可以練習一下身體不受氣溫影響的功夫,一旦永恒境界到來,人便需要這種功夫”[8]。他沉醉于植物世界,因為“在最單調乏味的野草中,隱藏著空氣、土壤、陽光、繁殖的奧秘”[9]。對植物學洞察力豐富的他來說,植物已然成為朋友,自然空間里的他自由、放松和快樂。
單身十五年,孤單使他意欲尋找情感寄托。聞名遐邇的他被很多女性視為情人或丈夫的優秀人選。在尋求真愛路上因缺乏拒絕女人的能力,純粹自我空間被外界打擾。當征服性極強的肥胖的戴勒·貝岱爾向他尋求性滿足時,他不敢拒絕;一夜情后,貝恩力圖躲避,這給她造成了巨大傷痛。性對戴勒是救命藥和止痛劑,對貝恩卻是毒藥。貝恩只得逃跑至巴西開植物形態學講座,而此時既非美人又非熟人的戴勒死于心臟驟停。他覺得“心碎而死的人確比因原子輻射而猝亡的人更多。然而,并不存在反對心碎的群眾運動,大街上也見不到反對心碎的示威游行”[10]。人們有意識保護自身免受原子輻射的危害,卻無法逃離愛人親人導致的心碎。
“度假勝地或村莊,滑雪場或陽光充沛的沙灘,作為享樂的代表性設施,彰顯著性和性欲、娛樂及肉體滿足”[11]。列斐伏爾此言明確表明,洋溢著性的娛樂設施易使人受控制。剛逃過豺狼,又遇上虎豹。在波多黎各的海邊奢華賭場酒店,他遇到了極具誘惑力的卡羅琳·本治。象征著美麗、性和需求的她,成為貝恩人生的又一入侵者。受她求婚所迫,當她給了航班號和抵達時間后,貝恩急忙逃至東京。沒有真愛的婚姻是囚籠和枷鎖,女性赤裸裸的性需求使他困惑和惡心。
歷經多年的“調情、追求、渴望、入迷、遺棄、侮辱、折磨、性奴役等”[12],他決定以婚姻結束所有折磨。相信瑪蒂爾達能夠給他真愛和平靜婚姻,他選擇了她。然而,在婚姻生活里,他逐漸意識到拜金主義追逐名譽的她并非真愛,卻是一直支配控制他的抽象空間“武士”。妻子提議看電影《驚魂記》,但描繪著抽象空間血淋淋畫面的電影使他恐懼惡心;妻子顯露的寬肩及分離的乳房也一直折磨著他。列斐伏爾提出:“社會空間以身體的使用為先決條件:手的使用,感覺器官和動作姿態。”[13]身體和空間互相聯系,前者是人類體驗外在空間的渠道,身體的重要性顯而易見。當貝恩碎片式地觀察妻子的身體時,之前的美感漸漸消失;當生活碎成千片萬片后,愛情漸被瓦解。他別無選擇只能逃離,而北極則成為療傷的完美絕對空間。
這些女性被描寫為“精明狡猾的女商為了獲得最大利益而謀劃著誘捕男人并與之訂立婚約”[14]。用性愛誘捕貝恩的戴勒、用婚姻支配控制他的卡羅琳和用金錢地位壓迫他的瑪蒂爾達,是抽象空間的代表者。為了逃離女性設下的愛情陷阱和婚姻枷鎖,他分別逃至巴西、日本和北極。不確定愛情和婚姻為何物的他,深感困惑和心碎,漸漸淪為無能男性。
三、抽象空間的消極社交
列斐伏爾指出:“資本主義有多種方面:土地資本、交易資本和金融資本——它們在實踐中發揮各自的作用。”[15]第二次工業革命后,“資本主義那只無形之手偏愛美國,把美國當成自己的寵兒”[16]。美國身為資本主義大國,是一個支配性、征服性、控制性、權威性的抽象空間。生活于美國社會里的貝恩,備受高樓大廈、他人對金錢的貪婪以及人造植物的折磨。懼怕資本主義社會,他多次逃至植物世界尋求庇護。
列斐伏爾認為,建筑“成功地將控制權力的對象和商業交換合并,產生了一個凝聚的殘酷社會關系”[17]。小說里的電子塔樓、阿維尼翁餐館、拉亞蒙家族的兩層公寓和瑪蒂爾達繼承的雷諾克宅邸,對貝恩而言象征著抽象空間的權力。站在充斥著可憎企業的塔樓前,貝恩深感無力和恐慌。塔樓這意象“象征了現代化、工業文明的巨大力量,代表了物質主義對人的侵襲,是現代城市中一切邪惡東西的化身”[18]。和岳父在高聳奢華的阿維尼翁餐館吃飯,貝恩難以下咽;他也無法接受妻子家里的奢華鋪張風格。身于此卻自覺外人,岳母房里的杜鵑花成為了他唯一的慰藉和精神寄托。當拉亞蒙家族唆使他跟舅舅要回錢財來裝修有著二十多個房間的“巨獸”雷諾克并給瑪蒂爾達提供富裕體面的生活時,貝恩茫然不知所措,悲痛心碎。相比之下,他珍惜自己的小公寓,畢竟那里有著快樂的回憶和珍貴的植物。
“資本主義和新資本主義產生了抽象空間,它凝聚了世界商品、自身邏輯性和策略、金錢的力量和政治國家的力量”[19]。貝恩年輕時敬愛自己的舅舅哈羅德·維里茨。當昔日寧靜小房被如今的電子塔樓取代后,舅舅的視財如命使兩人關系破裂。岳父對金錢的野心勃勃、妻子對金錢名譽的渴望以及他們的陰謀算計,使得貝恩想要逃離這冰冷殘酷的世界。“不喜歡那種由于難以把握天然和人造之間的界限而產生的不安情緒”[20],婚禮儀式上不舒服的他寄托于香脂冷杉;住在妻子家里,杜鵑花成為了精神支柱。當他意識到杜鵑是假的后心痛道,“一盆假扮的杜鵑——一個替代,一個圈套,一個騙子,一種擺設,一個引人上當的賭棍!”[21]他的精神支撐蕩然無存。模仿自然的人造物是抽象空間的典型產品,雖有自然特點卻充斥著冰涼的資本主義色彩,也象征著拉亞蒙家族的虛偽情感,時刻壓抑著貝恩。建筑、金錢和假杜鵑花是抽象空間的資本主義化身;舅舅和拉亞蒙家族亦是強大的抽象空間勢力。不知如何與人相處,難過困惑時,貝恩鉆進絕對空間,讓自然治愈破碎的心。簡言之,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敗者。
四、結論
“抽象空間是控制工具,使產生于它而極力想擺脫它的事物感到窒息”[22]。在絕對空間里,因植物不會控制人的思考和主觀能動性,貝恩能表現得強大且富有洞察力,和植物融為一體;而在抽象空間里,愛情和社交需要主人公和自我空間以外的他人發生交集,建立關系。在社交網絡上,他顯得軟弱無能為力,深感窒息。面對肥胖而咄咄逼人的戴勒、魅力誘人的卡羅琳和強勢且追名逐利的瑪蒂爾達,他因害怕對方的支配和控制而逃離至其他地方演講或尋找植物的慰藉;面對舅舅和岳父,他因憎惡經濟空間而茫然,不知如何面對和交流,漸漸反感遠離;面對高樓大廈、資本主義金錢和假植物,他無能為力軟如泡沫。性欲、假物,虛偽和欺詐讓貝恩受盡折磨。在抽象空間里,他一直逃離。為了從拉亞蒙家族的悲痛中尋得精神重生,最終逃跑到北極。“貝婁談及人生、真摯和愛情,但他的小說人物在無愛冷酷的世界上經受精神不安,盡管他們希望尋找到融化他人結凍的心的靈丹妙藥”[23]。貝婁希望人們可以勇敢融入社會,即使過程痛苦,如能蛻變成蝶亦是成功。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貝恩經歷了心碎愛情和失敗社交。被周邊人利用的他悲痛絕望,無法生存于使之窒息的抽象空間。幸運的是,他能夠踏入絕對空間幸免于難,尋得精神境界的重生。
【參考文獻】
[2] Borklund, Elmer. “How It Adds up for Saul Bellow”[J]. The Sewanee Review, Vol. 105, No.3 (Summer, 1997)436-439.
[23] Bronich, M. K. “Russian Allusions in Saul Bellows More Die of Heartbreak”[A]. Saul Bellow Journal[C]. Eds. Goldman, Liela., and Gloria L. Cronin. Michigan: 1999.31-36.
[1] Cronin, Gloria L. “Holy War Against the Moderns: Saul Bellows Antimodernist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J]. Studies in American Jewish Literature, Vol. 8, No.1 (Spring,1989): 77-94.
[11][13][15][17][19][22]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London: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14] Zheng, Li. “Liberating Pandora: A Study of the Female Images and Bisexual Relationship in Saul Bellows Four Novels” [D]. Master thes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2007.
[5] 籍曉紅. 索爾·貝婁對消費主義的批判——以《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為例[J]. 外國文學研究.2008.5.125-130.
[18] 塔樓與故鄉的村莊——小說《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的意象解讀[J]. 電子科技大學學報,2013.3.78-82.
[4] 劉兮穎.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的“對話”哲學[J]. 外國文學研究,2007.6.121-129.
[3] 喬國強. 貝婁學術史研究[M]. 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7][8][9][10][12][16][20][21] 索爾·貝婁.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6] 吳冶平.空間理論與文學的再現[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2008.
【作者簡介】
方 靜 (1992.04-)女,漢族,福建漳州人,碩士在讀,研究方向:英美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