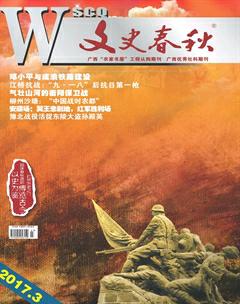京杭運(yùn)河:古代貫通南北的漕運(yùn)大動(dòng)脈
高秀麗
中國(guó)的京杭運(yùn)河是世界上開(kāi)鑿時(shí)間最早、流程最長(zhǎng)的一條人工運(yùn)河,它創(chuàng)始于春秋時(shí)期,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開(kāi)鑿的從江都(今揚(yáng)州)到末口(今淮安)的南北水道邗溝,距今已有2400多年的歷史。從此以后,中國(guó)人民一代接一代,以其勤勞、智慧和堅(jiān)強(qiáng)的毅力,由短到長(zhǎng),從局部到整體,不斷地開(kāi)鑿整修,持續(xù)了1000多年的時(shí)間,直至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終于完成了一條由杭州直達(dá)北京,縱貫?zāi)媳钡娜斯ご筮\(yùn)河。大運(yùn)河全長(zhǎng)1782公里,跨越今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四省二市,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zhǎng)江、錢(qián)塘江五大水系。長(zhǎng)度是巴拿馬運(yùn)河的21倍,是蘇伊士運(yùn)河的9倍。京杭大運(yùn)河不僅是許多王朝賴以生存的南糧北運(yùn)的大動(dòng)脈,也是傳統(tǒng)漕運(yùn)的主要交通渠道和可靠保障,更是我國(guó)古代經(jīng)濟(jì)交流的生命線。運(yùn)河的防務(wù)不僅是封建王朝的國(guó)家機(jī)器,同時(shí)也使軍隊(duì)和地方的百姓在這條賴以生存的河流上產(chǎn)生了更加緊密的聯(lián)系和依靠。這種聯(lián)系和依靠體現(xiàn)在經(jīng)濟(jì)、文化、民俗、科技、宗教等各個(gè)方面。
古代漕運(yùn)的重要河道
隋煬帝統(tǒng)一中國(guó)之后,先后開(kāi)鑿了永濟(jì)渠、通濟(jì)渠,并重修了江南運(yùn)河,終于鑿成和疏通了以東都洛陽(yáng)為中心,北起北京、南達(dá)杭州的京杭大運(yùn)河。唐代的運(yùn)河基本上是沿用了隋代大運(yùn)河的體系,只做了局部的變更和修整。所以后人有“隋朝開(kāi)河,唐宋收益”之說(shuō)。《新唐書(shū)·食貨志》說(shuō):“唐都長(zhǎng)安,而關(guān)中號(hào)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于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zhuǎn)漕東南之粟。”以運(yùn)河轉(zhuǎn)輸江南之粟成為保障京師糧食供應(yīng)的重要之路。北宋也十分重視開(kāi)發(fā)運(yùn)河交通運(yùn)輸,通過(guò)開(kāi)鑿整治舊運(yùn)河河道,把江浙、兩淮、荊湖等南方地區(qū)與河北、京畿一帶等北方地區(qū)連接起來(lái)。南宋也大力疏浚江南運(yùn)河以供運(yùn)輸。元代建國(guó)都于大都,也依賴江南糧米,《元史》云:“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運(yùn),百司庶府之繁,衛(wèi)士編民之眾,無(wú)不仰給江南。”
從歷代運(yùn)往京師的漕米供應(yīng)數(shù)量來(lái)看,運(yùn)河交通對(duì)于繁榮京畿也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據(jù)史籍記載,隋朝時(shí)期,就在運(yùn)河沿岸建倉(cāng),逐漸形成了“瀕河倉(cāng)廩”的布局。唐開(kāi)元年間“凡三歲,漕七百萬(wàn)石”比陸運(yùn)節(jié)省“傭錢(qián)三十萬(wàn)緡”,每年山東漕運(yùn)量在400萬(wàn)石以上。宋代建國(guó)都于汴京(今開(kāi)封),至宋神宗時(shí),定汴河漕量,“歲額600萬(wàn)石”。故時(shí)人有“四河所運(yùn),惟汴河最重”“大眾之命,惟汴河是賴”的緒論,說(shuō)明了汴河漕運(yùn)在整個(gè)漕運(yùn)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元代晚期,由運(yùn)河轉(zhuǎn)海運(yùn),每年至京師的糧食近350萬(wàn)石。明代永樂(lè)年間,最多時(shí)達(dá)到460萬(wàn)石。清代漕運(yùn)量雖有的年份有所增加,但大多年份的運(yùn)量仍維持在400萬(wàn)石左右,但其他品種的輸送量則大有增加,如南方的竹子、木材、茶葉、白糖、絲綢等。正因?yàn)榫┖歼\(yùn)河與京師供給、大宗運(yùn)輸、經(jīng)濟(jì)交流、百姓生活有著如此密切的關(guān)系,所以歷代朝廷都將運(yùn)河的暢通視為“社稷之要”,并置衙設(shè)官司,投以巨資,頒布行律令,嚴(yán)加管理。
運(yùn)河流域文化大融合
運(yùn)河流域文化是自隋開(kāi)通南北大運(yùn)河以來(lái)形成的,從全國(guó)的角度來(lái)看,運(yùn)河流域的文化是隋唐時(shí)期中國(guó)民族融合統(tǒng)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區(qū)域文化不僅包括黃河文化、長(zhǎng)江文化,而且還有因南北文化的碰撞、融合而形成的一種新型文化。運(yùn)河區(qū)域本身是一個(gè)開(kāi)放的概念,以洛陽(yáng)為中心,貫通南北,它將我國(guó)幾大水系錢(qián)塘江、長(zhǎng)江、淮河、黃河、海河溝通,這幾條水上大動(dòng)脈將沿途各地聯(lián)系在一起。中國(guó)土地遼闊,從南到北、從沿海到內(nèi)地,地理環(huán)境相距甚大,各地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文化。運(yùn)河以它的貫通性,汲取各地文化的滋養(yǎng),形成運(yùn)河文化的浩浩長(zhǎng)流,因而,運(yùn)河文化也是開(kāi)放性的。這種文化具有較強(qiáng)的拓展性,善于兼蓄外來(lái)文化,融會(huì)貫通,逐步豐富自己的文化內(nèi)容。如胡樂(lè)、胡舞、胡服,在運(yùn)河流域就風(fēng)靡一時(shí)。元稹的《法曲》云:“女為胡婦學(xué)胡妝,五十年來(lái)竟紛泊。”說(shuō)明唐朝在音樂(lè)、服裝上吸取了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內(nèi)涵。這種開(kāi)放性,不僅體現(xiàn)在吸收國(guó)內(nèi)各地的文化精華,而且還吸收外來(lái)文化的精華。如印度佛教傳人中國(guó)后,逐漸受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而中國(guó)化,在運(yùn)河沿線的長(zhǎng)安、洛陽(yáng)、楚州、揚(yáng)州、蘇州、杭州都建有大量的寺觀,而且都成為運(yùn)河流域佛教傳播的中心。如揚(yáng)州城內(nèi)有三四十座佛寺,其中華林寺、慧照寺、孝感寺、龍興寺、大云寺、西靈塔寺、禪智寺、大明寺、既濟(jì)寺、崇富寺、白塔寺、法云寺、興云寺、開(kāi)元寺、棲靈寺等均見(jiàn)諸記載。鑒真就是揚(yáng)州佛教界的著名律師(善解戒律者之稱)。揚(yáng)州就成為江淮地區(qū)最大的佛教傳播基地。從中國(guó)文化史上考察,外國(guó)文化進(jìn)入中國(guó),經(jīng)過(guò)中華文化的吐納和改造,創(chuàng)生新的形態(tài),中華文化正緣此不斷納新,得以生生不息,兼容與開(kāi)放,蔚為中國(guó)文化昌盛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加強(qiáng)漕運(yùn)的管理
唐初的漕運(yùn)管理仍習(xí)隋制,由都水使者、都水臺(tái)或都水監(jiān)掌管治河與漕運(yùn)兩職。唐玄宗開(kāi)元初年,為了加強(qiáng)漕運(yùn)的管理,設(shè)置了專管漕運(yùn)的轉(zhuǎn)運(yùn)使。自此以后,治河與漕運(yùn)分管,這就加強(qiáng)了漕運(yùn)管理的職能和權(quán)力。漕運(yùn)官員的職責(zé)是根據(jù)漕運(yùn)路線而設(shè)置的,不受行政區(qū)劃約束,往往由位極人臣的宰相兼領(lǐng),職權(quán)很大。漕運(yùn)官員的職責(zé)就是:將各地征集的糧食和貢品進(jìn)行驗(yàn)收、保管、運(yùn)輸,并組織人力押送、護(hù)運(yùn):管理漕運(yùn)船艫,還監(jiān)督沿河百姓不得盜用漕河之水“溉田”,以保證運(yùn)河的水量。唐開(kāi)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皇帝了解到大臣裴耀卿深諳漕運(yùn)之事,“拜耀卿為黃門(mén)侍郎同中書(shū)門(mén)下平章事,瘺江淮都轉(zhuǎn)運(yùn)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甲蕭炅為副使”此為運(yùn)河漕運(yùn)高官之始。
這時(shí)的漕運(yùn)分量主要在黃河之南河段。在唐代,“自裴耀卿言漕事進(jìn)用者常兼轉(zhuǎn)運(yùn)之職,而韋堅(jiān)為最”。唐代漕運(yùn)防務(wù)主要是都轉(zhuǎn)運(yùn)使司派員負(fù)責(zé)、派員押運(yùn),并無(wú)固定防務(wù)機(jī)構(gòu)。沿運(yùn)各段的河務(wù)管理均由當(dāng)?shù)毓?jié)度使負(fù)責(zé)。如“汴宋節(jié)度使春夏遺官司監(jiān)汴水,察盜灌溉者”。
北宋,國(guó)都汴京,每年從江南運(yùn)送來(lái)的稅糧亦不下600萬(wàn)石。沿運(yùn)設(shè)發(fā)運(yùn)司河轉(zhuǎn)運(yùn)使司,置漕臣。各地漕臣負(fù)責(zé)本地漕糧的集運(yùn),聽(tīng)候漕運(yùn)物質(zhì)的調(diào)用。如,紹圣年間,宋哲宗“詔淮、浙、江、湖六路上供米,計(jì)其遠(yuǎn)近分三限,自季冬至明年8月。在漕運(yùn)業(yè)務(wù)上,亦屬“發(fā)運(yùn)使司”節(jié)制。宋代基層漕運(yùn)單位稱為“綱”,各有自己的船隊(duì)、人員。宋哲宗紹圣二年(1095年),“通作二百綱”,即全國(guó)已有漕運(yùn)單位200個(gè)。有關(guān)宋代漕運(yùn)防衛(wèi),《宋史》卷一七五有載:“押汴河江南、荊湖綱運(yùn),七分差三班使臣,三分軍大將、殿侍。”汴河,即運(yùn)河中段,代指運(yùn)河。“綱運(yùn)”,宋代語(yǔ)言,即“漕運(yùn)”。這里是說(shuō),江南綱、荊湖綱的漕運(yùn)當(dāng)差押運(yùn)者,有七成隸屬三班使臣,三成隸屬大將、殿侍。換言之,有70%的押運(yùn)者為漕運(yùn)人員,30%的押運(yùn)者為兵卒,這便是軍隊(duì)介入護(hù)漕的開(kāi)始。
元代前期,基本無(wú)運(yùn)河漕運(yùn),京城元大都需要的南方漕米、貢品,主要靠海運(yùn)。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京杭運(yùn)河全線貫通,南方漕米才通過(guò)運(yùn)河運(yùn)往京師。起初,漕運(yùn)均交各省巡撫派員負(fù)責(zé),沿線有行都水監(jiān)協(xié)助。直至元惠宗后至元二年(1336年),才有京畿都漕運(yùn)司添設(shè)提運(yùn)使、同知、副使、判官、經(jīng)歷、知事等職,負(fù)責(zé)運(yùn)河的漕運(yùn)。但這個(gè)機(jī)構(gòu)駐節(jié)京師,大凡具體的漕運(yùn)、防務(wù)仍由各行省負(fù)責(zé)。為擴(kuò)大漕運(yùn)規(guī)模,朝廷曾“命三省造船兩千艘于濟(jì)州(今濟(jì)寧)”運(yùn)糧(《元史·食貨志》)。
明清時(shí)期是京杭運(yùn)河最繁盛的時(shí)期,這時(shí)期設(shè)置的河漕機(jī)構(gòu)規(guī)格高、分工細(xì)、作用大,經(jīng)常受到皇帝的“眷顧”,許多官員也將任職河漕視為“肥缺”。
明代初年曾仿元制,洪武年間設(shè)漕運(yùn)使。漕運(yùn)使,正四品,下設(shè)知事(正八品)、提控案牘(從九品)等官司員。永樂(lè)年間設(shè)漕運(yùn)總兵官司,“掌漕運(yùn)河道之事”,河道由漕運(yùn)總督兼任。首任即是平江伯陳碹。成化十七年(1481年)始設(shè)總理河道,駐地濟(jì)寧,與總漕平行。總河專管主持河道修治,總漕專理漕政。這是正式設(shè)立的漕運(yùn)總督,正二品,兼任當(dāng)?shù)匮矒幔偎狙迷O(shè)在淮安。嘉靖四十年(1561年),“改總督漕運(yùn)兼提督軍務(wù)”。漕運(yùn)總督兼任漕運(yùn)軍職,成為明代后期及其清代常見(jiàn)的機(jī)構(gòu)命官模式,軍政合一在漕運(yùn)管理中有著重要意義,它有利于漕運(yùn)管理的穩(wěn)定,體現(xiàn)著漕運(yùn)機(jī)構(gòu)的重要地位與特色,這是發(fā)展漕運(yùn)、促進(jìn)沿河經(jīng)濟(jì)繁榮的組織保障。明代漕運(yùn)總督屬下還設(shè)有漕運(yùn)行管機(jī)構(gòu)——漕儲(chǔ)道,駐漕運(yùn)防務(wù),運(yùn)河沿岸重鎮(zhèn)均設(shè)立了衛(wèi)所。如:德州衛(wèi)、臨清衛(wèi)、濟(jì)寧衛(wèi)、徐州衛(wèi)、邳州衛(wèi)、淮安衛(wèi)、高郵衛(wèi)、揚(yáng)州衛(wèi)、鎮(zhèn)江衛(wèi)、杭州衛(wèi)等,其隸屬關(guān)系并非全部屬于河、漕衙門(mén),但強(qiáng)化沿運(yùn)防務(wù)是明代軍事布防的基本宗旨。
清代漕運(yùn)防務(wù)較多地沿襲了明代晚期的設(shè)防格局,但又有調(diào)整。主管漕運(yùn)的最高長(zhǎng)官為漕運(yùn)總督,順治元年(1644年),漕運(yùn)總督部院署常駐淮安,其下屬防務(wù)機(jī)構(gòu)“標(biāo)兵及左右營(yíng)如制,將領(lǐng)九或八人,兵共四千有奇”。設(shè)“蘇州、鎮(zhèn)江、浦口、安慶、池太、東山、廣德八鎮(zhèn)總兵官”。《清史稿·兵志二》又云:“漕運(yùn)總督統(tǒng)轄各衛(wèi)所處,復(fù)統(tǒng)轄旗、綠、漕標(biāo)三營(yíng),兼轄淮安城守營(yíng)。”共計(jì)七營(yíng)。關(guān)于七營(yíng)的防務(wù)分工,《清史稿·兵志六》有載:“漕運(yùn)總督水師標(biāo)營(yíng),分中、左、右城守四營(yíng)。以中、左、右三營(yíng)任護(hù)漕之責(zé):以城守四營(yíng)任地方之責(zé):駐山陽(yáng)(今淮安市)境及漕運(yùn)所駐之地。其運(yùn)挽漕糧,則以衛(wèi)卒任之。”
統(tǒng)籌治水,管理河道
水運(yùn)水利的設(shè)官制度比較早,京杭運(yùn)河貫通后,唐宋元三代均設(shè)立“都水監(jiān)”,以統(tǒng)籌治水,管理河道。唐代都水監(jiān)設(shè)使者二人。使者,為正五品,
“掌川澤、渠堰、陂池之政,總河渠、諸津監(jiān)督”:并設(shè)都水監(jiān)丞二人,從七品;主簿一人,從八品。下屬機(jī)構(gòu)有“河渠署”,設(shè)河渠令一人,正八品;丞一人,正九品:河渠謁者六人,正八品。都水監(jiān)為水利治河專門(mén)機(jī)構(gòu),隸屬工部。為更好的管理好此事,工部還專設(shè)水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以分管并協(xié)調(diào)與都水監(jiān)的公務(wù)關(guān)系。宋代起,中央專門(mén)設(shè)立管理水利的專門(mén)機(jī)構(gòu),河渠案,又于嘉祜三年(1058年)設(shè)置都水監(jiān),都水監(jiān)下設(shè)河溝司等。元代起,配齊官員及其機(jī)構(gòu)。《元史·河渠志》言:“元有天下,內(nèi)立都水監(jiān),外設(shè)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修理河堤為務(wù)”。都水監(jiān)為元朝中央政府主管水政的機(jī)構(gòu),其官署設(shè)都水監(jiān)二人,少監(jiān)一人,監(jiān)丞二人,經(jīng)歷、知事各一人,下設(shè)令史、通事、知印、奏差、壕寨、典吏等屬官,以賺掌河渠、堤防、水利、橋梁、堰閘諸政。據(jù)考,唐宋時(shí)期的運(yùn)河河道防務(wù)沒(méi)有專職隊(duì)伍,只有治水機(jī)構(gòu)兼管。《宋史·食貨志上》記載:“靖康初,汴河決口有至百步者,塞之,工久未訖,干涸月余綱運(yùn)不通,南京及京師皆乏糧。責(zé)都水使陳求道等……同措置,水復(fù)舊,綱運(yùn)沓至,兩京糧乃足。”這說(shuō)明運(yùn)河無(wú)防務(wù),不然的話,不會(huì)河決百多步才責(zé)令都水監(jiān)使者“措置”。
明代最高河道管理機(jī)構(gòu)設(shè)在濟(jì)寧,成化七年(1471年),始設(shè)總理河道,或叫河道總督。總理河道一職為朝廷派出官員,常以侍郎、尚書(shū)銜領(lǐng)其職,總河以下按運(yùn)道設(shè)有分司,分司多由工部都水監(jiān)派遣,除朝廷統(tǒng)一派出的官司機(jī)構(gòu)外,沿運(yùn)各省也分派地方官吏參與管理河道之事。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都御史加工部銜,提督河南、山東、直隸河道。隆慶四年加提督軍務(wù)”。據(jù)《山東通志·兵防志》記載,為了運(yùn)河的防護(hù),永樂(lè)十八年(1420年),曾遣都御史負(fù)責(zé)沿運(yùn)防務(wù)。隆慶四年(1570年)在濟(jì)寧駐防的濟(jì)寧衛(wèi)、擁兵5600人,隸濟(jì)寧兵備道管轄,是河道總督署下設(shè)的專職防務(wù)機(jī)構(gòu)。《明史·兵防三》還記載:“治河之役,給事中張貞觀請(qǐng)益募士兵,捍淮、揚(yáng)、徐、邳”,經(jīng)皇帝允準(zhǔn),這四地駐兵也曾由河督節(jié)制以護(hù)衛(wèi)河道。
清代河道管理機(jī)構(gòu)基本上沿襲明代舊制,并逐漸調(diào)整簡(jiǎn)化,系統(tǒng)更加分明。清代的河道總督是管理運(yùn)河的最高行政長(zhǎng)官,原駐山東濟(jì)寧,后移駐江蘇清江浦,后增設(shè)副總河。雍正年間總河一分為三:一為江南河道總督,管理江蘇、安徽兩省的黃淮運(yùn),簡(jiǎn)稱南河,駐清江浦:二為東河河道總督,管理河南、山東兩省的黃、運(yùn)兩河,簡(jiǎn)稱東河,駐濟(jì)寧;三為直隸河道總督,管理海河水系及運(yùn)河,簡(jiǎn)稱北河,駐天津。北河、東河、南河為三督,共同掌治河渠,以時(shí)疏浚堤防,綜其政令,營(yíng)制視漕督地方河道管理機(jī)構(gòu)為三級(jí):道、廳、汛分段管理,并設(shè)有文職、武職兩系統(tǒng)。“道”相當(dāng)于明代的都水司,武官有河標(biāo)副將、參將等:“廳”與地方的府、州同級(jí),設(shè)同知、通判;“汛”同縣級(jí)、設(shè)縣丞、主薄等。武職,廳設(shè)守備,汛設(shè)千總等。“《清史稿·兵志二·綠營(yíng)兵》記載:“定山東官兵經(jīng)制,設(shè)副將或游擊以下將領(lǐng)八,兵凡三千,備河防護(hù)運(yùn)。”河道總督轄中軍署,中軍又稱為將軍,專司運(yùn)河河道的防務(wù)。其直屬的中營(yíng)、左營(yíng)、右營(yíng)、濟(jì)寧城守營(yíng)的防區(qū),南至徐州界,北至張秋“今屬東平縣張秋鎮(zhèn)”全長(zhǎng)365公里,下轄49汛。
據(jù)考,明清時(shí)期的漕督衙署、河督衙署均配置軍用船只。漕運(yùn)總督署的軍船主要是為漕運(yùn)船隊(duì)護(hù)航,河道總督署的軍船主要用于巡視河堤、橋閘,護(hù)理河道,打擊河盜,維護(hù)京杭運(yùn)輸線上的秩序。1956年4月,在梁山縣運(yùn)河西側(cè)的宋金河中出土了一艘明代兵船,現(xiàn)藏山東省博物館。該船呈柳葉形,船身全長(zhǎng)21.8米,中寬3.44米,共13個(gè)大小相同的船艙,各艙相通。船內(nèi)遺留有銅銃(即炮)、銅盔、軍刀、劍、鍘、剪、鋸、起子、馬鞍、馬鐙、馬嚼、錨、錢(qián)幣等金屬制品及瓷瓶、瓷碗等生活用品共計(jì)174件。“洪武五年造,一千三十九號(hào),八十斤重。”從器銘我們得知,這艘軍船用于運(yùn)河“護(hù)衛(wèi)”,為明代洪武年間制造。船錨已編號(hào)至“一千三十九號(hào)”就已說(shuō)明,軍船的數(shù)量是相當(dāng)可觀的。
除護(hù)河、護(hù)漕船只外,各衛(wèi)所、標(biāo)營(yíng)還配備有刀、槍、重炮。濟(jì)寧市博物館現(xiàn)藏有元明清鐵炮38尊,其中兩尊分別鑄造銘文:“崇禎拾叁年捌月總督兩廣軍門(mén)張行委濟(jì)寧衛(wèi)掌印指揮張古臣督造”“濟(jì)寧運(yùn)河道捐資鑄造崇禎拾……濟(jì)寧指揮張臣監(jiān)造”等字。其余均曾用于標(biāo)營(yíng)駐地的防護(hù)。
在清代運(yùn)河的防務(wù)中,由于時(shí)代發(fā)展需要和外國(guó)水哉設(shè)防經(jīng)驗(yàn)的傳人,部分區(qū)段還設(shè)立了水師,以熟習(xí)水性的士兵為主要兵員。如:“直隸水師四百七十六人,舢板戰(zhàn)船三十二艘,駐三貧河口。”濟(jì)寧“利捷水師營(yíng)”于1868年設(shè)立,哨官1人,水師25人,船24艘。南河漕督及河督也設(shè)立了水師。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河道總督裁撤,河漕管理及其防務(wù)均由地方分段管理,茲不贅述。
結(jié)語(yǔ)
京杭運(yùn)河是沿岸各地的母親河,是中國(guó)七世紀(jì)之后歷代封建政權(quán)的生命河,它的興衰曾與國(guó)家的興衰,沿岸的經(jīng)濟(jì)繁榮相關(guān)聯(lián),因而,研究這條古老的河,并古為今用,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現(xiàn)實(shí)意義。運(yùn)河防務(wù)便是其中課題之一。
綜上所述,唐、宋之際的運(yùn)河,因國(guó)都位于關(guān)中、中原,故黃河之南的運(yùn)河發(fā)揮了巨大作用,由于江淮運(yùn)河及江南運(yùn)河不易淤積,航道長(zhǎng)期保持良好狀態(tài),故漕運(yùn)發(fā)達(dá),漕運(yùn)防務(wù)體系初步確立。而北段運(yùn)河利用率低,發(fā)揮的作用較小,所以,常受黃河干擾的北運(yùn)河沒(méi)有受到朝廷的應(yīng)有重視,河道管理機(jī)構(gòu)沒(méi)有健全,河道防務(wù)初萌。南宋時(shí)期,宋、金以淮河為界,長(zhǎng)期對(duì)峙,官家漕運(yùn)受阻,分裂的局面使運(yùn)河管理分割,南北交流幾乎終止。元代著手運(yùn)河的直線溝通,河漕防務(wù)尚未受到應(yīng)有的重視,故效果甚微。明清兩代是運(yùn)河管理機(jī)構(gòu)、漕運(yùn)機(jī)構(gòu)的健全時(shí)期,故運(yùn)河的疏浚、漕運(yùn)、防務(wù)、信息傳遞都達(dá)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機(jī)構(gòu)級(jí)別之高,管理人員之眾、分工之細(xì),可與今天發(fā)達(dá)的陸路管理相媲美。據(jù)史載,清代河道總督屬下還設(shè)有河標(biāo)信息機(jī)構(gòu),名為“撥遞”,共設(shè)41撥、82丁,凡沿運(yùn)河防信息,短時(shí)間就可傳到總河署,或直傳京城。
漕運(yùn)、治河機(jī)構(gòu)正式建立后,也曾有過(guò)合并、短期裁撤,如:明萬(wàn)歷七年(1579年),漕運(yùn)總督“加兼管河道”河漕合并,合并后南方由漕運(yùn)總督負(fù)責(zé)治河,山東、直隸則交巡撫“兼管河道”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罷設(shè)總督”,治河與防務(wù)交由地方巡撫負(fù)責(zé)。
運(yùn)河防務(wù)機(jī)構(gòu)的駐軍除非常時(shí)期外,無(wú)軍隊(duì)的緝捕職能。如《清史稿·兵志六》云:“淮群舊為黃淮交匯之區(qū),特建兩大閘,設(shè)河兵及堡兵守之,河營(yíng)遂之漕營(yíng)并重……河營(yíng)升遷之例與軍功同,專司填筑堤筑堤防之事,而緝捕之責(zé)不與焉。”但調(diào)防仍屬軍隊(duì)性質(zhì)。如:順治六年至康熙六十一年,“裁撥抽調(diào)馬步兵共貳千零叁拾貳名”,其他年份也常有河防兵員調(diào)防。突發(fā)事件時(shí),其他駐軍也調(diào)入強(qiáng)化運(yùn)河防務(wù)。再如,清代咸同年間,捻軍活動(dòng)于蘇魯運(yùn)河沿線,皇室驚恐,特派僧格林沁率清軍,李鴻章率淮軍,加強(qiáng)運(yùn)河防務(wù)。1867年2月,“山東巡扶丁寶楨部署東軍加強(qiáng)運(yùn)河防線,并派水師在運(yùn)河巡河。”6月30日,“李鴻章至濟(jì)寧行營(yíng),辭行劃倒守運(yùn)河防線”。10月26日,“李鴻章在濟(jì)寧大營(yíng)組建淮軍游擊師三支,各一萬(wàn)人,配合六七萬(wàn)運(yùn)河河防軍,追堵東捻軍”。
從歷史上看,貫通南北的大運(yùn)河對(duì)歷代封建王朝的政治局勢(shì)有著具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隋唐以后,運(yùn)河的開(kāi)鑿與開(kāi)發(fā),無(wú)不是圍繞著鞏固和強(qiáng)化皇朝統(tǒng)治而展開(kāi)的,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出于軍事需要和經(jīng)濟(jì)需要。由于運(yùn)河區(qū)域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始終處于政治、軍事、經(jīng)濟(jì)、文化諸方面的中心地位,因而成為歷代封建皇朝著力控制的最重要的區(qū)域,每一代皇朝統(tǒng)治者也都要憑借運(yùn)河這個(gè)理想的地理位置、優(yōu)越的經(jīng)濟(jì)條件和人文環(huán)境,總攬大局,駕馭全國(guó)。同樣,當(dāng)皇朝遞變與變革之際,發(fā)生在運(yùn)河區(qū)域的戰(zhàn)爭(zhēng),包括統(tǒng)治階級(jí)內(nèi)部的戰(zhàn)爭(zhēng)、農(nóng)民戰(zhàn)爭(zhēng)和民族戰(zhàn)爭(zhēng)最多,也最為激烈。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shuō),誰(shuí)控制了運(yùn)河,誰(shuí)就能取得戰(zhàn)爭(zhēng)的勝利,誰(shuí)就能建立起穩(wěn)定的對(duì)全國(guó)的政治統(tǒng)治。因此,大運(yùn)河也就成了維系中央集權(quán)和中國(guó)大一統(tǒng)局面的政治紐帶,使隋唐以后政治中心逐漸北移的歷代皇朝呈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大一統(tǒng)色彩,特別是元朝實(shí)現(xiàn)全國(guó)統(tǒng)一以后,直至明、清兩朝,中國(guó)再也沒(méi)有出現(xiàn)大的分裂,從而奠定了祖國(guó)大一統(tǒng)局面的堅(jiān)實(shí)基礎(chǔ)。大運(yùn)河的貫通,大一統(tǒng)局面的形成,又加強(qiáng)了國(guó)內(nèi)各民族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與融合,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了民族團(tuán)結(jié)和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中華民族是一個(gè)民族融合大家庭,文化的差異源于自然條件的差異,軍事上的封建割據(jù)所形成的政治上的隔絕,隨著運(yùn)河的南北大貫通和迅速開(kāi)發(fā),運(yùn)河區(qū)域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達(dá)到了前所未有的興盛與繁榮,這不僅為運(yùn)河區(qū)域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質(zhì)基礎(chǔ),而且也促進(jìn)了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使各種地域文化和外來(lái)文化相互接觸、融合、整合,形成了獨(dú)具特色的運(yùn)河文化。
運(yùn)河文化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統(tǒng)一性,廣闊的擴(kuò)散性和開(kāi)放性,強(qiáng)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僅加強(qiáng)了中國(guó)傳統(tǒng)思想文化發(fā)源地齊魯?shù)貐^(qū)與中原地區(qū)、江南地區(qū)的文化交融,更把漢唐的長(zhǎng)安、洛陽(yáng),兩宋的開(kāi)封、杭州和金、元、明、清的北京文化中心連為一體,不斷減少區(qū)域文化的差異而呈現(xiàn)共同的文化特征,從而使各個(gè)區(qū)域文化融合為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的大一統(tǒng)文化,同時(shí)也使運(yùn)河區(qū)域成為人才薈萃之地,文風(fēng)昌盛之區(qū)。大運(yùn)河的水哺育了許多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科學(xué)家、發(fā)明家、文學(xué)家和藝術(shù)家,他們不但對(duì)運(yùn)河文化的發(fā)展作出了重大貢獻(xiàn),而且對(duì)中國(guó)歷史乃至世界歷史都有著廣泛而深遠(yuǎn)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