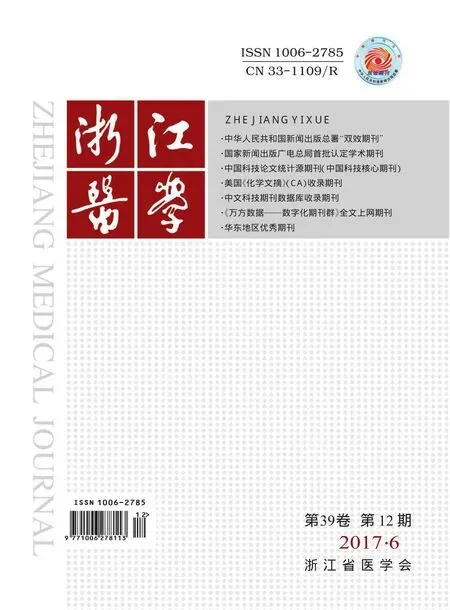認知行為療法在慢性疲勞綜合征康復中的應用效果
金玉蓮 黃海曉 趙娜 楊亞芳 楊曉麗 鄭勝利 陳亞林 林崇光
●護理園地
認知行為療法在慢性疲勞綜合征康復中的應用效果
金玉蓮 黃海曉 趙娜 楊亞芳 楊曉麗 鄭勝利 陳亞林 林崇光
目的 探討認知行為療法(CBT)在慢性疲勞綜合征(CFS)康復中的應用效果。方法 選擇給予常規護理+CBT(干預組)、僅常規護理(對照組)的CFS患者各60例,采用疲勞量表-14(FS-14)、抑郁自評量表(SDS)、焦慮自評量表(SAS)評價與比較兩組患者的療效。結果 干預前兩組患者FS-14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干預12周后,干預組FS-14、SAS、SDS均低于干預前(均P<0.05),且干預組均低于對照組(均P<0.05)。結論 CBT能促進CFS的康復。
慢性疲勞綜合征 認知行為療法 運動處方
慢性疲勞綜合征(CFS)是以全身持續、反復發作的嚴重疲勞為主要臨床表現的證候群,其臨床特征為不少于6個月的持續或反復發作的疲勞狀態,且非從事的工作引起,經休息后不能緩解,臨床評價后無法解釋,并伴隨有記憶力減退、頭痛、咽喉痛、關節痛、淋巴結腫大、睡眠紊亂、抑郁等多種軀體及精神神經癥狀。我國CFS人群約占1/3,其心理方面的異常表現可能比軀體方面出現得早;目前藥物治療對CFS的效果有限。認知行為療法(CBT)是一種通過改變思維、信念及行為來改變不良認知,達到消除不良情緒及行為的短程心理治療的方法。該療法已廣泛用于精神科臨床和心理咨詢門診中,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CFS患者中的應用還不多。因此,筆者設計本研究以探討CBT在促進CFS康復中的療效,為CBT的推廣應用提供依據。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選擇2016年1至8月在溫州市第七人民醫院治療的120例CFS患者為研究對象,其中干預組(常規護理+CBT)、對照組(常規護理)各60例。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1994年制定的標準診斷CFS:(1)記憶力或注意力下降而導致職業能力、接受教育能力、社會活動能力及個人生活能力等出現實質性下降;(2)咽痛;(3)頸部或腋窩淋巴結觸痛;(4)肌肉疼痛;(5)不伴有紅腫的多關節疼痛;(6)發作方式、類型及嚴重程度與以往不同的頭痛;(7)睡眠后不能恢復精力;(8)疲勞持續>24h。入選標準:年齡18~45周歲,學生或白領階層,初中及以上文化水平;持續疲勞時間>6個月,經休息后不能緩解;至少具備CFS診斷標準8項伴隨癥狀中的4項;經實驗室常規檢查、體格檢查排除其他引起疲勞癥狀的疾病。排除標準:無疲勞主訴,或伴隨癥狀少于4項;經休息后疲勞癥狀可以緩解;疲勞癥狀不引起工作能力、接受教育能力、社會活動能力及個人生活能力實質性下降;具有其他疾病明確診斷;懷孕或哺乳期婦女;嚴重肥胖;最近1個月參與臨床藥物實驗。本研究經醫院倫理委員會同意,且與所有受試者簽署知情同意書。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1。
1.2 干預方法 對照組予常規治療及護理,主要包括藥物治療、營養支持、定期體檢及健康教育;干預組在常規護理及治療的基礎上實施CBT。CBT具體流程如下,(1)成立課題組:由2位精神科醫生、2位內科醫生、5位治療師、3位康復師、3位護士組成科研小組,邀請著名專家及心理咨詢師對小組成員進行分工、制定目標等培訓,對各種測量工具及目標進行一致性評定。經培訓后的治療師每人負責12例患者。(2)統一流程:認知探查→找出核心信念→情緒ABC理論(三欄技術處理)→核心信念矯正→行為訓練→重新評價。認知探查:課題組成員設計評估量表進行定性訪談,量表條目包括性別、年齡、愛好、職業、業余時間、目前存在的壓力、軀體不適情況、患者的擔憂、最想解決的問題、支持系統等。找出核心信念:心理咨詢師運用蘇格拉底式詢問技術引導患者自動思維,并總結出患者的核心信念。情緒ABC理論:由美國心理學家埃利斯創建,認為激發事件A只是引發情緒和行為后果C的間接原因,而引起C的直接原因是個體對激發事件A的認知與評價而產生的信念B;即人的消極情緒與行為障礙結果(C)不是由某一激發事件(A)直接引起,而是經受這一事件的個體對它不正確的認知與評價所產生的錯誤信念(B)直接引起。咨詢師利用三欄技術對患者原來核心信念進行ABC情緒分析,讓患者主動找出自己的不良認知與錯誤信念;咨詢師在過程中不作對錯判定,只是分析、例舉說明、角色扮演[1]、引導啟發等。(4)核心信念矯正:經ABC理論分析后,患者對原來的核心信念產生動搖,嘗試改變自己的核心信念,此過程需要重復評價癥狀、更新目標,必要時檢查并評價身體相關指標,再確定最佳運動與生活方式,實施認知重建(改變認知疲勞嚴重程度、認知疲勞的環境特異性、認知疲勞所致的影響與結果、認知休息與運動解壓對疲勞的緩解作用),做到順其自然;繼而幫助患者建立起積極協助治療的情緒和狀態,協助其緩解情緒并授之以實用性技術(運動疏導壓力,調節環境與期望值)。此過程實施6~8次。(5)行為訓練:根據患者的興趣愛好選擇跑步、球類運動或瑜伽等運動方式;醫生與康復師共同設計運動處方,實施原則為“循序漸進、從小劑量開始、足量運動、堅持不懈”,從小劑量逐步到足量,足量為1次/d,50min/次,目標心率=(220-年齡)×(60%~80%);運動行為訓練以每天布置家庭作業的方式實施,利用互聯網+調動患者的積極性,且課題組成員參與其
中,以監督群內容的積極性、方法的正確性及有效性;聯合家屬利用激勵式干預策略,發揮患者的潛能,將良好行為轉變成習慣行為并持之以恒地堅持下去。(6)重新評價:運用疲勞量表-14(FS-14)、抑郁自評量表(SDS)、焦慮自評量表(SAS)進行評價。認知重建方面頻率:開始治療階段2次/周,2周后改為1次/周,8周后改為1次/2周,會晤時間>2h/次,為期12周。行為方面治療頻次:1次/d,逐漸成為習慣行為。
1.3 評價指標 人口學與臨床資料調查在干預前1~2d進行;FS-14、SDS、SAS在干預12周后測量。(1)人口學與臨床資料調查表:課題組自行設計問卷進行調查,內容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職業等。(2)FS-14:采用英國心理研究專家Trudie、Berelowitz等1992年共同編制的量表來測定疲勞癥狀的嚴重程度。FS-14由14個條目組成,根據受試者實際情況回答“是”或“否”。14個條目從不同角度反映疲勞的輕重程度,經主成分分析將14個條目分為兩類,一類反映軀體疲勞(第1~8個條目),一類反映腦力疲勞(第9~14個條目)。(2)SDS:由20個條目組成,每個條目采用Likert4級評分,將各條目得分相加再乘以1.25取整數,即標準分。53~62分為輕度抑郁,63~72分為中度抑郁,≥73分為重度抑郁。(3)SAS:由20個條目組成,采用Likert 4級評分,包括15個正向評分和5個反向評分,將20個條目得分相加再乘以1.25取整數,即標準分。<50分為正常,50~59分為輕度焦慮,60~69分為中度焦慮,≥70分為重度焦慮。
1.4 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17.0統計軟件。計量資料用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用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

表1 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例(%)]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干預前后FS-14評分比較 干預前兩組患者軀體疲勞、腦力疲勞因子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干預12周后,干預組2個因子均低于干預前(均P<0.05),且干預組均低于對照組(均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干預前后FS-14評分比較
2.2 兩組患者干預前后SDS、SAS評分比較 干預12周后,兩組患者SAS、SDS評分均明顯低于干預前(均P<0.05),且干預組均明顯低于對照組(均P<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干預前后SDS、SAS評分比較
3 討論
CFS是指以持續或反復存在軀體性或精神性疲勞為主訴,伴頭痛、喉痛、畏寒、低熱等癥狀,體格檢查、實驗室檢查均無其他異常發現的一個癥候群[2-3],其主要包括軀體疲勞與精神疲勞。CFS患者普遍存在抑郁、焦慮、睡眠質量差、強迫、軀體化和偏執等負性情緒,疲勞越重則抑郁、軀體化癥狀越明顯[4];對其采用CBT治療有效[5-6]。國外研究報道CBT可使69%的CFS患者恢復健康,效果明顯[7]。CFS患者疲勞總分與軀體癥狀各因子呈正相關,疲勞程度與心理行為問題呈正相關[8]。CBT通過改變患者不良認知而改善抑郁、焦慮情緒,與藥物治療具有相似的治療效果,且能降低復發率[9]。因此,應用CBT治療與護理CFS患者很有必要。本研究結果亦表明CBT療效明顯,即干預組在治療后軀體疲勞、腦力疲勞得分均明顯低于對照組,SAS、SDS評分均明顯優于對照組,考慮原因如下:(1)CFS發病機制尚不清楚,無法采取針對性的治療措施,CBT可針對改變扭曲或適應不良的認知及其相關行為障礙,讓患者正確認識疾病;(2)心理教育是CBT的常規程序,可以從心理認知角度改變CFS患者的態度,調動和組織其應對技能,使患者主動自愿接受系統認知行為干預;(3)CBT由專業治療師指導,能順利改變患者的認知,樹立正確的核心價值觀與信念,大大提高患者的依從性。
CBT包括行為療法的理論與治療方法。有效的認知治療通過改變來訪者的行為模式來最終實現和鞏固療效的。如果某種認知療法的理論很好,來訪者理解并掌握了知識,但是沒有落實到行為模式的改變上,那也不會產生實際且長遠的療效。本研究的行為模式采用運動療法,Karen等[10]提出了慢性疲勞綜合征患者的運動處方,認為有氧運動能有效改善其臨床癥狀[3,11]。研究表明CBT和分級鍛煉療法在減輕疲勞、保持機體功能方面長期有效。2011年一項研究發現CBT和逐步鍛煉療法(GET)能加快CFS患者的康復進展,有氧運動、無氧運動、放松訓練均有可能使疲勞患者獲益[12],其中CBT被認為對CFS有改善作用[13]。然而有學者認為運動可誘發CFS[14-15],故本研究提供的行為模式是運動處方,在循序漸進中改變患者的氣血虛弱問題,避免過勞而影響預后。經過CBT治療與護理后,患者養成良好的運動習慣,既能強身健體,又能提高機體合成IgG,可能增強機體IgG介導的體液免疫應答,提高機體免疫力。
CBT能促進CFS的康復,沒有不良作用,促進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與行為模式對CFS的療效持續持久。但是對患者的人格特征及心理素質有一定的要求,因此本課題選擇的是20~45周歲的白領階層、學生、醫務人員、公務員等,他們接受力、執行力均較強。
[1] 赫爾斯.精神病學教科書[M].5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0:836. [2] Komaroff A L,Fagioli L R,Geiger A M,et al.An examination of the working case definition of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J].Am J Med,1996,100(1):56-64.
[3] Shanks M F,Ho-Yen D O.Aclinical study of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J].Br J Psychiatry,1995,166(6):798-801.
[4] 陳曉琴,駱勇,黃兵,等.慢性疲勞綜合征患者和健康人睡眠主客觀評價對比分析[J].遼寧中醫雜志,2014,41(3):425-427.
[5] 王艷云,劉改芬.心理行為干預對慢性疲勞綜合征患者的康復作用[J].中華行為醫學與腦科學雜志,2012,21(4):343-345.
[6] 劉鯤鵬,房敏,姜淑云,等.推拿對慢性疲勞綜合征患者四肢骨骼肌力學性能的影響研究[J].中國中西醫結合雜志,2012,32(5):599-602. [7] Knoop H,Bleijenberg G,Gielissen M F,et al.Is a full recoverypossible after cognitive hehavioural therapy for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J].Psychother Psyehosom,2007,76:171-176.
[8] 李永杰,高旭光,王得新,等.慢性疲勞綜合肝患者心理學特征的研究[J].中華醫學雜志,2005,85(41):2926-2929.
[9] Cuijpers P,Sijbrandij M,Koole S L,et al.The efficacy of psychotherapy and pharmacotherapy in treating depressive and anxiety disorders:a meta-analysis of direct comparisons[J].World Psychiatry,2013,12(2):137-148.
[10] Karen E W,Alan R M,Carmel G,et al.Exercise prescription for individuals with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J].MJA,2005,183(3): 142-143.
[11] PowllP,BentallR P,Nye F J,et al.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of patient education to encourage graded exercise in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J].BMJ,2001,322(7283):387-390.
[12] McNeely M L,CampbellK L,Rowe B H,et al.Effects of exercise o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survivors: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CMAJ,2006,175:34-41.
[13] Nijhof S L,Bleijenberg G,Uiterwaal C S,et al.Effectiveness of internet-based cognitive behavioural treatment for adolescentswith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FITNET):arandomised controlled taial[J].Lancet,2012,379:1412-1418.
[14] Kennedy G,Norris G,Spence V,et al.Is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associated with platelet activation[J].Blood Coagul Fibrinolysis,2006,17(2):89-92.
[15] Singh A,Garg V,Gupta S,et al.Role of antioxidants in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in mice[J].Indian J Exp Biol,2002,40(11): 1240-1244.
2017-01-04)
(本文編輯:陳丹)
10.12056/j.issn.1006-2785.2017.39.12.2017-35
溫州市科技局科技項目(Y20160586)
325000 溫州市第七人民醫院三病區(金玉蓮、楊曉麗、林崇光),一病區(黃海曉),二病區(楊亞芳),二十三病區(鄭勝麗),防治科(陳亞林);溫州市中醫院神經內科(趙娜)
金玉蓮,E-mail:161433492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