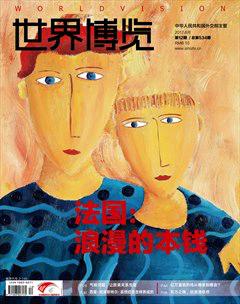散祛萬象浮華
蔣成龍
“作為一個市場參與者,我關心的是市場價值,即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作為一個公民,我關心的是社會價值,即人類和平、思想自由和社會正義。”——喬治·索羅斯
金融巨鱷索羅斯在《開放社會——改革全球資本主義》中如此闡述了自己對于投資市場中道德觀和價值觀的態度,尖銳、現實,聽起來又如此無可厚非。
盡管以此作為本文的開頭似乎有些過于沉重,但筆者本人倒也對此頗有同感。其實就如同這篇文章的題目一樣,在藝術本身的唯美、圣潔、感性之外,我們偶爾也需要從自我陶醉中清醒過來,以某些更加現實的角度,拋開一切迷眼亂花,在本質層面上觀察一下這個市場中到底發生了些什么,即將發生些什么,如此才能幫助我們理解過去出現過的一些現象,以及未來可能需要面對的風險和機遇。
價格與價值的區別
學習經濟學出身的筆者一直堅定地相信,世間任何行業背后的支柱永遠是資本。但是,資本在不同時期和社會形態下會以各種不同的姿態出現在世人面前,起到的作用也多種多樣:它可以雪中送炭,可以錦上添花,亦或是顛覆一些慣例,也能夠成就或毀滅一個行業;它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個人,可能是結構復雜的機構,也或許是一個宗教,甚至國家機器在全球資本市場的博弈也是分分秒秒永不停息的。
相信很多人都聽過這么一句話:“能花錢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對于資本市場來說,似乎這句話更沒什么毛病。然而對于藝術品這一特定市場來說,應該至少先搞清楚“我們到底要解決什么問題”。所以,首先需要明確的就是對于藝術品投資的目的性。
盡管資本總是趨利的,但如果此處的“利”僅局限于經濟利益,便不足以解釋很多偉大藝術品的誕生和傳承。實際上,很多傳世之作的誕生之初可能與經濟價值有關,但結果往往無法用經濟價值來衡量。它們所產生的社會效益,滿足的精神需求,甚至已經超越了空間和時間的定義。如此一來,對于這些藝術品的“投資回報”便無法簡單地以經濟價值進行衡量了。
十五世紀末,當列奧納多·達·芬奇在米蘭的圣瑪利亞感恩教堂道明會修道院繪制《最后的晚餐》時,生活可謂貧困潦倒,經濟狀態極為拮據,甚至在寫給公爵的信中間接指責瓜爾蒂埃洛·巴斯卡皮克扣勞務,使他不得不尋求其它工作謀生。小說家馬泰奧·班代洛當時在這所修道院做見習修道士,他經常會看著達·芬奇在修道院的北墻上工作來打發時間。據他所說,達·芬奇當時的年薪是2000達克特(Ducat,代號DVX,一種一戰前在歐洲普遍使用的貿易貨幣。每一達克特相當于純度為98.6%的黃金3.4909克),而另有消息人士聲稱摩爾人每年只付給他500達克特。按照《最后的晚餐》開始創作的1494年,到作品完成的1498年,如果以2000達克特年薪計算,這幅作品的工料成本最多也就是價值一萬達克特。如果以500達克特年薪計算,作品的總制作成本才不足3000達克特。
十六世紀初,教皇朱理二世取得圣彼得王位后,為紀念其叔父西克斯特四世而請布拉曼特重建西斯庭小教堂,并特意將正在進行陵墓雕塑工程的米開朗基羅·博那羅蒂召至羅馬,涂掉教堂內原有壁畫而重新繪制了舉世聞名的《創世紀》,歷時長達四年零五個月。有關米開朗基羅的收入情況可以從他個人平生的信函中一窺究竟,而這些往來書信如今存世的尚有495封,由埃爾文·史東(Irving Stone)編輯成一本名為《我,米開朗基羅,雕塑者》(I, Michelangelo, Sculptor)的書中。按照書信記載,前面提到的陵墓工程,米開朗基羅將獲得一萬達克特的酬勞,而建造陵墓所需的大理石總共需花費1000達克特。至于創作《創世紀》的酬勞則是3000達克特,而為此落下的工傷和勞損則不在“報銷”范圍內。以投入產出比的角度衡量,難怪為何米開朗基羅當時并不愿接下這筆委托了。
相比之下,喬凡尼·洛倫佐·貝爾尼尼的命運似乎一直與教廷密不可分,日子可謂是跌宕起伏。自羅馬紅衣主教舍皮奧涅·波爾蓋茲對他的賞識開始,他先后創作了《大衛》和《阿波羅與達芙涅》等偉大作品。隨后的十七世紀初,紅衣主教巴爾別里尼成為新教皇,既烏爾班八世。他將年輕的貝爾尼尼請至梵蒂岡并恩寵有加,不斷向他提出訂件,促使這位年輕的藝術家在建筑、雕塑和繪畫和教育等各方面碩果累累。直至英諾森十世登位,貝爾尼尼一度受到了猜疑與冷落,而之前的風光與當下的對比確實讓人難以接受。不過也因此,在為羅馬圣馬利亞·德拉·維多利亞教堂一間科納羅小禮拜堂制作《圣德列薩祭壇》時,貝爾尼尼一改曾經的輕蔑與獻媚態度,進行了更加深刻、冷靜的藝術思考,窮十二年之功完成了這件流芳千古的偉大雕塑作品。
在泱泱中華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類似的故事也不勝枚舉,但論時間跨度、宏偉程度以及對世人的影響之甚,鮮有能夠超越敦煌石窟者。當然,與其將敦煌石窟形容為一件藝術品,不如說是一個藝術、宗教、文化等載體的集群。自前秦時期開鑿,直至宋、元年間,歷經千年,以各自不同的藝術表現手法和特點在700多個石窟中呈現出了雕像3000余身,壁畫45000平方米,可謂驚世駭俗。它所承載的信息之龐大,價值之珍貴,甚至在全球學術范圍內產生了一個單獨的學科——敦煌學(Dunhuangology)。
那么目前為止,前面所提到的藝術品都變成了無法以經濟價值衡量的物品,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不是“商品”,所以不具備一些必須的屬性。
首先,這些藝術品不存在“流通性”,也就是交換、交易的可能。且不說壁畫這種藝術表現形式無法隨意移動搬運,他們的用途本身就不是為了流通而存在的,因此在建造之初就沒有考慮所謂“升值空間”的問題,更沒有易手的目標群體;第二,如果把這些藝術品看做商品的話,他們的“使用價值”決定了他們的特定用途。針對上面的幾個例子,他們最大的價值在于傳承宗教文化和理念,寄托人文思想和精神追求,而不是為了獲取經濟價值而被創造出來。所以盡管他們的使用價值無與倫比,幾百年來也一直如同預期般持續發揮著作用,但其經濟價值卻很難單純地根據其實物價值進行評估;第三,由于其特定的“使用價值”導致了“交換價值”的定向性。或者換句話說,人們走進教堂和石窟,看到了這些震撼心靈的偉大藝術品,其直接回報并非是為藝術品埋單,而是轉換至另外一些回報渠道。他們可能在精神層面受到震撼從而接納了宗教理念,又或許以物質方式直接參與到教會的建設中,形式可能多種多樣,而絕非簡單的買賣關系。
簡而言之,價值和價格具有本質的區別。很多具有學術、藝術、歷史價值的物品并不一定具有直接經濟價值,這取決于他們將要出現的時間、場合和具體用途。然而當我們把“價值”定義拓寬后就發現,其實資本市場的某些原理也同樣適用于這些藝術品。
“如果我們有堅定的長期投資期望,那么短期的價格波動對我們來說就毫無意義,除非它們能夠讓我們有機會以更便宜的價格增加股份。”
股神巴菲特的這句投資名言剛好也適用于我們上面的幾個例子中。如果將時間跨度放大到未來幾百甚至幾千年,將“投資期望”從單純的經濟價值轉為社會價值,那么對于一件藝術品來說,短短幾年或幾十年內的起起落落、跌宕起伏也只能算是驚鴻一瞥,轉瞬即逝而已。無論穹頂壁畫《創世紀》還是雕塑作品《圣德列薩祭壇》,他們的價值在漫長的歲月中都是逐漸增長,從未衰退的。而敦煌石窟中的藝術創作則是在不斷“增加股份”,從整體角度將這幅巨大的藝術創作集群升華到更高的層次,價值當然也是呈幾何數增長的。
那么現在讓我們回到正題,既然說的是資本眼中的藝術和藝術品市場,就要一俗到底,好好談談錢的事情。僅就“經濟價值”論英雄,情況似乎就變得不太一樣了。
作為一種商品,藝術品和石油、黃豆等顯然不是一類東西,他們都具有各自的特點,比如投資周期、回報率、市場影響因素等。然而除了某些特定自然屬性外,他們作為“商品”的屬性又并沒有太大的差別。這其中又有哪些門道和陷阱,適用于哪些市場規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