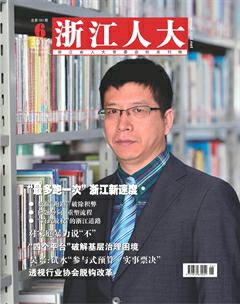“四個平臺”破解基層治理困境
金春華

“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鄉鎮對政權建設和組織建設起著重要作用。為破解縣鄉斷層、條塊分割等基層治理中普遍存在的難題,浙江省創新探索實踐基層治理體系“四個平臺”建設,著力打造中國鄉鎮治理現代化“浙江樣板”。
“四個平臺”是指綜治工作、市場監管、綜合執法、便民服務4個功能性工作平臺。
2016年12月,浙江省在試點的基礎上全面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四個平臺”建設。今年,該項工作納入“最多跑一次”改革整體推進。至5月10日,全省各地“四個平臺”建設進展順利,已有近一半鄉鎮(街道)完成建設,寧波、紹興已相繼實現全覆蓋。因為平臺的出現,縣鄉斷層、條塊分割這些基層治理中存在的全國性難題有了新的破解模式。
困境:尷尬的鄉鎮現狀
鄉鎮,中國行政體系的“最末梢”。
根據省政府網站顯示,2017年初,浙江共有鄉鎮929個,算上街道,鄉級行政區共1378個。它們在基層治理中起著主力軍作用,直接服務近5600萬群眾。
但目前,由于縣鄉沒有很好地統籌起來,產生了諸如縣鄉斷層、條塊分割等一系列難題。
“老百姓對此有兩種很形象的說法:一種說鄉鎮是‘打工型政府,說的是很多縣級部門把工作壓給了鄉鎮,鄉鎮為部門‘打工;另一種說鄉鎮是‘缺胳膊少腿型政府,說的是鄉鎮盡管任務多,但人手少、資源少、職權少。”5月初,全省市縣編辦主任年度培訓班上,與會人員在這一點上的感受竟出奇相似。
一邊是各鄉鎮“我的地盤難作主”的尷尬,一邊是“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的警示。這樣一個全國性難題,如何破解?
給鄉鎮加壓?最大限度發揮鄉鎮工作的效能?
不可行。省編辦和浙大曾合作搞過一個課題,對鄉鎮工作狀態進行摸底。結果是,全省大多數鄉鎮目前的工作已經滿負荷,壓力很大。
給鄉鎮減負?很多工作都由縣級部門及其派駐機構來承擔。
不現實。因為,鄉鎮黨委、政府在基層治理方面的效果比部門好。可以預見,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鄉鎮還是要承擔大量的工作任務。
繼續鄉鎮的“老辦法”——協作配合或者部門與鄉鎮共建?
效果也不甚理想。因為這些措施缺乏長效機制,而且與部門和鄉鎮的“一把手”的個人人脈、個人協調能力密切相關,如果“一把手”協調能力差,“共建”很可能就成了空架子。
如果賦予鄉鎮執法等權力呢?這需要對現行法律和體制作大調整,在省級層面并不現實。即使調整,也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
真的無法作為了嗎?
2015年3月4日,全省行政體制和機構編制工作會議在杭州召開,“四個平臺”概念首次提出。3個月后,省委十三屆七次全會明確提出要提升鄉鎮(街道)統籌協調能力,探索建設鄉鎮(街道)綜治工作、市場監管、綜合執法、便民服務四個功能性工作平臺。
破局:搭建平臺尋良方
平臺,是在沒有“最優解”情況下求得的“更優解”。
基層治理體系“四個平臺”,是一個資源集合平臺。它運用矩陣化管理理念,把鄉鎮(街道)和部門派駐機構承擔的職能相近、職責交叉和協作密切的日常管理服務事務進行歸類,完善機制,整合力量,形成綜治工作、市場監管、綜合執法、便民服務四個功能性工作平臺,并以綜合指揮、屬地管理、全科網格、運行機制為支撐。
鄉鎮工作千頭萬緒,四個功能性工作平臺夠了嗎?
楊汛橋鎮,位于紹興柯橋區西北部,是紹興的經濟重鎮之一,也是全國小城鎮綜合改革試點鎮。去年12月起,柯橋區以楊汛橋為試點,探索基層治理體系“四個平臺”的規范化、標準化和體系化建設。
“我們把鄉鎮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都整合到‘四個平臺的系統中,編制了開展工作的十項機制、六個流程,還把85%的綜合執法力量下沉到基層一線。”柯橋區編辦主任高來興介紹說。
在距離楊汛橋鎮約400公里的慶元縣淤上鄉,“四個平臺”同樣夠用。
淤上鄉是一個農業鄉、山區鄉。這里對綜合執法和便民服務的要求相對更高。鄉黨委副書記吳美英介紹說,去年底,鄉里基本完成“四個平臺”建設的運行工作。現在,鄉、村、網格三級信息形成應急聯動相應機制,機構實現了扁平化、信息化、聯動化。對違法建筑、違法使用土地、市場馬路等違法行為,鄉里基本可做到全鄉范圍內40分鐘趕到現場處置,綜合執法不過夜。
“‘七站八所變成了‘四個平臺,各部門的網格員也變成了一個。所有問題找他一個人就行,方便。”淤上鄉蒲潭村村民林生旺對鄉里的便民服務贊不絕口。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鄉鎮不管大小,和老百姓關系直接、密切的事務主要就在這“四個平臺”。基層治理體系“四個平臺”通過縣鄉之間職責重構、資源重配、體系重整,推動更多的資源向鄉鎮傾斜,使職權、力量等圍著問題轉、貼牢一線干。
要訣:屬地管理來“給力”
可以說,平臺是一種柔性的、功能性的工作機制,讓鄉鎮“借力”作為。
也有人擔心,要是部門不肯“給力”怎么辦?屬地管理成為鄉鎮的尚方寶劍。
建立統籌協調機制、調整人員管理機制、優化網格管理機制、強化定職定責機制,早在開始試點“四個平臺”建設之初,海寧市就制定了四項配套機制,加強屬地管理。
“統籌協調機制要求鎮(街道)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定期會商。人員管理機制中,市級部門派駐機構人員除編制保留在原單位外,工資福利待遇、考核、成長發展等,均由鎮(街道)黨委為主統一管理。為確保隊伍總體保持穩定,下派人員如需調整,事前必須同時向組織、編辦、人力社保部門報批。”海寧市編辦相關負責人介紹說。
鄉鎮“權”變大了,會不會出問題?
5月5日下午,在天臺縣龍溪鄉,黨委副書記許式統正在綜合信息指揮室翻看一天來的辦事記錄。由于基層治理體系“四個平臺”的任務指派都是“網上來網上去”,事件有沒有辦完、辦得怎么樣了、群眾反響如何,點點鼠標都能看到,而且圖文并茂。
“今年到4月底,鄉里有20多個項目開工建設,這也給我們基層治理帶來挑戰。我們要把每一件事做細做實。”許式統說,“四個平臺”的系統,對辦事流程上任何一環的負責人都是一種監督,對鄉鎮更是。
常山縣球川鎮黨委書記胡志彬也愛到指揮室轉轉,他還有另外一層考慮:“基層治理是一種依法治理,我們還是要按照法律規定來辦事。而且,現在各條‘紅線畫得這么清楚,我們更應該嚴守紀律。”
樣本:基層煥發新活力
基層治理體系“四個平臺”建設后,鄉鎮這個“龍頭”真正挺起來了。
今年3月初,安吉縣孝豐鎮有網格員發現,在南溪河畔有一企業修建圍墻超出了水利紅線范圍。這件事情的處理,涉及水利、綜合執法、國土、規劃、城建等多個部門,誰來牽頭?如何處理?信息流轉到鎮綜合信息指揮室,工作人員把它派送到新成立的綜合執法平臺。
“我們馬上連續召開兩個協調會,召集所有相關部門,集中協調,探討解決對策。”鎮綜合執法辦公室主任劉鑫午說,經過協調,企業很快依法整改。
全科網格構成一個信息收集端,觸角無縫覆蓋鄉鎮(街道)整個轄區;綜合信息指揮室進行研判分析和命令指派,成為一個高速運轉的處理器;“四個平臺”集合了多方力量,可以及時有效處理事件,成為一個處理終端。可以說,基層治理體系“四個平臺”重建了基層治理的模式,大大提升了鄉鎮的治理能力。
不僅如此,對派駐機構來說,基層治理體系“四個平臺”提供了全新的理念和視角,推動了工作的開展。
3月中旬,武義縣桐琴鎮綜合信息指揮室接到群眾舉報,鎮上有一家超市存在無煙草專賣零售許可證經營煙草制品零售業務等違法行為。線索在1分鐘后馬上被指派到市場監管平臺;再1分鐘,市場監管平臺就發出前往該超市依法進行執法檢查的指令。檢查發現群眾舉報屬實,當事人章某隨后受到行政處罰。
“相比‘四個平臺所提供的線索量,以前我們靠日常巡邏和部分群眾的舉報獲取的信息是比較少的,且容易存在盲點。”桐琴鎮市場監管所負責人說,鄉鎮和部門的雙重管理,讓信息獲取更加全面,工作人員履職也更加到位。
對群眾來說,以前是“有事不知道找哪個部門”,現在,“有事找政府(平臺)”,獲得感大大提升了。
這一份獲得感,將支撐著基層治理體系“四個平臺”成為中國鄉鎮治理現代化的浙江樣板。 攝影 蔡榮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