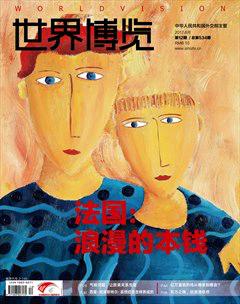鄰居的節(jié)日
杜先菊
每一個(gè)節(jié)日,背后都有它深厚的歷史、文化、宗教和民族的淵源。傳統(tǒng)、文化遺產(chǎn),并不總是“積極上進(jìn)”的,而很多節(jié)日,如國(guó)殤日、端午節(jié),也并不是快樂(lè)溫馨的,因?yàn)樗鼈兌汲休d著歷史,尤其是歷史中那些沉重悲傷的部分。
美國(guó)有“老兵節(jié)”和“國(guó)殤日”,“老兵節(jié)”是所有老兵的節(jié)日,而國(guó)殤日則是紀(jì)念美國(guó)在各次戰(zhàn)爭(zhēng)中的陣亡將士。當(dāng)然,國(guó)殤日有人互道快樂(lè),也不完全是因?yàn)樗麄儭皵?shù)典忘祖”。美國(guó)和平已久,局部戰(zhàn)爭(zhēng)雖然殘酷,真正影響到的人口畢竟有限,于是,在大部分“商女不知亡國(guó)恨”的普通老百姓眼里,“國(guó)殤日”只是意味著一個(gè)長(zhǎng)周末,更重要的是,它還是夏天正式開(kāi)始的標(biāo)志。就連穿衣服,也以這一天為界。美國(guó)人輕易不穿白褲子,要穿,一定要在“國(guó)殤日”(五月的最后一個(gè)星期一)和“勞動(dòng)節(jié)”(九月的第一個(gè)星期一)之間才能穿,否則就會(huì)貽笑大方。這個(gè)傳統(tǒng)開(kāi)始于三十年代。在大部分人都在大蕭條中掙扎的時(shí)候,有錢(qián)人夏天只穿白色,以區(qū)別于汗流浹背、身穿深色實(shí)用耐臟衣物的勞動(dòng)階層,白色也因而成為休閑、生活優(yōu)裕的象征。五十年代以后,戰(zhàn)后美國(guó)繁榮,這種習(xí)慣又蔓延到了中產(chǎn)階級(jí)中,穿白色而不知時(shí)令,一時(shí)成為時(shí)尚禁忌。
好在家庭、學(xué)校都提供了各種渠道,讓人們了解鄰居的節(jié)日,和鄰居的禁忌。小朋友一上幼兒園,隔一陣子就會(huì)帶回來(lái)粗糙的手工作品,就這樣,小朋友很自然地就學(xué)會(huì)了,哪一天是印度人的光明節(jié),中國(guó)人的中秋節(jié),有糖吃的萬(wàn)圣節(jié),大部分人都慶祝的感恩節(jié),還有要放長(zhǎng)假的圣誕節(jié)。學(xué)校里組織唱圣誕歌曲時(shí),還要加上幾首猶太光明節(jié)的歌曲,幾首流行歌曲。于是,在孩子眼里,每個(gè)人都各有不同,而這種“不同”本身,也是再自然不過(guò)了。
我在一家視頻點(diǎn)播公司做過(guò)產(chǎn)品經(jīng)理,負(fù)責(zé)產(chǎn)品支持的工程師是巴基斯坦穆斯林。我雖然學(xué)過(guò)中東歷史,卻不太懂得齋月的具體規(guī)矩,只知道齋月來(lái)了以后,他上班的時(shí)間會(huì)調(diào)整。他也敬業(yè),我一緊張就給他打電話,我一打電話他也會(huì)匆忙趕到辦公室。只有開(kāi)齋節(jié)那一天,他才明確告訴我,這一天他不能來(lái)。后來(lái)我一直慚愧,那整整一個(gè)月,他在白天是不能進(jìn)食的,連水都不能喝,我們匆匆忙忙地調(diào)試產(chǎn)品的時(shí)候,他都是餓著肚子的。
圣誕節(jié)期間,基督徒慶祝宗教節(jié)日,商人們大肆促銷(xiāo),畢竟這一個(gè)節(jié)日就是他們一年百分之二十的收入,而猶太人和其他一些不信基督教的人也形成了一個(gè)新的傳統(tǒng):猶太人都在圣誕節(jié)那天去中餐館吃飯。不去教堂的猶太食客,和不去教堂的中餐館老板,在二十世紀(jì)初期的美國(guó),兩個(gè)非主流的移民群體,就在圣誕節(jié)這一天找到了共同之處,形成了“猶太人的圣誕節(jié)”的傳統(tǒng)。
今天,很多中國(guó)移民來(lái)美前或來(lái)美后選擇皈依基督教,猶太人來(lái)中餐館慶祝“圣誕節(jié)”,也不再有從前那種苦命人和苦命人“同病相憐”的苦況,也就是一種傳統(tǒng)、一種習(xí)慣而已,其中不乏幽默風(fēng)趣之處。
2010年,美國(guó)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艾蕾娜·卡根(Elena Kagan)的聽(tīng)證會(huì)上,來(lái)自共和黨的參議員咄咄逼人地問(wèn)她:圣誕節(jié)爆炸那一天,你到底在哪兒。她正在搜索枯腸地想出一個(gè)滴水不漏的回答,對(duì)方又追問(wèn): “我只是想問(wèn)你,圣誕節(jié)那一天你到底在哪兒?” 她會(huì)心地笑著,停頓了一小會(huì)兒,賣(mài)了個(gè)小關(guān)子之后,才慢悠悠地補(bǔ)上:“像所有猶太人一樣,那一天我可能是在一家中餐館里。”嚴(yán)肅的參議院哄堂大笑,主持聽(tīng)證會(huì)的人說(shuō):“我就知道她會(huì)這么回答!那一天就只有中餐館才開(kāi)門(mén)!”挑戰(zhàn)的參議員口氣也軟下來(lái):“知道了。圣誕節(jié)那一天,你和你的家人正在慶祝圣誕節(jié)。”卡根聽(tīng)證順利通過(gu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