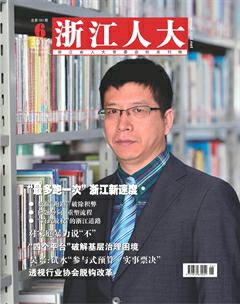破除人大主導立法的迷思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健全有立法權的人大主導立法的體制機制,發揮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中的主導作用。”近年來,各地也都開展了這方面的實踐探索,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導作用也日益凸顯。但在現實中,依然存在立法不如政策、政策不如紅頭文件的巨大尷尬,以及立法中部門利益的博弈,這些都給人大主導立法蒙上了一層迷霧,人大主導立法是否可能、有沒有做到,引起了不少學者和人大工作者的思考。
人大主導立法不是一個偽命題
■現實中,許多地方立法仍然是遵循由政府提供法規初稿、人大或其常委會審議通過這一程序,從而也出現了“人大主導立法是一個偽命題”的說法,針對這種情況,該如何去理解?
□陳維民: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主導立法,或者說在地方立法中發揮主導作用,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明確的事情。無論是在改革開放初期因種種原因,地方立法任務主要由政府承擔,還是現在許多地方仍主要由政府提供法規初稿,有的地方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法規議案走過場等,都不能成為懷疑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主導地方立法這一憲法原則和立法實踐的依據,更不能片面地認為“在中國,如果沒有政府同意人大對地方法規不可能自主決定”。
在我國,從1954 年的第一部憲法直至1982 年的第四部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一直作為重要的憲法原則體現在憲法里。2000 年,為了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我國制定了立法法,從立法權限、立法程序、法律解釋等重要環節對全國以及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主導立法作出了詳盡規定。這就表明,人大主導立法,不僅是憲法原則,而且是維護國家法制統一的憲法責任。
□秦前紅:基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中國憲制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憲法、立法法的文本規定,人大主導立法既是立法的基本原則,也是立法的重要價值追求,這點不容否認。事實上,立法權能是當下中國人大行使得最充分的權能。社會對人大地位的感知往往是通過人大的立法權來實現的。
□李翔宇:在現代國家,特別是成文法國家,法律制定權天然歸屬于民主機構。人大及其常委會作為我國的國家權力機關,由人民選舉產生,受人民監督,具有民主性特點,是我國的民主機關、民意機關。經過人大及其常委會以審議、表決方式通過的文本制度,才具有本區域人民共同意志的性質,才能夠被本區域人民一體遵循,并成為司法判決的依據。因此,人大及其常委會是法定的在立法工作中發揮主導作用的有權機關。
■對人大主導立法產生疑問的原因是什么?
□陳維民:之所以會對人大主導立法產生疑問,關鍵在于對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導地位和主導作用缺乏全面、準確的認識。
□楊云彪:在立法程序中一般很難辨別誰是主導。總的來說,一部法律的完成,有分工的不同。我國憲法、地方組織法和立法法等國家法對法律法規的制定主體和分工都有明確界定。政府動議法案,人大審議通過,這是一個常態化的程序。如果一部法規,由人大自己啟動立法調研,自己動議修訂,最后由人大通過,那么可以說,這是人大主導立法。但是,事實上,我國絕大多數立法都是政府動議、人大審議通過的。即使在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立法一般也是政府啟動、議會審議通過的。在此需要做一個概念上的澄清,所謂立法程序,包括起草、動議、審議、聽證、通過等一系列程序,在此過程中,有很多參與主體。人大不是唯一的參與主體,也不是從頭到尾“主導”的主體。
人大主導立法不能過于理想化
■如何正確理解“人大主導立法”的真正內涵?
□秦前紅:討論人大的立法主導問題,必須堅持規范不等于現實、應然不等于實然、個別不等于全部的立場,必須通過對人大立法的系統觀察、整體分析來回答人大主導立法是否可能、有沒做到?對人大主導立法必須堅持類型化分析,區別政治性立法、社會性立法、經濟性立法的不同樣態,以達致一個客觀、翔實的結論。
人大主導立法是指人大完整地實現立法權能、表達立法意志的能力。它的實質意味著只要滿足民主的正當性,即便有其他法定公權力機關的反對,仍能自行立法。
在當下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下,追求人大主導立法不能過于理想化。立法法之所謂立法主導,其立法原意是指立法議題不能完全按照政府或政府部門的步調亦步亦趨,尤其要摒棄因人立法、因人廢法。間接代表制為主的人大結構,提升人大立法品質才是王道,不能為主導而主導。
□楊云彪:從積極意義上說,所謂人大主導立法,是為了體現人大立法的人民性。但是,立法是一門系統科學,尤其是法案的目的是為了調整一定的社會關系,專業性較強,不深諳其道根本無法提出有針對性的立法。從消極意義上說,政學兩界提出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乃至“人大主導立法”,其中一個重要目的是因為部門利益法制化之弊。需要看到的是,人大在立法中的話語權不足,確實導致部門利益法制化傾向,所以改善和提升人大立法主動權,確實具有價值。
□陳維民:人大對地方立法工作統籌安排、總體設計,統領立法工作全局。在立項、起草、審議、修改等各個環節發揮統籌協調作用,合理配置立法資源,牢牢把握立法方向和立法進程,既充分調動行政司法機關以及社會有關各方的積極性,妥善平衡各方需求,積極回應社會關切,又防止部門利益干擾,樹立立法機關的權威性。
回歸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本意
■針對當下立法程序的現實情況,您認為人大如何才能真正立好用的法、管用的法?
□楊云彪:應該重視立法中的利益訴求和利益平衡,回歸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本意。法治問題,說到底是權力與權利的配置和博弈問題。立法雖然不能直接解決法治問題,但是立法本身是法治現象的觀照,對于塑造法治具有重大的引領作用。部門利益法制化,無非是權力與權利關系的錯配。如果人大立法僅靠人大機關與行政部門討價還價,依然是權力對權力的博弈,不能發揮權利對權力的制衡意義,所立之法依然沒有擺脫權力獨斷的陰影,甚至好心辦壞事也不少見。相反,如果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作用,尊重代表委員立法起草權、動議權、審議辯論權、質詢調查權,讓利益訴求在立法中找到歸屬,讓利益關系在立法中得到平衡,讓公權在立法過程中受到教育,法治才能在立法中得到彰顯,從而回歸科學立法、民主立法的本意。
當然,這個構建有個歷史過程,包括需要逐步推進選舉制度和會議制度的變革。但是,這條路遲早要走,否則,通過人大立法推進法治進步無從談起。
□李翔宇:人大主導立法并不一定意味著在民主的質量上一定有了顯著的提高。只有著力于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運行,改革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運行的具體方式和議事規則,使人大真正成為有效的社會利益的輸入、辯論、整合的政治平臺,使組成人員既具有扎實正當的民意代言人的身份基礎,又能夠通過辯論、發表意見、表決的方式,充分發表政策主張,在立法中發揮決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