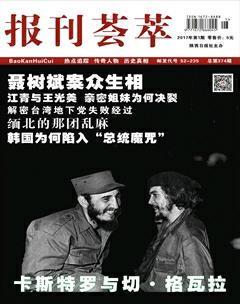1969——1976中國核軍控政策調(diào)整內(nèi)情
詹欣
回顧中國早期核軍控政策,反對超級大國的核壟斷是貫穿其中的核心內(nèi)容。起初,反對的重點是美國,但在1969年中蘇邊界沖突之后,中國在核軍控領(lǐng)域主要是揭露蘇聯(lián)的“假裁軍、真擴軍”,對美國的批評有所減弱。事實上,從70年代初調(diào)整國家安全戰(zhàn)略開始,中國對國際核軍控機制的態(tài)度就悄然發(fā)生了變化,開始從理想主義向現(xiàn)實主義轉(zhuǎn)變,而這種變化正是從中美接觸開始的……
珍寶島事件引起毛澤東警覺
新中國成立之后,美國在朝鮮戰(zhàn)爭和臺海危機期間,曾多次揚言要對中國使用核武器,也曾試圖把中國的核武器計劃扼殺在搖籃里。因此,在20世紀60年代,無論是從國家利益還是國民情感上說,中國都對美國和蘇聯(lián)控制的國際核軍控體制持抵制態(tài)度。這一時期,中國的核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中國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中國發(fā)展核武器,是為了打破核大國的核壟斷;中國鄭重承諾“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即著名的“不首先使用原則”。基于此,當(dāng)時中國的核軍控政策具有兩個特點:其一,中國站在被壓迫民族一邊,強烈反對超級大國的核壟斷,反美色彩要濃于反蘇;其二,中國所強調(diào)的并非單純的核軍控,而是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也就是說,中國早期核軍控政策具有濃重的理想主義色彩。
然而,1969年珍寶島事件后,一切都發(fā)生了變化。
中蘇珍寶島事件并非簡單的軍事沖突,它背后籠罩著強烈的核陰影。過去都是美國對中國進行核威脅,1969年,蘇聯(lián)倚仗核武器對中國進行軍事威脅,這還是頭一遭。毛澤東隨即以他慣用的革命口號提出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jié)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fā)動的侵略戰(zhàn)爭,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zhàn)爭,如果這種戰(zhàn)爭發(fā)生,全世界人民就應(yīng)以革命戰(zhàn)爭消滅侵略戰(zhàn)爭,從現(xiàn)在起就要有所準備。”9月23日和29日,中國分別進行了首次地下核試驗和一次新的氫彈試驗,如此密集的兩次核試驗,也彰顯出中國并不畏懼蘇聯(lián)核威脅的決心。
“聯(lián)美制蘇”
中蘇關(guān)系的惡化為中美接觸提供了良機,但中美關(guān)系的改善卻是緩慢的,甚至是曲折的。由于中美之間長時間的對立,中國在分析中美蘇三者關(guān)系的時候,很難擺脫掉“美蘇既互相勾結(jié),又互相爭奪”這種政治化的分析模式,尤其是對待核軍控問題。因此,中國一直對美蘇限制戰(zhàn)略武器談判極為關(guān)注。10月20日,蘇聯(lián)正式通知美國,同意進行限制戰(zhàn)略武器談判。10月26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把美蘇核會談與中蘇邊界會議聯(lián)系在一起,指出:“中蘇邊界會議一開,蘇聯(lián)即告美國在赫爾辛基于下月17日舉行核會談預(yù)備性討論。于是,雙方都從實力地位出發(fā),向各方施加壓力或顯示威力。”
翌年1月初,周恩來又指出:“美國現(xiàn)在削減常規(guī)武器,減少外國軍事基地,搞大規(guī)模核武器,特別是在赫爾辛基會談之前,大搞擴軍備戰(zhàn),看來都是對付蘇聯(lián)的。”也就是說,在中國領(lǐng)導(dǎo)人眼中,美蘇爭霸仍是主要的,而他們之間勾結(jié)起來反華和單獨發(fā)動對中國的侵略戰(zhàn)爭似乎還不太可能。
根據(jù)國際形勢的這種變化,中國開始謹慎地與美國進行接觸,毛澤東的“聯(lián)美制蘇”戰(zhàn)略構(gòu)想初露端倪。在核軍控問題上,中國開始對自己的政策進行微調(diào),盡管仍堅持核軍控的一貫立場,但在語境上,批判美國起碼要比過去和緩得多,甚至在針對蘇聯(lián)的核裁軍建議上與美國達成了某種程度的默契。
這一默契在1972年達到了頂峰。是年,在尼克松訪華前夕,周恩來談道:“美國搞擴軍備戰(zhàn)既是針對我們的,但更多的是針對蘇聯(lián)的,它把我們看做是潛在的敵人。”
這反映出中國對美國核戰(zhàn)略認知的變化。2月21日,尼克松訪華。關(guān)于核軍控問題,周恩來一方面對蘇聯(lián)的“假裁軍”進行批判,另一方面又堅持了中國的原則和立場。他對尼克松說:“你們兩家(指美蘇)搞軍備競賽,水漲船高……搞核武器花那么多錢,不能吃,不能穿,又不能用,到一定時候還要報廢,下個世紀(人民)會批評為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財力搞核武器。”
尼克松訪華后,中美關(guān)系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毛澤東的“聯(lián)美制蘇”戰(zhàn)略構(gòu)想也進一步得以確立。
7月24日,毛澤東同周恩來、姬鵬飛等談話時說,我們的政策是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利用矛盾,如果要打的話,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能兩面作戰(zhàn)。
1973年2月15日,基辛格訪華。毛澤東在17日晚至18日晨與基辛格的會談中,試圖把“聯(lián)美制蘇”戰(zhàn)略構(gòu)想進一步深化,不僅中美聯(lián)合對抗蘇聯(lián),還要在國際社會建立一個反蘇統(tǒng)一戰(zhàn)線。毛澤東說:過去中美兩國是敵人,但現(xiàn)在我們是朋友。我們應(yīng)當(dāng)“搞一條橫線,就是緯度,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這就是毛澤東著名的“一條線”理論。為進一步統(tǒng)一思想,2月25日,周恩來起草關(guān)于基辛格訪華的外交通報,指出:中美關(guān)系的改善,并不改變中國反對美蘇兩霸的原則立場。今后中國的對外方針“依然是反對兩霸,但要有主有次”,“打擊揭露的重點應(yīng)是蘇修”。
“三個世界”
也正是在1973年,美蘇緩和達到高潮。11月10日,基辛格再次訪華。12日,毛、基會談,主題是“聯(lián)美制蘇”戰(zhàn)略。基辛格一上來就大談蘇聯(lián)對華威脅的嚴重性,并強調(diào)美國絕不允許中國的安全環(huán)境受到破壞。毛澤東則回道,中國的“核力量不比一只蒼蠅大多少”,并不具備威脅,更何況當(dāng)前蘇聯(lián)的“能力與野心相矛盾”,其發(fā)動進攻的可能性應(yīng)該不大。但是在整個會談中,基辛格那種施舍的姿態(tài)令自尊心極強的毛澤東多少有些不快。與此同時,在與周恩來會談時,基辛格不僅強調(diào)蘇聯(lián)進攻的可能性,而且還詳細地提出了與中國建立熱線等具體方案,這讓周恩來多少有些吃驚。本來就對美國踩在中國的肩膀上與蘇聯(lián)搞緩和表示不滿的毛澤東說,有人要借我們一把傘,我們就是不要這把傘,這是一把核保護傘。
考慮到美蘇緩和對中國的沖擊以及中美關(guān)系的冷淡,1974年初,毛澤東開始重新思考中國對外戰(zhàn)略問題,2月22日,他借會見贊比亞總統(tǒng)卡翁達之際,提出了著名的“三個世界”理論,這一次明確地指出了中國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所處的地位,以反對美蘇兩霸為基本目標,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世界身上。
基于“三個世界”理論,中國加強對美蘇核軍控政策的批評。不久,鄧小平出席聯(lián)大第六屆特別會議,在向世界闡述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的同時,也對美蘇核軍控政策進行了批評。他說:“它們兩家都擁有大量的核武器。它們進行激烈的軍備競賽,在國外派駐重兵,到處搞軍事基地,威脅著所有國家的獨立和安全。”
至1974年中期,無論中國還是美國,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內(nèi)政問題上,無暇顧及中美關(guān)系的進展。鄧小平取代身患重病的周恩來成為中美高層對話的中方首席代表,但根基并未牢固;而尼克松由于水門事件辭職,副總統(tǒng)福特繼任,在外交政策上謹小慎微。中美緩和由此陷入停滯。
1975年11月24日,美蘇簽署聯(lián)合聲明,計劃簽訂限制進攻性戰(zhàn)略武器的新協(xié)定。第二天基辛格順道訪華,為福特訪華做準備并向中方通報美蘇峰會的情況。由于中美緩和陷入停滯,中方對基辛格態(tài)度冷淡。對于計劃中的《美蘇限制進攻性戰(zhàn)略武器條約》,中國表示強烈的質(zhì)疑,指出:“這個協(xié)議只規(guī)定了這種武器的數(shù)量限額,而這個限額又超過了它們各自現(xiàn)有的數(shù)量,至于質(zhì)量則沒有任何限制。因此,很清楚,這樣一個協(xié)議,與其說是一個限制戰(zhàn)略武器的協(xié)議,不如說是一個擴充戰(zhàn)略武器的協(xié)議。事實也確實如此。在這個協(xié)議簽訂后,美蘇雙方都在加緊發(fā)展和部署新型的戰(zhàn)略武器,力圖壓倒對方。”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后,中國的外交政策并未立即發(fā)生根本性改變,“三個世界”理論仍然指導(dǎo)著中國的核軍控政策。“三個世界”理論是毛澤東晚年外交思想的精華,其核心仍然是他所熟悉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他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世界廣大發(fā)展中國家身上,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核爭霸。但是,隨著中國對外政策從以革命為中心轉(zhuǎn)移到以國家利益為中心,中國核軍控政策的理論主義色彩開始越來越淡。(摘自《中共黨史研究》2016.8期)B④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