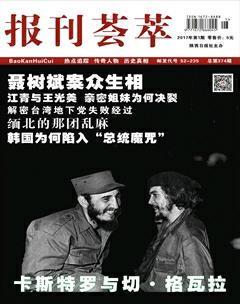吳宓的“夫子自道”
史飛翔
吳宓是我國近現代著名的國學大師、詩人、教授、教育家、紅學家、報刊編輯家、外國文學專家,我國比較文學的先驅者和開拓者。吳宓的一生充滿理想主義、浪漫主義、唯美主義,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吳宓的一生也是失意的一生、凄涼的一生、悲劇的一生。縱觀吳宓一生頗類似于孔子,摩拳擦掌、志向遠大、孜孜以求、誨人不倦,然囿于時代局限加之個人性格因素,終其一生都壯志難酬,“棲棲遑遑如喪家之犬”。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是“雖千萬人吾往矣”,“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雖九死而不悔”。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吳宓的一生,那就是“孔子的現代版”。
吳宓喜歡自我反思。他經常通過寫日記、與人聊天、自我懺悔、甚至是自言自語的形式,以此來進行嚴厲的自我剖析。這里我們不妨摘錄幾段吳宓的部分談話,以此來走近這位國學大師復雜而又矛盾的內心世界。
“我經歷了幾個時代:從晚清王朝、中山先生革命、袁世凱稱帝、國民黨政府、抗日戰爭,直到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我認為從事政治起伏變化大,風險太多;搞教育和文化工作則崇高而平安。”吳宓不愿涉足政治,對政治過問甚少,他天真地以為,遠離政治就能萬事大吉。殊不知,正是因為對政治缺乏基本的了解和遠見卓識,才導致了他悲劇的一生。
吳宓一直被世人視為是“保守主義者”,事實真的是那樣嗎“?我雖然多年研究古典文學,但絕不是‘國粹遺老,古典文學只是我的偏愛;好的新文學和西方文學,我也喜歡。中國古典名著我讀得很多,能談出它們的中心主題。我主張知識沒有國界,知識應當廣博。”“在北京,我和胡先骕、梅光迪辦過《學衡》;還主編過《大公報·文學副刊》;是我邀請的朱自清,兩人合編《大公報·文學副刊》,我搞古典文學,他搞新文學。”“我不迷信中醫,也不迷信西醫。”“我很欣賞歐陽漸的學生王恩洋,追求過他,我欣賞的是他的道德。我主張抑制欲望,養浩然之氣;不作危言激論,持中庸老成態度,服從國家政策法令,與時代和諧相處。”盡管吳宓一再聲稱他不是“國粹遺老”,而且一再表明自己“中西結合、兼容并蓄”的思想文化立場,但遺憾的是,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后,很多人都將他視為是“文化保守主義”的代表人,更有甚者認為他是“文壇怪人”,開歷史倒車,是徹頭徹尾的歷史復古主義者,倒行逆施,因而遭到無情的批判。或許這正是歷史的詭異之處。
生活中的吳宓喜歡直來直去、坦誠相待,甚至不乏天真。他說:“我喜歡早起,早晨空氣清新,腦子清醒,記憶力強。”“我不喜歡玩撲克,我會下圍棋,但很少,不愿花時間在上頭。”“我最看重時間,浪費時間就是浪費生命,哪怕一分鐘的浪費,也會使我精神不安。”“我主張個性不受壓抑。小孩哭泣或受責打,表示小孩不為大人所了解,我深感痛苦。”吳宓對人性也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說:“從性格上說,人可分成陽剛的和陰柔的。陽剛的奔放,陰柔的含蓄,后者不容易為社會所理解,造成寂寞和孤立。”“遭遇不幸的人,往往是好人,正因為他們好,好就軟弱,就不會權變狡詐,就不會應付,就成為犧牲者,這尤其當逢到時代變遷、天災人禍的時候,更容易表現出來。”這與其說是吳宓的理性分析,不如說是他的內心自白,是他的“夫子自道”。
吳宓的高足錢鍾書先生曾這樣評價他這位老師:“吳宓從來就是一位喜歡不惜筆墨、吐盡肝膽的自傳體作家。他不斷地鞭撻自己,當眾洗臟衣服,對讀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顆血淋淋的心。然而,觀眾未必領他的情,大都報以譏笑。所以,他實際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像他這種人,是偉人,也是傻瓜。吳宓先生很勇敢,卻勇敢得不合時宜。他向所謂‘新文化運動宣戰,多么具有堂吉訶德躍馬橫劍沖向風車的味道呀!而命運對他實在太不濟了。最終,他只是一個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錯位的悲劇英雄。在他的內心世界中,兩個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敵手,沖撞著,撕扯著。”沒有比這更到位的評價了。惜哉,吳宓。痛哉,吳宓!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