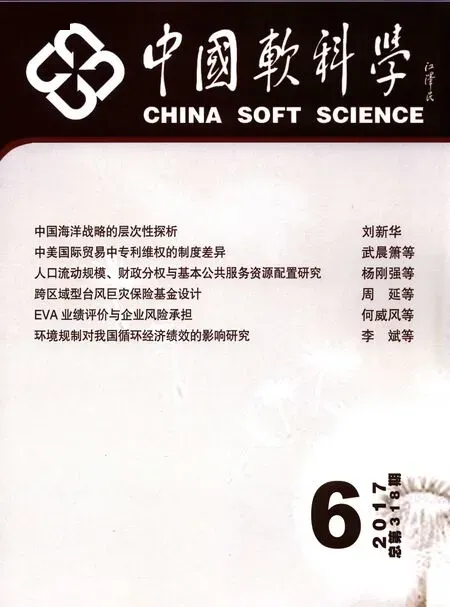企業社會責任、道德認同與員工組織公民行為關系研究
劉鳳軍,李敬強,楊麗丹,3
(1.中國人民大學 商學院,北京 100872; 2.北京物資學院 商學院,北京 101149;3. 中國農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北京 100032)
?
企業社會責任、道德認同與員工組織公民行為關系研究
劉鳳軍1,李敬強2,楊麗丹1,3
(1.中國人民大學 商學院,北京 100872; 2.北京物資學院 商學院,北京 101149;3. 中國農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北京 100032)
采用服務型企業調查數據實證揭示了道德認同在企業承擔與員工相關的社會責任影響組織公民行為機制中的作用。研究表明,企業社會責任是一種獲取組織公民行為的重要員工治理工具,員工內化(表征)道德認同在其關系中具有顯著的調節(中介)作用,研究對深入理解企業社會責任戰略投資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內化道德認同;表征道德認同;組織公民行為
一、引言
理論界與企業界普遍認為,員工是企業最有價值的資產及企業競爭優勢的關鍵來源[1],尤其對服務企業而言。員工與顧客的互動是維持服務質量的重要因素[2],“好”員工行為在“企業—員工—顧客”三維互動良性循環為企業持續創造高利潤過程中起到決定性作用,因而管理者的一個重要但困難的任務就是如何減少員工的不良行為——經濟學文獻稱為“道德風險”,激發員工良好的組織公民行為。長期以來,管理學與經濟學研究文獻開出的藥方是貨幣激勵設計,并指出通過與績效工資直接掛鉤的薪酬設計有助于員工與企業的利益達成一致,從而規避員工的不良行為。然而大量文獻都指出貨幣激勵存在局限性[1],于是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轉向基于關系的激勵機制和激勵因素研究,如通過實施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包括平衡工作和生活投資(兒童看護、彈性時間)、員工健康與安全等改善員工組織公民行為、減少工作場所不良行為,將企業社會責任作為員工治理的重要戰略工具來獲取可持續的競爭優勢[1, 3-5]。
現有文獻關于企業社會責任與組織公民行為關系的結論卻不盡一致,例如Manika等(2015)[6]研究發現企業在環境方面的社會責任行為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中的回收利用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但對能源節約、印刷降低行為無顯著影響;Newman等(2015)實證研究發現員工感知的對社會和非社會利益相關者的企業社會責任顯著正向組織公民行為,但對員工、顧客及政府的社會責任則無顯著影響組織公民行為;而Lin等(2010)[8]則發現企業履行自愿的社會責任顯著地負向影響組織公民行為。可見,目前對于企業社會責任影響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作用機制仍未有清晰的解釋。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是企業社會責任內容的豐富性弱化了其對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因此本研究聚焦在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上,研究其影響組織公民行為的內在機制,這有利于為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與人力資源管理提供策略支持。
另一方面,以往研究顯示任務特征[9]、領導行為[10-11],企業特征[12]及個體特征[13]是組織公民行為的重要影響因素,員工的組織支持、組織公平以及組織道德氛圍感知越高,越會表現出積極的組織公民行為。然而,這些研究只是部分地驗證了與員工相關的支持、公平、關愛等企業社會責任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關系,很少具體討論員工如何對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做出何種反應,尤其是以“德”量才的中國企業文化背景下,不同道德水平的員工會對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做出何種反應并不明確。因此,本文首先聚焦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對已有爭議做出驗證。其次,在建立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和組織公民行為關系模型時,引入員工的道德認同作為中介與調節變量。因為,中國歷來崇德,《薛方山紀述》中有“君子之仕也,其上考德,其次考行,其下考績”。而著名企業家牛根生曾用“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無才,培養使用;有才無德,限制錄用;無德無才,堅決不用”一句話概括蒙牛集團的用人標準,充分說明“德”對員工評價的重要性。因而,從員工的道德認同角度解釋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和組織公民行為關系,可同時為企業社會責任治理以及人力資源管理提供理論支撐。
二、概念界定、文獻述評與假設提出
(一)概念界定
1.企業社會責任和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定義在現有文獻中仍存在很大差異[14],至今還沒有一個明確且統一的概念界定,但逐漸達成共識的是,企業社會責任意味著“合乎倫理地對待利益相關者和社會整體”[3],在本質上都是在探討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和法律主體在社會中的角色和功能、與社會的關系以及對社會的影響這一根本問題[15]。從利益相關者視角看,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自愿對其資源進行合理分配,以改善社會福利進而提升企業與核心利益相關者關系的實踐活動[5, 16-17],是與關鍵利益相關者關系構建的重要投資,已成為企業獲取競爭優勢、提升品牌影響力的戰略工具[18]。人力資源是企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員工是重要的利益相關者之一[19],因而與員工相關的社會責任一直是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重要內容[19],也是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國際標準化組織等國際機構致力于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化的重要內容*例如國際勞工組織早在1977年就通過了《關于多國企業和社會政策三方原則宣言》,并于2000年和2006年進行了修訂,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提出的《聯合國全球契約十項原則》,國際標準化組織2010年出版的《ISO 26000社會責任指南》、社會責任國際(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出版的《SA 8000(2014版)》都將員工責任等內容納入企業社會責任范疇。,通常被認為是企業在經濟價值上對工會的支持及員工需求的認可[17, 20],或從社會責任人力資源管理角度認為在管理決策中對員工訴訟程序、隱私、言論自由、安全等權利的最大限度的考慮[21]。
由于對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理解的不同,實證研究中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的測量必然不可能呈現出一致的分類形式,例如Greenwood和Simmons(2004)[22]根據“社會責任高-低”與“利益相關者涉入有限-寬泛”兩維度將企業承擔員工社會責任分為硬責任、軟責任、道德責任,而Shen和Zhu(2011)則劃分為與勞工法相關的法規遵從責任、員工導向責任及普適的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促進責任。劉遠和周祖城(2015)[3]認為在研究時由于企業社會責任測量的差異性,研究者可以根據研究目的和內容進行選擇,因而本研究選擇Greenwood和Simmons(2004)的分類方式,并采用Mason和Simmons(2011)[23]的概念界定:硬責任是指企業較少考慮員工關注及期望,最大限度地提高短期和組織利益產出,極端的硬責任是僅提供低薪資、有限發展機會、繁重勞動及較差工作環境,并將員工與其它組織資源一樣最大限度地算計其為組織目標的貢獻;軟責任則是在特定的經濟與法律界限內將員工關注與期望納入管理決策,重視員工能力培養,為員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環境及福利補貼,將員工發展作為組織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道德責任是企業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行為,將員工視為所有利益相關者中最獨特的成員,并賦予員工更多的參與權力。
2.組織公民行為
組織公民行為作為員工實施、組織受益的工作角色外行為,從誕生之日起便備受關注。它是一種有利于組織的工作角色外行為和姿態,既非正式角色所強調的,也不是勞動報酬合同所引出的,而是由一系列非正式的合作行為構成的[24]。雖然它與正式的獎勵制度沒有直接或外顯的聯系,但卻是一種能從整體上有效提高組織效能的個體行為[11]。現有研究關于組織公民行為結構維度存在二維、三維、四維、五維、七維等模型[3],但應用較多的是五維和七維模型,如Organ(1990)提出了利他行為、文明禮貌、運動員精神、責任意識和公民美德,Podsakoff等(2000)[25]概括為七維,即助人行為、運動員精神、公民道德、組織忠誠、組織遵從、個人主動性和自我發展。鑒于組織公民行為許多維度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越來越多的學者[3, 11, 26-28]傾向于采用整合方法,將組織公民行為分為指向個體的有利于他人的公民行為和指向企業的公民行為,前者是指直接對特定他人有利,間接對組織有利的公民行為,后者則是維護組織聲譽、保護組織資源等直接有利于組織的公民行為[3, 23, 29]。
3.道德認同
道德認同與性別認同、職業認同等一樣,都是個體自我概念的重要組成,是圍繞一組道德特質(聯想)形成的自我概念(圖式)[30-31],是個人持有的有關其道德特質的心理表征和道德自我的認知圖式[32-34],是人們用于自我建構的重要基礎。與組成自我認同網絡的其它自我圖式相比,道德認同圖式在信息處理上更為長期可接近、更容易被迅速地啟動和激活[33]。由于人們普遍希望保持自我和諧,因而它是道德動機的強大源泉,決定了人們會怎么想,如何感受,怎么做[33]。Aquino和Reed(2002)[30]基于道德自我的“擁有”和“行為”兩個方面,提出道德認同由內化和表征兩個維度,前者指道德特質(如愛心、同情心、公平)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我概念的核心,即個體“擁有”這些道德特質的程度,內化道德認同越高意味著道德認同在自我概念中越處于中心位置,更愿意將自己看作有道德的人來顯示與他人的不同[35];而表征道德認同指個體在現實“行為”(如選擇或行動)中表現的道德特質[30, 32],即高表征化的人會積極參與能將其符合社會規范的道德品質展示給他人的活動,控制其形象以獲得他人良好評價[35]。
(二)文獻述評及假設提出
1.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和組織公民行為
現有研究關于企業履行與員工相關社會責任的行為影響員工組織公民行為機制通常表現為以下途徑:首先基于社會交換理論,認為企業為員工提供較多的資源會使員工期望通過提高組織公民行為來尋求與組織之間平衡互惠的交換關系[36-37],即企業對員工的社會責任能使員工感知到組織關懷,激發工作熱情[19],企業為員工做出的責任行為越多、付出的越多,員工越是主動地產生回報組織的動機,投入的組織公民行為越多[3]。其次,通過組織公平感知及社會認同途徑,員工可以從企業參與的社會責任計劃來獲取管理者及企業是否在個體、團隊及整體水平上公平的線索,并評估企業態度是否與個體身份相匹配,如果匹配,員工就會擁有歸屬感,在未來的行為中將強化該認同[1];當然,通過培養人際關系、提供培訓和晉升機會、鼓勵參與決策等其它特定激勵,企業可以提高員工對當前工作的認知,實證研究表明[1, 3, 7, 17, 39-40],實施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計劃的企業被認為具有公正性和關懷性,更容易吸引高質量的潛在雇員,提升他們的自我概念、自尊,培養員工對組織價值觀和實踐的參與度和承諾,并留住優秀員工。最后,可以通過社會學習的方式促使員工產生積極的組織公民行為,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計劃內容可以作為員工與企業信息溝通平臺,通過密切互動可以將企業的行為規范標準傳遞給員工,減少兩者之間信息的不對稱[1],研究表明當員工意識到企業行為是值得贊許,就會傾向于在后續行為中模仿這些行動,有助于產生積極的組織公民行為。可見,企業積極履行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計劃有助于提高員工更積極的行為,由此提出假設:
H1a: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正向影響指向個體的公民行為;
H1b: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正向影響指向企業的公民行為。
2.道德認同的中介與調節作用
如同組成個體社會自我圖式的其他社會認同一樣,道德認同可以被背景、情境因素或個體差異化變量所激活或抑制[30, 33],道德認同能影響一個人的道德判斷、道德選擇和道德行為[35]。當企業積極實施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計劃時,就是在通過一系列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營造一種負責任的工作環境,特別是企業的道德責任行為能在工作場所營造關愛型的道德氛圍,進而激發員工兩種潛在的組織公民行為動機:親社會價值觀(即幫助他人)和關心組織(即為組織多做貢獻)[42]。換言之,當企業不僅履行和實施法律所要求的硬責任,還積極為員工發展、家庭——工作平衡計劃提供支持、公平對待、尊重和關心員工時,員工的道德認同就越容易被激活,即組織道德環境是影響員工道德行為的關鍵因素[43],當員工認為工作環境是公平且企業堅持其道德政策時,更可能表現出道德行為[12],因而道德認同在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和組織公民行為的關系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但內化道德認同與表征道德認同的作用卻存在差異[44]。
首先,根據社會認知理論,道德認同是將道德認知轉化為道德行為的關鍵心理機制,一般會促進個體親社會行為的產生[45],是激發道德行為的重要動機[30],即外在情境因素可以激活個體的道德認同,進而促使個體表現出符合倫理要求的行為[46]。特別是表征道德認同,它說明人們想通過他們的行動向他人表達其道德特質的欲望[47]。研究發現高表征道德認同能激勵可識別的親社會行為(如組織公民行為),因為可識別的親社會行為提供了向他人展示其道德特質的機會[48],因而企業可以通過與員工相關的社會責任行為自身的榜樣作用,促進員工道德一致性的形成和發展,增強員工道德認同,進而減少員工非倫理行為[49-50]。實證結果也表明,表征道德認同越高的員工,志愿服務行為就越高[48],有助于消除群體區隔,對許多外群體的人也表現出較高的道德關注[51-52]。因而,企業實施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計劃可以激活員工的表征道德認同,并通過表征道德認同積極參與到親社會行為中(組織公民行為),企業在與員工相關的社會責任活動投入的越多,員工就越可能通過表征道德認同實施組織公民行為,于是提出以下假設:
H2a:員工表征道德認同在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和指向個體的公民行為關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H2b:員工表征道德認同在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和指向企業的公民行為關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其次,內化道德認同更能反映其道德價值觀在個人自我建構中的重要性與顯著性,圍繞誠實、關懷、善良等特質的內化道德認同具有道義的本質特征,在有些研究[49, 53-54]中甚至代替道德認同,視為一種相對穩定和持久的人格特質,是有道德在自我認同中核心、重要和本質的程度[55],在企業社會責任對組織公民行為[39]、非倫理行為[56]、規避越軌行為[57]的關系中具有調節作用。實證研究結果顯示,道德認同可以放大員工感知的企業社會責任對其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39],內化道德認同高的員工能更敏銳地意識到與道德相關的問題[30],能避免從事與道德認同相悖的不當行為,自覺選擇做正確的事情,對幫助外群體成員具有更積極的態度、意愿和行為[44, 52]。所以,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對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在不同內化道德認同水平的員工中存在差異,當員工的內化道德認同越高,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對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越大,并且由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激發的表征道德認同越高,于是提出以下假設:
H3a:員工內化道德認同對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和指向個體的公民行為關系具有正向調節效應;
H3b:員工內化道德認同對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和指向企業的公民行為關系具有正向調節效應;
H3c:員工內化道德認同對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和表征道德認同關系具有正向的調節效應。
最后,道德認同是維持道德行為的關鍵因素,一個人要想表現出穩定的道德行為就必須在不同情境下均保持對自身道德標準的高度認同[45]。基于認同的動機理論認為,對于個人而言,某一特殊的認同越處于中心位置,該認同越容易影響其思想、情感及行為[58],內化道德認同水平越高,道德認同在自我概念中的位置越處于中心,個體會更努力地堅持道德自我形象,表現出更強烈的表征道德認同[59],另外,由于情境因素和內化道德認同都會對道德相關認知、情感和行為產生影響,所以,情境因素對道德認同的影響會因內化道德認同的不同而不同[44]。于是提出以下假設:
H4:員工內化道德認同正向影響表征道德認同。
綜上所述,本研究理論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本研究理論模型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樣本及數據收集
本研究選取服務型企業的員工為研究樣本,因為人力資本是服務型企業發展的關鍵[11]。服務型企業更愿意通過實施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計劃來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如海底撈),研究服務型企業與員工相關的社會責任和組織公民行為的關系更具有實踐價值。研究選用可行抽樣方法[60],在預調研時選一家服務型企業發放問卷100份進行量表的修正;正式調研通過國資委朋友關系共向5家服務型企業發放1000份問卷。為避免共同方法偏差的潛在影響,采取多源多次方式調研,第一輪調研由員工填寫感知的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員工的內化道德認同和表征道德認同以及人口統計信息;第二輪調查是在第一輪結束一個月后對參與調查的員工的直接主管進行調查,要求他們評估第一輪參與調查的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為保證員工與其對應主管的數據匹配,對員工和主管調查收集的數據提前進行了編碼;刪除無法匹配的、缺少信息和無效樣本之后,最終有效樣本為466份。
從性別(GEN)上看,樣本中男性占48.7%,女性占51.3%;年齡(AGE)段上看,24歲及以下占6.7%,25—34歲占63%,35—44歲占24.9%,45—54歲占5.1%,55歲及以上占0.3%;從受教育程度(EDU)看,高中、中專及以下占7.8%,大專占13.9%,大學本科占51.7%,碩士及以上占26.6%;從其在企業的位置(COMPO)看,普通員工占54.5%,基層管理者占24.3%,中層管理者占17.6%,高層管理者占3.5%。
(二)變量測量
本研究所有量表均借鑒國內外較為成熟的量表,但為了保證測量指標表達的準確性,做了比對與調整。所有量表均經過3名企業社會責任研究領域內的研究學者和2名英語專業的博士比對,盡可能地使量表與原意一致并符合研究設計需要,量表均采用7級李克特量表。
1.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量表借鑒Mason和Simmons(2011)[23]、何顯富等(2011)[38]中與員工相關的CSR指標,共3個維度,其中硬責任維度采用“我所在的企業僅提供最低的工資標準”等3項反向指標,軟責任采用“我所在的企業將員工視為重要的利益相關方,珍視員工資源”等3項指標,道德責任采用“我所在的企業支持員工參與慈善等公益活動”2項指標。經預調研后該量表未刪減指標,該量表的信度系數為0.859。
2.員工道德認同量表采用研究中廣泛采用的Aquino和Reed(2002)[30]編制的道德認同量表,兩個維度共10項指標。該量表通過向被調查者描述9個道德品質:“有愛心”“友好”“慷慨大方”“樂于助人”“誠實”“勤勉”“和藹”“公正”“富有同情心”,然后要求被調查者回答與之相關的10項描述的同意程度。經預調研后使用的正式量表中,內化道德認同采用“我一直在追求這些道德品質”“這些品質對描述我是什么樣的人很重要”等3項指標,表征道德認同采用“我積極參與具備上述道德品質的活動”“工作之余我做的事情就具備上述道德品質”等3項指標,該量表的信度系數是0.856。
3.組織公民行為采用Lee和Allen(2002)[27]開發的兩維度16項測量指標的量表。經預調研量表修正后,其中指向個體的公民行為采用“該員工總會盡可能地幫助新同事盡快地適應工作環境”等8項指標,指向企業的公民行為采用“該員工總是維護企業的榮譽和形象”等7項指標,該量表的信度系數是0.920。
四、數據分析及假設檢驗
(一)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為減少同源偏差,本研究雖進行了控制,但仍需對使用的變量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本研究采用潛在誤差變量中無測量方法的方法因素效應檢驗,首先構建了包含所有潛在變量的結構方程模型作為基準模型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然后逐步合并相關變量,最終將所有測量指標在共同方法偏差潛在變量上有載荷,通過檢驗模型的擬合指數變化及卡方原則來檢驗,見表1。據此可以發現,五因子基準模型的擬合程度最好,并符合相關指標的參考值,因此說明五個變量之間具有良好的區分效度且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影響。所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信息及相關系數見表2。

表1 測量模型比較
注:模型1合并MII和MIS,模型2合并OCBI和OCBO,模型3合并ERCSR與OCBI、OCBO,模型4合并所有變量,模型5增加共同方法偏差因子。
(二)假設檢驗
1.主效應和中介效應的結構方程分析
本研究采用Lisrel 9.2來進行路徑系數的分析,結果如圖2所示。結構方程模型擬合指數(χ2=894.846,df=245,χ2/df=3.652,CFI=0.905,NNFI=0.893,IFI=0.905,RMSEA=0.077)顯示模型擬合較好,結果顯示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顯著地正向影響指向個體的公民行為(γERCSR→OCBI=0.115,SE=0.049,t=2.331),顯著地正向影響指向企業的公民行為(γERCSR→OCBO=0.184,SE=0.054,t=3.403),說明假設H1a和假設H1b得到了驗證。
而員工的內化道德認同顯著地正向影響表征道德認同(γMII→MIS=0.563,SE=0.060,t=9.305),因而假設H4得到了驗證。同時,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顯著地正向影響表征道德認同(γERCSR→MIS=0.287,SE=0.051,t=5.607),且表征道德認同顯著地影響指向個體的公民行為(γMIS→OCBI=0.434,SE=0.061,t=7.125)和指向企業的公民行為(γMIS→OCBO=0.215,SE=0.059,t=3.653),說明員工表征道德認同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參照溫忠麟等(2004)[61]的方法和標準,采用Lisrel 9.2命令“EF”輸出的間接效應與總效應(表3)檢驗中介作用顯著性。結果顯示,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對指向個體的公民行為和指向企業的公民行為的間接效應估計值對應的t值均大于1.96,說明中介效應顯著,同時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對指向個體的公民行為和指向企業的公民行為的直接作用仍然存在,因而H2a和H2b假設的表征道德認同部分中介作用成立。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及相關系數
注:**P<0.01(雙尾),*P<0.05(雙尾);對角線上的粗斜數字為該變量平均方差提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的平方根。

圖2 主效應及中介效應結構方程模型結果

效應比較變量ERCSR估計值標準誤t值總效應OCBI0.2400.0504.796OCBO0.2460.0534.624間接效應OCBI0.1240.0264.732OCBO0.0620.0193.572
2.調節效應檢驗
按照溫忠麟和吳艷(2010)[62]的方法,首先將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和內化道德認同指標中心化處理,然后進行配對乘積,并將乘積項作為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和內化道德認同交互項的測量指標,然后檢驗交互項與表征道德認同、指向個體的公民行為和指向企業的公民行為的路徑系數及顯著性。分析結果顯示(圖3),加入交互項后結構方程模型擬合指數(χ2=1374.553,df=314,χ2/df=4.378,CFI=0.862,NNFI=0.846,IFI=0.863,RMSEA=0.087)均有所變差,但基本符合擬合要求。同時,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對表征道德認同(γERCSR→MIS=0.241,SE=0.052,t=4.674)、指向個體的公民行為(γERCSR→OCBI=0.100,SE=0.049,t=2.029)和指向企業的公民行為(γERCSR→OCBO=0.148,SE=0.053,t=2.793)的系數均降低,但仍然在P<0.05水平顯著,并且內化道德認同對表征道德認同的影響也降低至0.510(SE=0.061,t=8.390)。更為重要的是,潛變量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和內化道德認同的交互項對表征道德認同的作用是0.152(SE=0.053,t=2.874)、對指向個體的公民行為的作用是0.105(SE=0.051,t=2.040)、對指向企業的公民行為的作用是0.146(SE=0.055,t=2.652)均在P<0.05水平上顯著為正,由此可知內化道德認同對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和表征道德認同、指向個體的公民行為和指向企業的公民行為具有顯著地正向調節作用,所以假設H3a、H3b和H3c得到支持,其調節效果見圖4。

圖3 調節效應結構方程模型分析結果
3.控制變量分析
通過對相關潛變量“化潛為顯”及所有變量中心化處理后,分別以指向個體的公民行為和指向企業的公民行為為因變量進行回歸,結果發現在所有控制變量中,僅有年齡對指向個體的公民行為和指向企業的公民行為的系數0.149(t=3.570)和0.141(t=2.912)在P<0.01水平上顯著,說明員工隨著年齡的增長,在企業內部表現出較多的組織公民行為。鑒于員工道德認同因素在企業社會責任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作用機制中的顯著作用,本研究非常關心什么樣的員工具有更高的道德認同,即“好”員工具有哪些人口統計特征,為此本研究對員工道德認同在人口統計變量上進行獨立樣本的T檢驗,檢驗結果見表4所示。

圖4 員工內化道德認同的調節效應圖

變量名稱①檢驗值性別年齡②受教育程度③企業職位男女低年齡組高年齡組低教育組高教育組職工組管理組內化道德認同均值-0.1320.126-0.0340.092-0.0530.097-0.0470.060標準差1.0470.0610.0931.0441.0060.9841.1070.841t值⑤-2.806**1.2121.5591.187表征道德認同均值-0.1710.162-0.0250.066-0.0050.009-0.1040.135標準差0.9641.0011.0020.9961.0890.8151.1100.820t值-3.638**0.8730.1562.677**道德認同均值-0.1770.168-0.0340.092-0.0340.062-0.0880.114標準差0.0640.9971.0010.9941.0670.8651.1290.791t值-3.771**1.2161.0532.269*
注:①所有道德認同變量均以因子得分做員工評價得分,其中道德認同是以內化道德認同和表征道德認同在更高維度上的因子得分為評價得分;②年齡分組低于35歲為低年齡組,35歲及以上為高年齡組;③教育程度本科及以下為低教育組,本科以上為高教育組;④企業職位以普通職工為普通職工組,基層管理者、中層管理者及高層管理者為管理者組;⑤t值為查看過方差相等檢驗后的值;⑥*表示P<0.05(雙尾),**表示P<0.01(雙尾),樣本量N=466。
結果顯示,女性無論是在內化還是表征道德認同,抑或整體上都比男性表現出高的道德認同傾向,但在年齡和受教育程度上沒有顯著差異;然而在普通員工和管理者分組比較中發現,兩者在內化道德認同盡管無顯著差異,但在表征道德認同上,管理者顯著地高于普通員工,在道德認同整體構念亦表現出同樣的現象。
五、研究結論與未來展望
(一)結論討論與管理啟示
1.企業履行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是服務型企業員工治理的重要戰略投資。分析結果顯示,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不僅能激發員工指向個體的公民行為和指向企業的公民行為,而且可以喚醒員工表征道德認同,產生更積極向上的道德傾向。與傳統的企業社會責任研究關注較為寬泛的社會責任內容不同,本研究基于服務型企業背景,聚焦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內容具有更為現實的價值,員工是服務型企業的核心資源,是企業發展的關鍵資本,如何發揮其核心競爭資源的優勢一直是服務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人員關心的課題,本研究不僅支持了主流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基本觀點,而且再次證明服務型企業進行平衡工作與生活的投資、支持員工社會責任行為等人力資源投資,能積極影響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從而為企業創造更好的績效,就像《海底撈你學不會》一書中描述的那樣,形成競爭對手無法復制的競爭優勢。因此,服務型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者應該在履行好企業基本的硬責任同時,更應該調查研究、設計適合本企業員工需求的軟責任和道德責任計劃。
2.員工道德認同在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對組織公民行為的作用機制中發揮著復雜的作用。企業履行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計劃能否產生積極的員工組織公民行為,員工自身的道德水平具有重要的中介與調節效應。道德認同是員工重要的品質特征之一,對其思想、情感、行為具有重要影響。本研究結果表明,(1)在構成道德認同的兩個重要維度中,員工內化道德認同能顯著地影響員工表征道德認同,即當員工認為在自我概念構成中,諸如助人為樂、慷慨、道德特質越處于中心位置,他/她就更愿意將自己的行為、活動或思想上來顯示與他人的不同。換言之,擁有較高內化道德認同的員工在平時的工作中會表現出越多的表征道德認同的行為。(2)員工表征道德認同行為恰恰是企業與員工相關的社會責任計劃影響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關鍵環節,無論是指向個體的組織公民行為,還是指向企業的組織公民行為,員工表征道德認同都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即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產生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員工表征道德認同行為的多少。(3)內化道德認同在整個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和組織公民行為的作用機制中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當一個員工在道德特質上越覺得高于其它人,企業與員工相關的社會責任在其身上發揮的作用就越積極,從互惠和社會交換的理論視角看,“好”員工確實越容易“將心比心”,企業對自己越好,自己越表現出更積極的組織公民行為。因而,在管理實踐中,服務型企業以德量才是非常必要的,無論是在人力資源管理的招聘環節還是培訓環節,管理者都要努力發現并提高員工的道德認同,從而使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計劃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3.不同性別和不同職位層級的員工之道德認同水平存在顯著差異,而年齡較長員工表現出較多的組織公民行為。研究結果發現,女性員工的道德水平評價顯著地高于男性員工,這與已有研究[63]結論一致。由于本能關懷在女性評價和執行道德行為的過程中更重要性,女性往往表現出比男性更高的道德傾向,因而服務型企業雇傭女性員工似乎是一項不錯的選擇。而相對于基層普通員工,管理者的道德認同評價顯著地較高,這說明在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計劃可能在管理者中間更能發揮其戰略作用,但對于服務型企業而言,基層普通員工是與顧客接觸的最多,所以提高基層普通員工的道德認同水平應該是人力資源管理工作中的一項重要任務。與此同時,企業對新進企業的年輕職工應該給與更多的關注,特別是在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計劃上要針對性設計一些滿足這些員工實際需要的項目,充分激發年輕新進員工的道德認同水平以及更積極的組織公民行為。
(二)研究不足與未來展望
首先,由于本文僅檢驗了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系,盡管這有助于使研究聚焦和更具有針對性,但在反映整個企業的社會責任水平上代表性有所降低,因而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不斷地增加與其它利益相關者相關的社會責任內容,以增加研究的廣泛性。
其次,本研究選取的是員工個體層面的數據進行分析,沒有涉及到企業層面,但對于與員工相關的企業社會責任和組織公民行為可能用服務型企業或部門層面的數據更能全面反映企業的實際情況,并且個體匯報的道德認同有可能存在自我夸大的潛在影響,因而在未來的研究可以使用分層數據并結合企業不同的特征變量來進行驗證。
最后,本研究選取樣本是服務型企業的員工,結論的普適性可能會受到影響,未來的研究可以擴展到更多的行業。
[1]FLAMMER C, LUO 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an employee governance tool: Evidence from a quasi-experiment[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38(2): 163-183.
[2]衛海英,劉紅艷. 服務企業員工互動響應能力的生成路徑研究[J]. 營銷科學學報, 2015, 11(1): 121-132.
[3]劉 遠,周祖城. 員工感知的企業社會責任、情感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的關系:承諾型人力資源實踐的跨層調節作用[J]. 管理評論, 2015, 27(10): 118-127.
[4]劉 剛,李 峰. 企業道德建設對員工滿意度影響機制的實證研究:基于員工感知的企業社會責任中介效應分析[J]. 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 2011(3): 89-97.
[5]顏愛民,李 歌. 企業社會責任對員工行為的跨層分析:外部榮譽感和組織支持感的中介作用[J]. 管理評論, 2016, 28(1): 121-129.
[6]MANIKA D, WELLS V, GREGORY-SMITH D, et al.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attitudinal and organisational variables on workplac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ehaviours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5, 126(4): 663-684.
[7]NEWMAN A, NIELSEN I, MIAO Q. The impact of employee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actices on job performance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private sector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15, 26(9): 1226-1242.
[8]LIN C, LYAU N, TSAI Y, et al. Modeling corporate citizenship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0, 95(3): 357-372.
[9]周紅云. 工作特征、組織公民行為與公務員工作滿意度[J].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 2012(6): 131-136.
[10]DECONINCK J B. Outcomes ofethical leadership among salespeople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5, 68(5): 1086-1093.
[11]劉 朝, 張 歡,王賽君,等. 領導風格、情緒勞動與組織公民行為的關系研究:基于服務型企業的調查數據[J]. 中國軟科學, 2014(3): 119-134.
[12] 張兆國,陳華東,曹丹婷.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治理整合研究[J].科學決策,2016(3):27-37.
[13]張 斌, 譚道倫,李永強. 員工社會網絡對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研究[J]. 中國軟科學, 2011(10): 131-137.
[14]SHIU Y, YANG S. Does engagement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rovide strategic insurance-like effect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38(2): 455-470.
[15]李敬強,劉鳳軍. 企業社會責任特征與消費者響應研究:兼論消費者-企業認同的中介調節效應[J]. 財經論叢, 2017, 215(1): 85-94.
[16]MISHRA S, MODI S B.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hareholder wealth: The role of marketing capability [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16, 80(1): 26-46.
[17]KORSCHUN D, BHATTACHARYA C B, SWAIN S 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ustomer orientation, and the job performance of frontline employee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14, 78(3): 20-37.
[18]劉鳳軍, 李敬強,李 輝. 企業社會責任與品牌影響力關系的實證研究[J]. 中國軟科學, 2012(1): 116-132.
[19]王清剛,徐欣宇. 企業社會責任的價值創造機理及實證檢驗: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和生命周期理論[J]. 中國軟科學, 2016(2): 179-192.
[20]HILLMAN A J, KEIM G D. Shareholder value, stakeholder management, and social issues: What’s the Bottom Line?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22(2): 125-139.
[21]CELMA D, MARTNEZ-GARCIA E, COENDERS 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 analysis of common practices and their determinants in Spain[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4, 21(2): 82-99.
[22]GREENWOOD M R, SIMMONS J A. Stakeholder approach to ethic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 Business & Professional Ethics Journal, 2004, 23(3): 3-23.
[23]MASON C, SIMMONS J. Forward looking or looking unaffordable? Utilising academic perspectives o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asses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its adoption by business[J]. Business Ethics: A European Review, 2011, 20(2): 159-176.
[24]ORGAN D W. Themotivational basis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J].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0, 12(4): 43-72.
[25]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PAINE J B, et al.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iterature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0, 26(3): 513-563.
[26]文 吉,侯平平. 顧客粗暴行為與酒店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研究:基于組織支持感的中介作用[J]. 南開管理評論, 2015, 18(06): 35-45.
[27]LEE K, ALLEN N J.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workplace deviance: The role of affect and cognitions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2, 87(1): 131-142.
[28]WILLIAMS L J, ANDERSON S E.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s predictors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and in-role behavior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3): 601.
[29]宗 文, 李晏墅,陳 濤. 組織支持與組織公民行為的機理研究[J]. 中國工業經濟, 2010(7): 104-114.
[30]AQUINO K, REED I I A. The self-importance of moral identit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2, 83(6): 1423-1440.
[31]MAYER D M, AQUINO K, GREENBAUM R L, et al. Who displays ethical leadership, and why does it matter? An examination of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ethical leadership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55(1): 151-171.
[32]REED A, AQUINO K, LEVY E. Moral identity and judgments of charitable behavior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7, 71(1): 178-193.
[33]AQUINO K, FREEMAN D, REED I A, et al. Testing a social-cognitive model of moral behavior: The interactive influence of situations and moral identity centrality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9, 97(1): 123-141.
[34]吳 波, 李東進,張初兵. 他人的利益重要嗎?道德認同與解釋水平對綠色消費的交互影響[J]. 營銷科學學報, 2015, 11(2): 69-84.
[35]林志揚, 肖 前,周志強. 道德傾向與慈善捐贈行為關系實證研究:基于道德認同的調節作用[J]. 外國經濟與管理, 2014, 36(6): 15-23,31.
[36]CROPANZANO R, ANTHONY E L, DANIELS S R, et al.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 critical review with theoretical remedi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7, 11(1): 479-516.
[37]CROPANZANO R, MITCHELL M S.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5, 31(6): 874-900.
[38]何顯富, 陳 宇,張微微. 企業履行對員工的社會責任影響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實證研究:基于社會交換理論的分析[J]. 社會科學研究, 2011(5): 115-119.
[39]RUPP D E, SHAO R, THORNTON M A, et al. Applicants’ and employees’ reactions to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first-party justice perceptions and moral identity.[J]. Personnel Psychology, 2013, 66(4): 895-933.
[40]SHEN J, JIUHUA ZHU C. Effects of socially responsibl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on employe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11, 22(15): 3020-3035.
[41]EVANS W R, GOODMAN J M, DAVIS W D.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corporate citizenship on organizational cynicism, ocb, and employee deviance [J]. Human Performance, 2011, 24(1): 79-97.
[42]LEUNG A S M. Matchingethical work climate to in-role and extra-role behaviors in a collectivist work setting[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8, 79(1): 43-55.
[43]ARNAUD A. Conceptualizing andmeasuring ethical work climat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ethical climate index[J]. Business & Society, 2010, 49(2): 345-358.
[44]吳 波, 李東進,王財玉. 基于道德認同理論的綠色消費心理機制[J]. 心理科學進展, 2016, 24(12): 1829-1843.
[45]王興超,楊繼平. 道德推脫與大學生親社會行為:道德認同的調節效應[J]. 心理科學, 2013, 36(4): 904-909.
[46]LEAVITT K, ZHU L, AQUINO K. Good without knowing it: Subtle contextual cues can activate moral identity and reshape moral intuition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6, 137(4): 785-800.
[47]WINTERICH K P, MITTAL V, AQUINO K. When does recognition increase charitable behavior? Toward a moral identity-based model [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13, 77(3): 121-134.
[48]WINTERICH K P, MITTAL V, SWARTZ R, et al. When moral identity symbolization motivates prosocial behavior: The role of recognition and moral identity internalization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3, 98(5): 759-770.
[49]王端旭,趙 君. 倫理型領導影響員工非倫理行為的中介機制研究[J]. 現代管理科學, 2013(6): 20-22.
[50]ZHU W, TREVIO L K, ZHENG X. Ethical leaders and their followers: The transmission of moral identity and moral attentiveness [J].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2016, 26(1): 95-115.
[51]WOO J C, WINTERICH K P. Can brands move in from the outside? How moral identity enhances out-group brand attitudes [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13, 77(2): 96-111.
[52]REED II A, AQUINO K F. Moral identity and the expanding circle of moral regard toward out-group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3, 84(6): 1270.
[53]文 鵬,陳 誠. 非倫理行為的“近墨者黑”效應:道德推脫的中介過程與個體特質的作用[J]. 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6, 55(4): 169-176.
[54]許灝穎, 杜晨朵,王 震. 道德領導對員工越軌行為的影響:道德調節焦點和道德認同的作用[J]. 中國人力資源開發, 2014(11): 38-45.
[55]SHAO R D, AQUINO K, FREEMAN D. Beyond moral reasoning: A review of moral identity research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business ethics[J].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2008, 18(4): 513-540.
[56]吳明證, 沈 斌,孫曉玲. 組織承諾和親組織的非倫理行為關系:道德認同的調節作用[J]. 心理科學, 2016, 39(2): 392-398.
[57]石 磊. 道德型領導與員工越軌行為關系的實證研究:一個中介調節作用機制[J]. 預測, 2016, 35(2):
23-28.
[58]MCFERRAN B, AQUINO K, DUFFY M. How personality and moral identity relate to individuals’ ethical ideology [J].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2010, 20(1): 35-56.
[59]MULDER L B, AQUINO K. The role of moral identity in the aftermath of dishonesty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3, 121(2): 219-230.
[60]KEPPEL G, SAUFLEY W H, TOKUNAGA H. Introduction to design and analysis: A student’s handbook[M]. Worth Publishers, 1992.
[61]溫忠麟, 張 雷,侯杰泰,等. 中介效應檢驗程序及其應用[J]. 心理學報, 2004, 36(5): 614-620.
[62]溫忠麟,吳 艷. 潛變量交互效應建模方法演變與簡化[J]. 心理科學進展, 2010, 18(8): 1306-1313.
[63]DONLEAVY G D. Noman’s land: Exploring the space between gilligan and kohlberg[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8, 80(4): 807-822.
(本文責編:海 洋)
Study on Relationships among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Moral Identity and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LIU Feng-jun1, LI Jing-qiang2, YANG Li-dan1,3
(1.SchoolofBusines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2.SchoolofBusiness,BeijingWuziUniversity,Beijing101149,China;3.ChinaNationalAgriculturalDevelopmentGroupCo.,Ltd,Beijing100032,China)
This study uses the data from service business to investigate role of moral identity in the mechanism on how employee-relate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 influence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OCB).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mpanies use CSR as an employee governance tool to increase employees’ OCB, employees’ moral identity internalization (symbolization) has significant moderating (medi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SR and OCB. These findings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implications of strategic CSR investment.
employee-relate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oral identity internalization; moral identity symbolizatio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2017-02-10
2017-06-05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71272153)
劉鳳軍(1963—),男,黑龍江慶安人,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通訊作者:李敬強。
F279
A
1002-9753(2017)06-011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