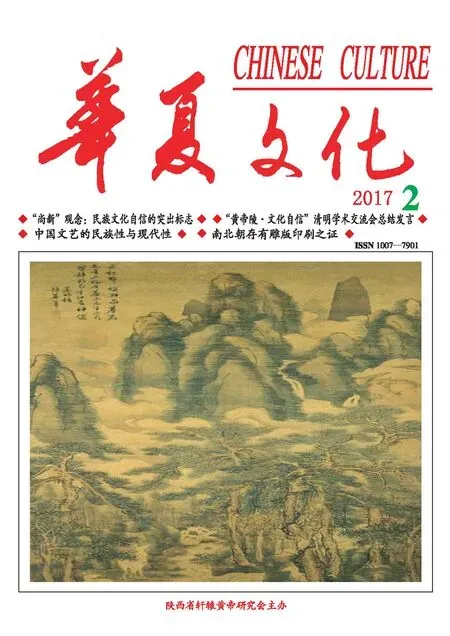唐代官員勸諫帝王游獵的方式
□ 華信輝
唐代官員勸諫帝王游獵的方式
□ 華信輝

唐代是我國歷史上一個較開明的時期,官員積極勸諫帝王,以期輔助帝王成為有道明君,實現自身的政治理想。目前學界對唐代諫書、諫官制度的研究成果較多,但對唐代官員勸諫帝王出游方面的研究多僅為涉及而已,并未專題研究。因此,本文試圖從這一方面試做分析,以期深化對唐代帝王游獵活動的認識。
在儒家道德信仰和忠君思想的熏陶下,唐代官員認為帝王應該堅守“克己慎終、深謀遠慮”的為君之道。因此,帝王的游樂活動在臣工看來恰恰釋放出危險的信號,一般都會被貼上怠政甚至亡國的標簽,認為任其發展勢必會給國家帶來危機。官員希望通過提出有利于社稷穩固的勸諫,提醒帝王以民為本,以道為準,引導帝王朝著為國著想,為民解憂的方向發展。唐代官員對帝王旅游活動進行勸諫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諷諫
即不直指其事,用諷刺的手法,委婉曲折的隱喻,來規勸帝王。這種婉言隱語的方式不會激化君臣矛盾,易于讓帝王接受勸諫。如先天元年(712年)冬天,魏知古曾隨從玄宗畋獵于渭川,面對當時錯綜復雜的政治形勢,因獻詩諷曰 :“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此欲誠難縱,茲游不可常。子云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舊唐書》本傳)針對玄宗的狩獵游樂,魏知古在詩歌中沒有直接進行批評,而是通過歷史典故的渲染鋪陳,把勸諫的內容滲透其中。對夏太康的批判其實正是切中時弊,對現實有諷諫之意,諷刺玄宗縱情于狩獵游樂。對禹、湯明君的頌揚是魏知古理想政治理念的指向,當然歌頌的內容恰恰是現實缺失的,用來引起玄宗的深思,達到諷諫的目的。又如元和初年,憲宗頗出游畋,柳公綽獻《太醫箴》一篇,因事諷諫:“畋游恣樂,流情蕩志,馳騁勞形,咤叱傷氣。惟天之重,從禽為累……人乘氣生,嗜欲以萌,氣離有患,氣凝則成。巧必喪真,智必誘情,去彼煩慮,在此誠明。”(《舊唐書》本傳)柳公綽以探討疾病的形式切入,譏諷憲宗的游樂行為。同時做出診斷,從正面分析造成疾病的原因,是“畋游恣樂”,并指出最好的辦法就是“圣心不惑”,柳公綽用常見的隱喻就將精深的治國之道巧妙的表達出來。再如唐敬宗荒僻日甚,游幸無恒。寶歷元年(825年)李德裕獻《防微箴》“以諷輕出游幸”,其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資治通鑒》卷二四三)李德裕借動亂的現實,言語實質是指責敬宗所追逐的生活;掩藏其中的諷刺意味,則是對敬宗的委婉批評和對現實政治的失望。
二、譎諫
即直接指出問題而委婉、鄭重地規勸。這種方式通過系列生動的意象來達意,以人性化誘導為重心,開啟帝王心扉,促使帝王自我說服。如谷那律隨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太宗因問“油衣若為得不漏?”那律回答道:“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 。”(《舊唐書·儒學傳》)谷那律順著太宗的話題,在違背常理的基礎上,巧妙地按照太宗的邏輯推理,進行不合理的夸張,將油衣、瓦與治國理政建立起映射對應關系,不僅彰顯了谷那律的智慧、耿直,而且營造了一種生動的諧趣效果,將勸諫太宗不要過度游獵的言外之意以旁敲側擊的方式傳達出來。又如貞觀五年(631年)太宗在洛陽苑打獵,遇到野豬襲擊,唐儉下馬搏擊,面對太宗嘲諷:“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唐儉回答道:“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于一獸 ?” (《舊唐書》本傳)唐儉通過對漢高祖的理想化描繪和稱贊,來表達對現實中太宗狩獵行為的委婉批評。字里行間飽含著治理國家的微言大義,提示太宗不要沉溺狩獵這種不智之舉,回歸正確的治國之道。
三、直諫
就是立場堅定、直截了當的規勸。通過徹底、直接指出帝王行為的偏差,把一種理想的政治理念強加到帝王身上,這樣的勸諫方式需要膽量和勇氣。如蘇世長曾隨高祖在高陵校獵,看著滿載而歸的戰利品,高祖興奮地對群臣說:“今日畋,樂乎?”只有蘇世長回答道:“陛下游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為樂!”上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于臣則狂,于陛下甚忠。”(《資治通鑒》卷一八九)當高祖詢問群臣的狩獵心得時,只有蘇世長敢于直言不諱地揭露高祖的過錯。雖然蘇世長機智地按照高祖話語的邏輯來推理,得到與高祖初衷相反的結果,并以幽默的語言說出了自己的反對意見。但是嬉笑中有鞭笞,他的頂撞言辭仍然觸怒高祖。最后他憑借非常誠懇的態度,緩和了君臣關系。又如敢于直言勸諫的魏徵和虛心納諫的太宗,留下了許多勸諫、納諫的佳話。魏徵有一次外出歸來言于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從上可以看出魏徵犯言直諫太宗時,雙方的言語交鋒是多么的激烈,魏徵直言勸諫的咄咄逼人氣勢,迫使太宗作出讓步委曲求全,甚至太宗游樂的想法剛冒出來就因顧忌魏徵而自我打消。再如中宗時期,安樂公主深得中宗和韋后的疼愛,權勢熏天,弄權享樂,生活奢侈。在向中宗索要昆明池未果后,安樂公主強搶民田、民房建造豪華的池館,“大役人徒,別掘一池,號曰‘定昆池’。”(《隋唐嘉話》卷下)安樂公主池館新成,中宗就帶領百官去慶祝,并要求跟隨的官員吟詩作賦營造喜慶氣氛。面對安樂公主的張揚跋扈和為所欲為,以及中宗的縱容和追求安逸游樂,其他大臣都選擇明哲保身,只有李日知清醒地認識到,帝王耽于這樣的狀態無益于王朝的穩定和發展,沒有阿諛奉承,而是冒著嚴重的后果,在不合時宜的場合進行勸諫:“但愿暫思居者逸,無使時稱作者勞 。”睿宗對李日知這次犯顏直諫記憶猶新,以至于在繼位后,發出“當是時,朕亦不敢言之”的感嘆。
四、死諫
即冒死進諫。古有文死諫武死戰的思想提倡,這就意味著不顧自身生死直言進諫,是留給官員的終極職責。唐代還有專職諫官群體,他們有“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的信念。盡管冒死直諫是一種極端的勸諫方式,但體現出官員的高度責任感和使命感,以及他們心系江山社稷、不顧自己生命安危的態度。如敬宗即位以后沉溺于游獵,不務朝政。劉棲楚“以額叩龍墀出血”的誠懇態度和急切的真情苦諫曰:“陛下即位已來,放情嗜寢,樂色忘憂,安臥宮闈,日晏方起……伏以憲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君,恪勤庶政,四方猶有叛亂。陛下運當少主,即位未幾,惡德布聞,臣慮福祚之不長也。”見自己的進言不被采納,又言辭激烈的聲稱“不可臣奏,臣即碎首死 ”(《舊唐書》本傳)。劉棲楚以不遺余力甚至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決心對敬宗進行勸諫,話語中不乏逼迫和赤裸裸的威脅,冒死進諫不給自己留下后路,將自己諫官的職責履行得如此徹底。
五、結語
唐代官員對帝王游獵活動進行勸諫,體現著他們為國為民的苦心良言。在古代君主專制制度下,官員通過進諫使“君王話語的絕對權力得到修正和補充”,因此,唐代官員們通過不同的勸諫方式,不僅起到了糾正帝王行為偏差的作用,而且反映出臣子對帝王的期待,希望帝王自我約束,專心國政。
(作者:重慶市四川外國語大學重慶南方翻譯學院,郵編4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