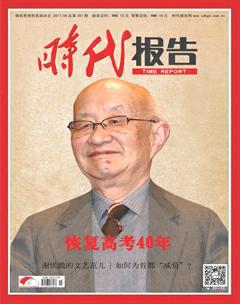殲—20服役,中國完成一個小目標
鄧濤
近日,殲-20加入中國空軍服役成為世界關注的熱點新聞。不少海外媒體認為,殲-20正式服役是中國軍隊現代化的“最新里程碑”。比起媒體的熱鬧,殲-20總設計師楊偉的態度則很從容:“殲-20只是走向‘中國制造2025途中完成的一個小目標,我們不會停止發展新的裝備,這一點毫無疑義。”
殲-20是重型戰斗機,也稱重四,這是為攻勢制空而設計的。重四將是中國空軍的尖刀,可以有效地將爭奪空優的戰線向遠離中國邊境的方向推。另外,作為中國航空科技的里程碑,重四對中國科技的拉動將不限于實物和相關科技,還波及心理作用——中國人也是可以占據世界科技前沿的。不過,雖然“重”比“輕”要強大,但“重”也有“重”的難處。在技術上,“重”意味著相對于“輕”的復雜,而越復雜的東西,麻煩也就越多。
關于產能
由于技術裝備的高度復雜性,現代空戰無疑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個上午損失掉半年的產量”不僅是個段子,更是個殘酷的現實。在技術的追逐中,航空作為高投入產業,在世界上早已成為“貴族”產業。50 年前,美國、蘇聯、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瑞典、荷蘭、意大利、波蘭、捷克都有不同規模的航空產業。但隨著這場“高技術+高投入”的游戲不斷升溫,如今只有美國、俄羅斯還具有完整的航空工業,主要歐洲國家必須聯手合作才能共同維持完整的航空工業,其他國家則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美、俄、歐洲航空工業體系里的配角,只有中國的異軍突起算是一個例外—— “重四”就是中國航空工業的成人禮。這個成人禮當然意義非凡,但相比于百年積淀的美、俄、歐,中國航空工業體系在很多環節上依然是相對羸弱的。以軍用飛機碳纖維材料中的小絲束產品為例,這種材料屬于戰略性物資,是制造第四代戰斗機的必須品,國外對華禁運,日本曾經對賣航空主承力級和航天級碳纖維材料給中國的人員判刑嚴懲,所以我國高層相當重視,現在是戰略重點。中航工業對國產碳纖維產品進行支持,規定成員單位必須使用已達標的國產碳纖維產品。但既便如此,四代機所用的高端碳纖維材料也尚未達到產業化的程度。如T800級別的高端碳纖維材料,江蘇航科5個月的產量只有500千克,即每個月100千克的規模,可以說仍然在試生產階段。
事實上,國內十數家碳纖維生產廠家,群雄并起,看似熱鬧,實際上有很大一部分并沒有掌握核心技術。要么是關鍵設備、關鍵材料需要進口,要么是工藝參數和質量控制沒有吃透。簡而言之,中國碳纖維行業生產長期徘徊在“能做出來,就是做不好;能做好,就是貴”的尷尬局面中,而高性能碳纖維材料的生產又只是整個航空產業鏈條中諸多薄弱環節中的一個,也可以說是一個縮影,由此導致的問題之一便是制約了四代機的產能——這不是多建幾條總裝配線就能解決的事情。由于技術的高度復雜性與工藝的高度精密性交織在一起,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樣,一年能生產10萬架各型號軍用飛機的時代早已遠去了,今天重型四代機的生產在成為一個巨大挑戰的同時,也成為老牌航空強國與新興航空大國之間進行角力的一個隱形戰場。但在和平時期,決定戰斗機年生產能力又與需求量有關,很難反映出真實的情況。鄰近的日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受制于可憐的訂單數量,日本在2000年后開始生產的F-2戰斗機其年產量只有個位數,因為其總需求量只有不到95架,但該國工業技術能力水平卻是眾所周知的,這意味著日本的戰斗機生產能力顯然不止如此。由此及彼,雖然由于信息公開的原因,我們無法了解“重四”的實際產能情況,但在2016年美國F-35的總裝線卻已經達到了每天一架的速率,這是一個十分驚人的能力,但這仍然不足以反映出戰時美國戰斗機生產的真實能力。
關于可維護性與可部署性
殲-20是第一種中國可以正視世界而宣稱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戰斗機,這不需要文字游戲,美國國內不乏重開F-22生產線的呼聲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F-22是因為成本過高和能力過度而在羅伯特·蓋茨任國防部長期間被下令提前停產的,在反恐和軍費開支高峰時被看作不必要的奢侈,時任空軍參謀長麥克·莫斯利上將和空軍部長麥克·韋恩還因為反對削減F-22數量在“政治不正確”而被革職,B-52違規帶核彈飛行只是借口。但“低成本”的F-35有違重望,成本居高不下,性能卻令人不放心,尤其是空戰性能。美國空軍對蘇霍伊T-50還不太擔心,但殲-20的出現使得F-22的能力突然之間不再過度了。這使美國空軍內部對F-22早早停產不免口誅筆伐,同時也是對殲-20能力的一種肯定。但世界先進水平并不意味著就是完美無缺的。殲-20這樣的重型四代機是昂貴的先進裝備,在性能達成突破的同時,技術上更是異常復雜,這不可避免地要帶來很多問題。比如,由機體吸波材料引起的可維護性問題就是一個可以預見的大麻煩。
重型四代機的低可探測性不能完全依賴于氣動外形設計的針對性,相關的吸波涂料技術是非常關鍵的一個環節。理想的吸波材料,要能滿足以下幾個要求。首先,除了反射截面積要小,吸收率要高以外,能吸收的電磁波頻帶還要寬。其次,它的工作角度要大,能吸收各個方向上照射過來的電磁波。最后一點則是涂料必須要有很好的耐受力,能耐雨水紫外線,能耐受高溫,尤其是能耐受高速飛行時的空氣沖刷。然而,即便是以美國的飛機低可探測性技術水平,也很難同時兼顧這些方面。單一材質的涂料無法達標,就必須采用多層復合設計。這不但意味著工藝成本的提升,維護難度的增加同樣是必然的。由于設計年代較早,F-22的吸波材料仍然是涂料形式。對于非常強調超聲速巡航的重型四代機而言,氣流的沖刷效應對涂料的破損剝離特別歷害——最近布署在中東參加實戰的F-22機群便因此飽受折磨。事實上,美國空軍每次部署F-22,都要動員大量的后勤和技術人員,攜帶繁復的維護設備和工具,甚至包括臨時涂抹隱身涂料的涂料。需要幾十個小時的維護才能進行1小時的飛行。這種令人頭疼的維護狀況甚至直接影響到了F-22的戰術使用方式和部署規模。由于F-22要想在設備完善、后勤和技術保障充分的大機場不顯行蹤成了一件令美軍高層非常頭疼的事情——變大機群布署為小機群布署的“快速猛禽”戰術由此出臺。
所謂的“快速猛禽”簡單的說就是一到兩架,最高三到四架F-22由一架KC-135加油機和一架C-17空中霸王伴隨,從美國本土經過9次空中加油悄悄抵達歐洲或者亞洲的第一島鏈,然后對俄羅斯和中國進行威懾。這個“快速猛禽”戰術的主要特點是保持出擊的突然性,第二是克服備用機場的后勤保障困難,在對手認為不可能降落的機場降落,以增強機動的隱蔽性和欺騙性。第三就是不斷變換機場的可操作性。2016年4月11日,美國空軍第95遠征戰斗機中隊的4架F-22從佛羅里達州廷德爾空軍基地啟程,在空中經過9次空中加油,飛行9個半小時抵達英國皇家空軍肯西斯基地。這是F-22首次部署歐洲,接著就是按照“快速猛禽”的劇本上演的“流竄部署”,一會兒部署到黑海邊上的羅馬尼亞,一會兒部署到波羅的海的立陶宛,每次部署不超過三個小時,作戰兩小時,每次部署最少要一次空中加油,隨后是C-17滿載F-22需要的各種設備和油料以及零配件降落在F-22剛剛落下的機場,進行保障和維修、補給——“快速猛禽”戰術或許是很聰明的一種變通,但誰又能說這不是一種無奈呢?雖然在F-35上,吸波材料被換成了類似于塑料薄膜的形式,可維護性將在理論上比原來有大幅度的進度,但這種理論上的優越性是否能實實在在地轉化為實戰收益卻不可預測。吸波涂料的耐受性問題只是四代機在部署和使用中所遭遇的一系列可維性問題中的一個。這些問題必須依靠大量的戰場條件部署來暴露、驗證及改進,在保障條件良好的基地中能作的非常有限。而F-22與F-35碰到的一系列可維護性問題,殲-20同樣無法繞過,要有一個大量試錯的磨合過程,這其實是很考驗耐心的一個事情,更意味著多年來形成的機務維護體系和習慣方法或許會被全盤推翻。
從小目標看出大戰略
重型四代機在西方也是頂級技術,擁有殲-20意味著中國空軍第一次在主戰裝備的技術層面上與對手形成了對等。這些技術即便在西方航空工業,也是頂級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國主戰裝備的技術水平長期處于第二甚至是第三梯隊,可供借簽的東西很多,大量現成的經驗就放在那里,相應的思維習慣早已養成。但現在一下子站在第一梯隊的位置上,可供借簽的東西變少了,目標成了尚未成熟的東西,信息不全加上對方自己也在摸索,東西拿到手后下一步怎么走就成了一個問題,這反倒容易在思維上迷失了方向。簡而言之,重型四代機的研發、制造當然充滿挑戰,但形成有效使用這種昂貴復雜裝備的思維何嘗不是?差別在于前者的成就容易看見,容易認可,而后者相對來說“看不見摸不著”,很容易成為隱憂,這其實是很致命的。
大量的軟性因素與西方仍有一定差距,這是必須承認的現實。畢竟老牌航空國家擁有的優勢是一種整體上的優勢,其扎實是深入骨髓的,體現在各個方面各個層次,是百年積淀的結果。當然,承認現實不代表低頭認輸。這不是對中國航空的譴責,而是在肯定進步的同時,認識差距。中國起步晚,基礎弱,追趕是需要一個過程的。雖然領跑者的數量和差距都在縮小,但學習和追趕,仍將是我們這個民族今后很長一段時間的常態。只有懷著這樣的心態來看問題,我們才有可能真正走在前沿,實現超越。
據悉,作為首款被西方承認的“中國研發的最先進戰斗機”,中國眼下并不打算拿殲-20到國際市場上出售。通過殲-20這個小目標,不難看出中國的大戰略:從容應對他國威脅、維護國家安全,更有力地促進地區和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