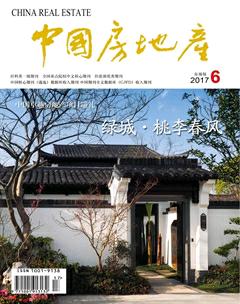這波樓市調控中不能忽視的兩個信號
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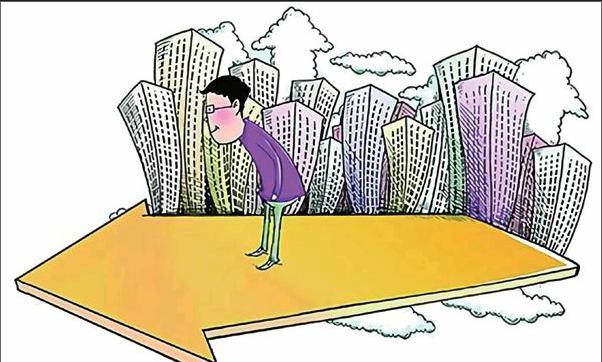
此輪樓市調控收緊兩月有余,熱點城市新房價格漲幅全部回落,市場成交量也明顯萎縮。調控的威力已經顯現,但我們對調控的認識不宜停留在此,至少還有兩大信號值得我們重視。
第一大信號是調控手段中的殺手锏——“限售”正潛流暗行。此輪調控緊縮的看點主要是限購升級、限貸加碼、限價“窗口指導”,并配合“限離”等各類“打補丁”手段,全面封堵投資炒房的政策空子。整體上,這些手段的核心是著眼于需求調控——限購。而在調控的另一端,悄然興起的又被忽視的是殺手锏是——“限售”。
最先引發對限售的關注是保定推出了“雙限雙競”、10年內不能買賣房屋的土地出讓條件。“限房價競地價,限低價競房價”,競得土地的競買人需告知購房人,在取得不動產權證之日起10年內不得買賣。這種限價房并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商品房,而是政府為調控房價,解決收入困難人群住房問題推出的臨時性措施;也不是此輪調控的首創,早在2007年就已誕生,且附加了滿五年或七年方能出售的附加條件,部分城市還規定出售時需繳納一定比例的差價作為土地收益給政府。此次保定大幅提高了限售的時間跨度,再加上此前已有不少城市采取限售政策,故引發輿論關注。
有機構統計,已有超過30個城市實施“限售”,但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不多。比如,北京的商品房限售主要針對企業,即企業購買商品住房需滿3年才能上市交易;廣州除了對企業限售,也對居民家庭購房限售,即需取得產權證后滿兩年才能交易。成都、廈門、南京、長沙等二線城市也有“需取得產權證后滿兩年方可上市交易”等類似限售要求。一般而言,購房人獲得新房的產權證大概是買房后的兩年之后,所以新房上市再交易的時間至少需要四年。
交易時間的拉長增加了炒房人的資金成本和收益獲取的不確定性風險,有助于遏制樓市的投機炒作。“限售”的城市范圍可能繼續擴圍,與“限購”一起構成樓市調控的兩把利刃,抑制市場泡沫。但在推進建立房地產調控長效機制的當下,筆者認為,限購、限售等措施宜進一步規范化、法制化,建立穩定的市場預期。
第二個信號則是利率上升。利率是對資產價格影響最直接和最敏感的因子,利率上行將加劇資產價格泡沫破滅的風險。就房地產市場本身而言,居民住房按揭貸款的利率上行已頗為明顯,北京二套房利率升至基準利率的1.2倍,且還有繼續上調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就整個貨幣金融環境而言,利率上行的信號也頗為明顯。
金融領域去杠桿的號角已經吹響,金融部委的各類防風險措施已密集出臺,信用環境趨緊的態勢也已顯現,這是利率上行的主要原因。從信用債利率來看,個別AA級信用債發行利率突破7%;從十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突破3.7%,市場對無風險利率上行的預期較為強烈。同時,金融監管趨嚴,打擊各類違規套利行為,引導資金脫虛向實,也將推動銀行惜貸,資金價格上浮。
從外部影響因素來看,美國今年可能再次加息1-2次,最近一次加息可能在6月,這將對國內貨幣政策造成直接影響。實際上,年初央行已經兩次上調貨幣市場操作利率,這既有抑制國內資產價格泡沫的意圖,更有對沖美聯儲加息造成匯率和資本外流壓力的考慮。下半年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在實際操作中料維持偏緊態勢,依然是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及MLF、SLF等形式來提供合理的流動性,或呈現出緊貨幣、緊信用的狀態。
在資金價格整體上行的態勢下,房地產企業面臨的則是各類融資渠道的收緊——自籌資金大幅下降,發債融資通道變窄,各類資管計劃入房被限……
Wind資訊統計顯示,按照信用債申萬房地產行業劃分,今年1月1日至5月21日,企業債發行只數為10只,發行額為98.7億元;公司債發行34只,發行額為296.8億元。而去年同期,企業債共發行52只,發行額643.8億元;公司債共發行294只,發行額3901.53億元。
海外發債方面,今年以來房地產企業海外發債規模116.95億美元,發行債券數量31只,均創同期歷史新高。其中,一季度房地產企業海外發債規模99.5億美元,是去年同期的近四倍;但二季度以來,房地產企業海外發債規模為17.45億美元,為2013年以來同期次低。
銀行信貸方面,截至一季度末,金融機構人民幣房地產貸款余額為28.4萬億,同比增長26.1%。而房地產貸款中,地產開發貸余額同比下滑21.5%,自2016年四季度后連續兩個月負增長。
另外,如果地產銷量持續低迷,隨著債務到期量增加,未來企業流動性將面臨較大挑戰。地產行業存量債務到期壓力或集中在2018-2021年,國內地產存續債券中約有75%是在2019-2021年間到期。貸款的期限以3年為主,過去兩年產生的大量貸款也將在2018-2019年到期,故年內債務到期壓力不大,但未來2-5年地產行業債務到期壓力集中。
這將極大地考驗開發商的資金管理和融資能力。缺乏融資渠道的中小開發商宜加快周轉,現金為王;融資通暢的開發商也不要盲目自信,激進擴張。
以往調控歷史似乎告訴開發商們一個事實,每一次調控都是一次做大的機會,只看你是否會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