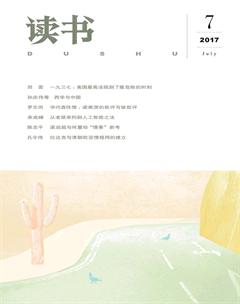中國農(nóng)村應(yīng)有怎樣的未來
郝志東
近年來讀過不少回鄉(xiāng)見聞,多數(shù)作者都不看好農(nóng)村的未來:空心化、老年化、百業(yè)凋敝、垃圾圍村、衰落、即將消失等等描述不一而足。那么農(nóng)村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境況,到底有沒有未來,如果有的話,是一個怎樣的未來?的確,在城鎮(zhèn)化的大潮下,很多村里的年輕人都去了城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但是有的農(nóng)村也正在發(fā)展鄉(xiāng)村經(jīng)濟,或建設(shè)旅游景點,另外一些農(nóng)村則在兩者之間徘徊,不知何去何從。呂延濤的《老鄉(xiāng):對中國西北一個移民村莊的一線調(diào)查》(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二0一六年版)所描述的似乎是后一種情況。
本書作者居住了二十八天的村莊叫顧山村,有八十一戶人家,回族,長相從身高、皮膚、頭發(fā)、眼睛、鼻梁等方面看,和漢族有所不同,他們的祖先來自中亞,有的在吉爾吉斯斯坦還有親戚。從書里諸多的照片上看,無論男女大都長得很標(biāo)致。但是他們的村子比較偏僻,二年級以上的小學(xué)生每天要翻溝越嶺到六七里以外的馬洼村小學(xué)上學(xué),來回走兩小時。有的地方坡陡路窄,下雨便無法走,需要繞行十幾里。如果下雪,孩子們來回要走三四個小時。村里傳統(tǒng)的土窯洞一遇大雨,便有塌方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縣里根據(jù)寧夏回族自治區(qū)的計劃,要求大家兩三年內(nèi)搬遷到離顧山村七八里外的移民點。
這顯然是城鎮(zhèn)化的思路,似無可厚非。但是,正如村民們所說,到那里去之后人們怎么生活?“面子”有了,“里子”有沒有呢?拿新的移民點新集鄉(xiāng)的團結(jié)村來說,二0一0年有十戶顧山村民遷來,但是其中五戶又陸續(xù)遷回了顧山。移民點沒有通地下管道,用旱廁所,污水排不出去。政府為每戶人家改了牛棚,但是要走十幾分鐘,看管難(有人曾養(yǎng)過三頭牛,不久就被偷了一頭),且牛飼料也沒有來源。所以幾百個牛棚建好,卻基本沒有人在里面養(yǎng)牛。正如一位村民對作者說的:“好我的老哥呢,我也想到城里去生活,可是到了城里,在啥地方弄錢呢?老婆娃娃跟著喝西北風(fēng)呀!”
那么顧山村民能不能不移民到這樣的城鎮(zhèn),而將精力放在建設(shè)美麗鄉(xiāng)村上面?顧山難道真的是窮鄉(xiāng)僻壤、自然條件惡劣到不能生存的地步了嗎?完全不是。顧山的張建福自辦養(yǎng)雞場,養(yǎng)了九千只雞,是彭陽縣最大的養(yǎng)雞專業(yè)戶。張萬仲養(yǎng)了七十多只羊,還擁有一輛夏利轎車,一輛四輪拖拉機,一輛蹦蹦車,還有割草機等各種配套農(nóng)機具。村里好多人家都養(yǎng)羊養(yǎng)牛,種玉米、苜蓿等以解決飼料問題,幾乎家家都有摩托車、三輪車等等交通以及農(nóng)用機具。自古以來,該地區(qū)就以畜牧業(yè)見長。那么讓更多的人在村里好好發(fā)展畜牧業(yè),建設(shè)既有“現(xiàn)代文明”又具“田園風(fēng)光”的美麗鄉(xiāng)村,不是也可以嗎?是哪些因素在阻撓“鄉(xiāng)村城市化”“城鄉(xiāng)一體化”的可能呢?
從作者書中的報道來看,顧山村經(jīng)濟發(fā)展的瓶頸是貸款問題。很多人都因為貸不到款而不能擴大養(yǎng)殖業(yè),導(dǎo)致生活過得比較緊巴。其實政府已經(jīng)提供多項貸款,比如農(nóng)村婦女創(chuàng)業(yè)貸款、“雙帶”資金(一個黨員帶兩戶農(nóng)民,有資金協(xié)助)、農(nóng)村信用社貸款、郵政銀行貸款、農(nóng)業(yè)銀行的職工擔(dān)保貸款。但是由于僧多粥少,貸款分不到幾戶就沒有了;另外大多數(shù)農(nóng)戶并沒有公務(wù)員或教師等親戚可以擔(dān)保。再加上各種各樣的限制,農(nóng)民得到的貸款遠(yuǎn)遠(yuǎn)不足以滿足他們發(fā)展的需要。
有些時候則是貸款的組織與管理不到位。比如張鵬想利用郵政銀行的“三戶聯(lián)保”貸款,但是“知道這個信息時已經(jīng)太晚了,又一直找不到愿意互保的鄰居,結(jié)果沒有貸成”。姬秀蓮一家找來保人之后,上面又說“要由村上來找保人”,拖來拖去,沒了下文。這些情況,黨支部和村委會有沒有出面協(xié)調(diào)呢?張世旦因為不知道銀行規(guī)矩改變沒有按季清還利息,“糊里糊涂地被銀行列入了黑名單”,再也沒有辦法貸到款。銀行為什么沒有將規(guī)則的改變通知給每一個客戶呢?如果不能擴大生產(chǎn),每年的收入只能維持生活,那么又如何還貸呢?本金和利息(5%到10%,顧山村民通常可以拿到5%的利息)加在一起,欠賬不是越來越多、窮者更窮、永無出頭之日嗎?張桂芳一家也因為沒有及時還清貸款而被列入黑名單,五年內(nèi)不能再貸款。類似的情況還有張平,多年前貸了一萬元,未能及時償還本息而被列入黑名單。養(yǎng)殖大戶張萬仲貸到了“三戶聯(lián)保”款,張建福貸到了公務(wù)員擔(dān)保款,但是兩人都感到還是不能滿足擴大生產(chǎn)的需要。這些情況,鄉(xiāng)里、村里有沒有幫助解決呢?或許是他們也沒有辦法?
農(nóng)業(yè)部長韓長賦在解讀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時,說要解決“農(nóng)業(yè)貸款難、融資貴、保險少的問題”。比如無論是土地經(jīng)營權(quán),還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設(shè)施和大型農(nóng)機具都可以抵押。無論是否貧困縣,都有一個資金整合與管理的問題。關(guān)鍵是什么措施,是否有效。至少我們在《老鄉(xiāng)》一書中看到的措施并不少,但是效果卻不理想。《老鄉(xiāng)》一書也提到:“最近上面推出了許多鼓勵放開民營金融結(jié)構(gòu)的政策,這讓顧山村民似乎看到了貸款的希望。村里的干部也感覺可以松口氣了……不用擔(dān)心為貸款的事情被村民罵了。但是,在實際操作中,解決貸款問題仍然存在不少障礙。”本人建議,可以考慮貧困農(nóng)民的實際情況,結(jié)合國際上的做法,對貧困地區(qū)農(nóng)民的貸款和債務(wù)不要利息(無息貸款)。這樣做,或許可以大大緩解農(nóng)民貸款的壓力,從而使農(nóng)民較快過上好日子。
農(nóng)村的問題,還有一個比較嚴(yán)重的面向是農(nóng)民工問題,這在《老鄉(xiāng)》一書中也有很詳細(xì)的描述。在這三十多年的發(fā)展中,似乎多數(shù)農(nóng)民工并沒有能夠積累什么財富,這便制約了他們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第一是活累,第二掙錢少,第三有時候干了活但是拿不到工錢。顧山村的張萬武在陜西的乾縣、禮泉等地都割過麥子。因為他身體好,一天能割兩畝麥子,每畝掙七八塊錢,一次干十幾天,活累錢少。有一回給人割了半天麥子,最后卻找不到主人家,工錢便拿不到。二00六年,張鵬帶著老婆孩子去彭陽縣打工,經(jīng)常吃不飽飯,一碗飯三個人推來推去,盡量讓別人多吃一口。后來他們又到煤礦打工:張鵬下煤窯挖煤,老婆馬梅給礦工做飯。但是工資很低,三人勉強過活。
在銀川打工的張平,每天早上六點起床,草草吃兩個饅頭就是早餐,工作到十二點才能休息。午飯后十四點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九點。夏天還要延長半個小時。一個月老板才給大家改善一次伙食,吃一次肉。張平?jīng)]有被欠過工資,但是掙錢很少,零花夠用,其他基本上被用來看病了,并沒有儲蓄。趙銀明十多年來“年年在外打工,去過很多地方,做了很多活兒,吃了很多苦,但沒落下錢”。趙銀明做包工頭時被欠了六萬元:老板不敢欠工人的錢,但是敢欠包工頭的錢……假如這些農(nóng)民工沒有被欠工資,假如他們在吃飽飯之后還能有些積蓄(包括養(yǎng)老金、公積金之類的儲蓄),那么他們在回到村里后生活還會這么拮據(jù)嗎?再假如他們能夠在城市體面地生存下來,甚至還可以接濟在農(nóng)村的親友,農(nóng)村的家會像現(xiàn)在這樣困頓嗎?
二0一七年三月五日,央視財經(jīng)頻道播出了《城市夢想》第三集《父親》,討論欠薪問題。中央黨校教授卓澤淵在寫給欄目組的一封信中說:“沒有農(nóng)民工,就沒有今日中國的現(xiàn)代化。他們是中國城市現(xiàn)代化最大的付出者,有時還是最大的犧牲者。但是誰來保護(hù)他們的合法權(quán)益?……他們的戶口問題、購車問題、購房問題、醫(yī)療問題、養(yǎng)老問題……正是這些最辛勞的城市建設(shè)者,在城市中被活生生地當(dāng)著異邦人,承受著二等市民、三等市民的待遇,我們真的公正么?”“歷史會記住農(nóng)民工的貢獻(xiàn),我們欠農(nóng)民工一個公正的制度安排。”期待一個公正的制度安排能早日到來。
除了體制機制需要改革之外,還應(yīng)該調(diào)動社會的力量。比如顧山村的清真寺,在村民的生活中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村民們集體選出的馬西平阿訇威信很高,他和隊長張萬平一起解決了不少鄰里和家庭的糾紛。在農(nóng)村,宗教和宗族是可以承擔(dān)一些社會功能的,與公權(quán)力一起,共同協(xié)商,來解決農(nóng)村面臨的諸多問題。
如果說《老鄉(xiāng)》一書有什么缺點的話,是關(guān)于村支部和大隊的運作情況沒有太多的描述,比如支書的選舉、大隊長的選舉、有無村委會、他們和鄉(xiāng)與縣里的關(guān)系、村里有無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效果如何等等。宗教的作用也可以再深入討論。公權(quán)力和民間社會的互動需要進(jìn)一步討論,比如搬遷、貸款、鄉(xiāng)村建設(shè)(農(nóng)村的產(chǎn)業(yè)發(fā)展、能否建養(yǎng)老院、如何保育農(nóng)村的文化遺產(chǎn))等問題有無一個協(xié)商機制、決策機制?
但是無論如何,呂延濤的這本書,讓更多的人來了解農(nóng)村的現(xiàn)狀、思考農(nóng)村發(fā)展的路徑、做些持續(xù)的努力去幫助農(nóng)村走向現(xiàn)代化,貢獻(xiàn)良多,非常值得大家關(guān)注。書里提出的問題,也是其他大多數(shù)農(nóng)村所面臨的問題。希望通過政府和民間共同的努力,農(nóng)民們能夠在自己“家門口過上好日子”,外出打工的農(nóng)民也有一條回家的路,能夠回到那個充滿“踏實、溫暖、親情”的家。
一個既有“面子”又有“里子”的城鎮(zhèn)化非常需要,但是也應(yīng)該為建設(shè)“美麗鄉(xiāng)村”付出更多的努力,實現(xiàn)鄉(xiāng)村城市化、城鄉(xiāng)一體化。這是可以做到的,也是應(yīng)該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