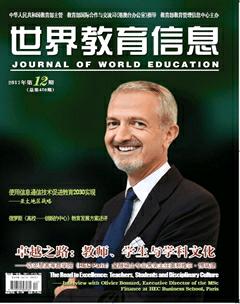擇校與美國教育的未來
琳達·達林-哈蒙德++周岳峰
2017年2月7日,在經過聯邦參議院一次富有爭議性的50票贊成50票反對表決、最后由副總統麥克·彭斯(Mike Pence)投下關鍵性一票打破僵局之后,貝琪·德沃斯(Betsy DeVos)被確認為美國新任聯邦教育部長。接手這項工作時,德沃斯無論是作為學生、家長、教育工作者,還是作為教育委員會的成員,在公共教育方面都乏善可陳。她所做出的唯一公開承諾是要通過特許學校和私立學校教育券在全美范圍內擴大“選擇”,德沃斯在她的家鄉密歇根州一直致力于推動此項工作。
在密歇根州,在擴大營利性特許學校為特色的自由市場體系方面,德沃斯扮演著關鍵性角色:密歇根州79%的特許學校都是營利性的,這是極為不尋常的,因為全美范圍超過80%的特許學校都是非營利性的。德沃斯在K12 公司(K12 Inc)中也持有股份,后者是全美規模最大的營利性特許學校的經營者。在2000年,她資助了一項旨在改變州憲法、以便允許發行各種私立學校教育券的活動,結果未獲成功。
最近,在就有關她出任聯邦教育部長后所設定的目標接受采訪時,德沃斯說她打算進一步闡述選擇的構想,“我預計會有更多的公立特許學校。我預計將會有更多的私立學校。我預計將會有更多的虛擬學校。我預計將會有更多甚至還未出現的各類學校。”
“選擇”已變成為教育改革圈子里一句流行的口頭禪,它主要被用于描述旨在增加獲得公共資助但是由私人經營的特許學校的數量以及旨在通過各種教育券體系給私立學校增加資金的各種倡議。在這兩種情況里的推斷是它們將會給家長和學生增加各種高質量的選項。
然而,即便在特許學校的熱心支持者當中,德沃斯對于“選擇”所采取的做法也是富有爭議性的。出人意料的是,因為出于對密歇根州松懈問責制規定下許多特許學校質量低劣現狀的擔憂,麻省特許公立學校協會(the Massachusetts Charter Public School Association)反對德沃斯的聯邦教育部長提名。此外,美國特許學校主要支持者與資助者之一、億萬富翁伊萊·布洛德(Eli Broad)向參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和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遞交了一封措辭激烈的信件,強調他反對德沃斯出任聯邦教育部長一職。布洛德寫道:“我們必須有一位相信公共教育并且相信有必要使公立學校保持公立的教育部長。”
顯然,相對于各種典型的支持或反對特許學校,圍繞著擇校的各種問題更加復雜。對于處于民主社會里的一種公共教育制度來說,核心問題不是擇校是否應該存在,而是所有的孩子是否都能夠就讀于高質量學校。每當我們匆匆瀏覽500個有線電視頻道卻未找到一個理想的收視選項時,“選擇并不保證質量”這個事實應該是很清楚的。在公立教育方面,這種選擇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結果。
因此,關鍵問題是我們是否能夠建立一個所有學校都值得選擇以及所有孩子都被好學校所選擇的制度。德沃斯的議程會如何影響到這些目標呢?
一、教育選擇的現狀
盡管選擇與私人經營的特許學校和教育券項目有著聯系,但是絕大多數可供選擇的學校均是由公立學區管理的。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各個學區推出了磁石學校(magnet schools),主題學校(譬如專注于藝術、法律或者衛生保健專業的學校),語言沉浸式學校等替代性學校,以及諸如國際公校網絡(the Internationals Network for Public Schools)、新技術網絡(the New Tech Network)、加州的鏈接學習學院(Linked Learning Academies)等各種創新型學校模式。包括紐約、舊金山和馬薩諸塞州劍橋在內的許多城市都最先采用了家長們能夠在他們所在社區的各種不同公立學校中的各種擇校制度。
第一個現代教育券項目是于1990年率先在密爾沃基市(Milwaukee)推出的,該項目向學生們提供公共資金以抵消他們就讀于私立學校的學費。從那時起,各種教育券項目在法院和公投中引發了激烈的爭論。雖然現在全美有14個州和華盛頓特區進行著25個教育券項目,但是,領受教育券人數僅為178070人,這個數字在所有學齡學生總數里所占的比率遠不到1%。大多數教育券項目面向少數學生,而且不包括全額學費,因此,大多數教育券的領受者是已就讀于私立學校的學生。
特許學校這種理念最初是由教師工會領導人阿爾伯特·尚克爾(Albert Shanker)于1988年提出的,并且為進步的教育工作者們所接受,他們將此類學校視為教師能夠進行創新的場所。明尼蘇達州于1991年通過了第一部特許學校法律,到2013年,全美共有42個州頒布了類似的法律。各種聯邦激勵措施開始于喬治·布什政府時期,在奧巴馬執政時代有所增加,而且,由于來自于布洛德、蓋茨(Gates)、沃爾頓(Walton)基金會等慈善組織的大量投資,激勵措施數量進一步增加。現在全美大約有6500所公立特許學校,為250萬名學生提供服務,占到K-12教育學生總人數的5%左右。
雖然公立特許學校總數很少,但是也存在著這樣一些社區,在那里,旨在關閉由學區管理的公立學校的倡議已使得許多或者大多數的學生都留在特許學校里。最極端的事例發生在新奧爾良市:隨著最后一批由學區管理的學校被關閉,或者被改造為特許學校,自新學年開始,所有學生都將需要注冊一所特許學校或者一所私立學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鑒于尚克爾的早期構想,長期以來許多特許學校支持者的一個主要目標是解散各個教師工會。路易斯安那州在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之后辭退了新奧爾良市所有7000名公立學校教師,并以未參加工會組織的特許學校教師取而代之。等到法院宣布此舉非法時,恢復這支公立師資隊伍已為時太晚。
隨著時間的推移,特許學校已從由具有各種創新教育理念的團體所創辦的個別學校發展成為由各種特許管理組織所經營的各種連鎖學校,其中某一些是營利性公司。在1995年至2012年期間,經營特許學校的營利性教育管理公司的數量從5家增加到99家,而由它們經營的特許學校的數量則從6所猛增到758所。
這些教育公司對美國決策過程施加了重大影響。正如《教育周刊》在2013年所報道的,K12公司是一家公開上市的在線特許學校公司,德沃斯曾是其中的一位投資者,該公司在2012年安排了39名游說人士“為將會幫助擴大虛擬學習用途的州和地方的政策效力。”而且,在2004年至2012年期間,營利性的特許學校經營者白帽管理公司(White Hat Management)及其員工向俄亥俄州政治人士的各種競選活動投入了總額超過200萬美元的資金。當時,《教育周刊》曾報道說白帽管理公司“因為表現太差遭到攻擊。”
二、“選擇”的后果
在經過了歷時25年的各種特許學校的努力之后,出現了一些促進高質量教育創新的特許學校。某些特許學校提供包括蒙臺梭利教學法和華德福教學法在內的獨特教學理念,而像圣地亞哥高科技高中(High Tech High in San Diego)等某些特許學校則提供新的學校模式,圣地亞哥高科技高中是專題式的和技術導向型的。在課程以及所提供的各種教學服務方面,其他特許學校與周邊傳統的公立學校幾乎沒有什么差別。
一些很成功的特許學校服務于未經歷“優中選優”過程的具有高度需求的學生,這個過程是一種現在極為常見的做法,學校籍此只接受那些最有前途的學生,并且將那些正在努力學習的人推出去。然而,對于許多學校而言,選擇性已成為它們維持積極結果的主要方法之一。在一種通過考試成績評估學校,且若不繼續提高考試成績的話就面臨被關閉危險的問責制里,取得成功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拒絕或者趕走表現差的學生。
雖然無論是特許學校還是由學區管理的學校都有過類似行為,但是管理各自招生政策和開除學生政策的特許學校會更容易些。在路易斯安那州等州,特許學校可以如同私立學校那樣確定招生政策;在加州等其他一些州,這種做法是非法的。最近一項研究發現,加州1/5的特許學校因限制高度需求學生的入學機會而違反了州法律。大多數研究發現,相比于所在學區的公立學校,特許學校向英語學習者和特殊教育學生所提供的服務不足,在種族和經濟隔離程度方面,特許學校在總體上也高于公立學校。
雖然選擇的承諾聽起來十分誘人,但是現實證明此事更為復雜。事實證明,在許多擇校制度中,只有少數孩子——通常是最有優勢的孩子——才有機會就讀于數量極少的好學校。例如,在新奧爾良市,南方貧困法律中心(the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不得不通過起訴來確保特許學校接受特殊教育學生,因為大多數特許學校拒絕接受這些學生。斯坦福大學研究人員發現,即使在此項訴訟獲得成功之后,特殊教育學生以及其他處于弱勢地位的年輕人仍幾乎沒有什么實際的選擇,因為他們常常被分配到差校,這種分配違背了他們自己的意愿。在新奧爾良市,這些很成功的特許學校明顯地將多數貧窮黑人學生限制在被州評定為“及格”或“不及格”的學校,而只為白人學生以及家境較好的學生服務。
隨著各個州和地方政府利用各種財政危機,以及根據《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里的聯邦激勵措施關閉由學區所管理的學校并且用私營特許學校取而代之,近年來,一種類似的動態在其他20多個城市里已經逐漸展現。例如,在底特律市,最近一名由州政府任命的應急經理(emergency manager)打算用特許學校取代其他學校。而在賓夕法尼亞州,時任賓夕法尼亞州州長的湯姆·科貝特(Tom Corbett)將費城教育預算額削減了數億美元,從而使其陷入財政困境,數百名教育工作者遭到解雇,并且安排了一名經理,由其來分割該學區,并且將其大部分轉交給私營機構。
一個名為“正義之旅”(Journey for Justice)的新組織已著手制止這種趨勢,要求“取代私有化和拆除公立學校體系這種做法的社區主導型替代方案”。該組織由24個城市里的民權和基層團體組成。該聯盟指出,在其每一個學區里,學校關閉會明顯地影響到非裔美國學生和拉美裔學生和社區。因此,許多團體根據《民權法案》第六條款規定提交了訴狀,要求聯邦教育部對這些城市由公立學校關閉所造成的種族后果展開調查。
三、“選擇”的代價
盡管爭先恐后地以學區管理的公立學校換取各種私營的選項,但是研究發現,無論對于教育券項目還是對于特許學校來說,結果都是參差不齊的,一些特許學校表現較好,而其他特許學校表現則比公立學校更加糟糕。例如,斯坦福大學教育結果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Education Outcomes)針對來自于16個州的學生數據所完成的一項大規模研究發現,只有17%的特許學校所產生的學術成果好于傳統公立學校,而37%的特許學校的表現要比與其相對應的公立學校更加糟糕。大多數特許學校則沒有顯示出任何差異。
結果在各個州也是不同的,這些州有著極為不同的法律。在加利福尼亞州,特許學校受到相當嚴密的監管,以此確保公平入學、深思熟慮的課程以及合格的員工。雖然總體表現與其他公立學校類似,但那些專注于在家教育或者遠程學習的特許學校的表現較為糟糕。特許高中學生在數學方面的表現較差,而在英語方面的表現較好。在俄亥俄州和亞利桑那州,不受管制的營銷策略已經產生了種類繁多且鮮有公共保障措施的營利和非營利性的提供者,大多數特許學校評級不高,而且特許學校學生的表現一向不如公立學校的同齡學生。
在線特許學校存在著大量丑聞,鑒于經營者不必因辦學購置校舍而且常常以低薪雇請少量教師,這些學校雖然一向有負面消息結果卻獲取了最高利潤。例如,在最近十年里,《哥倫布電訊報》(The Columbus Dispatch)曾對俄亥俄州一所名叫ECOT(優科泰)的網絡學校做過報道,該網校在一個月里為2270名學生獲得了932030美元納稅人的錢,但是僅提供了7名學生登錄的證據。
在德沃斯的故鄉密歇根州,批評者說不負責任的特許學校政策在最貧窮的社區中已經產生了大量差校。盡管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一項研究發現,就各種結果來說,密歇根州特許學校學生們的表現好于“補習學校”(feeder schools)相似的學生們,但是該項研究并未將特許學校的各種結果與密歇根州2/3學生們并未離開的學校——該州實力較強的學校——進行比較。
一些密歇根州官員認為,這項選擇計劃和同時削減公立學校預算的影響在全州范圍都是負面的。州教育委員會主席(the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約翰·奧斯汀(John Austin)特別提到選擇的擴大正在“破壞各種學習結果。”而且,確實,在過去十年里,該州的整體表現已急速下降。直到21世紀初,密歇根州排名一直穩定地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且常常在國家教育進步評估(the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中位居各州中的第一梯隊,尤其是在數學方面。然而,到2015年時,它卻落后于大多數州。在四年級閱讀各項評估中,只有7個州得分低于密歇根州,而且沒有一個州黑人學生在閱讀或者數學方面的分數下降。雖然八年級學生的表現更好一些,但是他們的得分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在閱讀和數學方面,非洲裔美國學生的表現不如幾乎所有其他州里的同齡人。底特律學生的得分低于美國所有其他主要城市學生的得分。
四、國際視野
這些結果跟我的同事們與我在對一些沒有保障措施的情況下采用了私有化倡議的國家調查里所獲得的結果是相似的。在我們所著的《2016年全球教育改革》(2016 Book Global Education Reform)一書中,我們追蹤了在智利以及后來在瑞典所發生的情況,前者是從1980年獨裁者奧古斯托·皮諾切克(Augusto Pinochet)統治時期開始的,后者則是從1992年開始的。當時,這兩個國家廣泛采用了像教育券項目和特許學校那樣的政策,包括向私立的營利性學校注入公共資金,同時從各自公立學校體系里撤資。種族隔離和不平等程度加深以及跟國際同齡人相比學習成績大幅度下滑之后,兩國正在設法改弦易轍。
瑞典曾是表現優異的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教育“明珠”,現在該國在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中的表現卻遠不如大多數歐亞國家。瑞典與芬蘭形成了鮮明對比,芬蘭曾是斯堪的納維亞地區國民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一個國家,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芬蘭在建立一個高質量的公共教育體系方面投入了龐大資金,該國現在在教育領域各項國際排行榜上的表現一直名列前茅。
同時,智利的表現甚至不如瑞典,較為接近于發展中國家的排名,而且該國優異生的數量僅為古巴的1/3,后者在中南美洲地區各項排行榜上居于領先位置。如同芬蘭一樣,古巴在本國的公立學校投入了一支準備充分的師資隊伍、一系列探究取向課程,以及與學生家庭之間建立了牢固關系。
在像瑞典和智利等一些國家里,當私立學校數量激增以及營利性機構的提供者為了獲得更大利潤而犧牲質量、從而產生負面結果的時候,也許就會出現一個臨界點。當美國一些州在私有化選擇方面接近于一個臨界點的時候,同樣的情況也許將會發生。例如,與公立學校里類似的學生相比,對路易斯安那州和印第安納州的教育券項目所展開的三項研究發現,它們對于學生們的成績產生了大量負面影響。
顯然,存在著一些極為出色的私立學校和特許學校,但是,也存在著一些極為失敗并且剝削利用最弱勢學生的私立學校和特許學校。一個公共教育體系不可能對選擇抱著僥幸心理:它必須確保所有孩子都享有就讀于高質量學校的均等機會。
五、“選擇”和民主可以共存嗎?
是否存在著美國可以獲得選擇的各種好處同時沒有伴隨著像密歇根州那樣的倡議而產生的各種缺點的辦法呢?解決這一挑戰的關鍵是創建一種由值得選擇的學校所構成的體系,而且在該體系里,所有的孩子都是由一所好學校選擇的。
在某些州和某些國家所發現的各種糟糕的結果與我們的表現最佳的州——馬薩諸塞州的那些結果形成了對比。馬薩諸塞州有許多所由學區管理的選擇學校(schools of choice),以及少數高績效的特許學校——只有81所,這些特許學校是按照對特許學校所設定的數量上限運營的。人們不僅對于這些學校的課程、人員素質和學業成績抱有期望,而且對于招收并保留高度需求的學生都抱有很高的期望。
馬薩諸塞州的例子證明也許支持一種包含富有成效的選擇的民主制度的原則。這樣的制度將會通過鼓勵創新和允許包括各個學區所管理的公立學校在內各個學校多樣性的方式提高教育質量和公平性。它將定期監測各種公開的招生政策,保持對平等和機會所做出的承諾,并且將禁止選擇性招生或者將學生們趕走的做法。學校的撥款將以學生的需要作為根據,而且在學費、其他費用或者交通方面將不會給家庭帶來任何負擔。允許各種營利性實體經營的學校將會被認為造成一種固有的利益沖突。簡而言之,這種體系將有必要如同一個公共體系那樣運作。
最后,當在學校方面的各種投資使得所有的年輕人能夠變成有效地為他們的民主社會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做好準備的負責任公民的時候,就是促進公共福利的一種最好方式。正如約翰·杜威(John Dewey)在《學校與社會》(The School and Society)一書中所寫道的:“最好和最有智慧的父母為其孩子所爭取的,一定也是整個社會為所有的孩子所爭取的。關于我們學校的任何其他想法都是狹隘的、不恰當的;如要那樣做,就會破壞我們的民主……只有讓所有的個人充分發展,社會才有機會實現自身的目的。”
編輯 朱婷婷 校對 許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