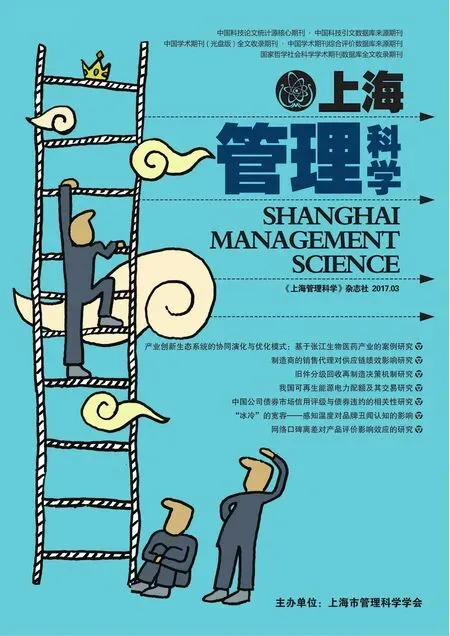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的相關性
——基于我國本土數據的實驗研究
錢 坤, 秦向東
(上海交通大學 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上海 200030)
?
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的相關性
——基于我國本土數據的實驗研究
錢 坤, 秦向東
(上海交通大學 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上海 200030)
現有文獻描述性地探討了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的相關性:總體而言,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呈弱負相關性。本文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理論模型進一步研究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的決策機制;并通過實驗驗證了兩者的弱負相關性:有相當一部分決策者前后行為選擇不一致。我們利用道德許可效應和道德凈化效應對這一結果進行了解釋。本文指出,道德許可效應給組織帶來的危害勝于道德凈化效應給組織帶來的益處。本文支持管理者必須對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進行引導,不可放任員工自行調整道德行為。
組織公民行為; 反生產行為; 道德自我調節
1 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
組織公民行為是指有助于保持或改善支撐任務績效的組織社會心理環境的行為。反生產行為是指有損于組織的運作或財產,或者降低員工效率的行為。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雖然短期看起來對組織運作影響不大,但長時間積累會對組織運作產生重大影響。
組織公民行為對于組織的積極影響可以歸納為提高生產效率、高效運用資源、協調群體活動、提高管理效率、改善企業文化、吸引優秀人才和維持組織穩定 (Podsakoff,2000)。
反生產行為對于組織的消極影響更加易于量化:美國每年因為員工偷竊和欺詐行為造成約400億美元的損失;33%~75%的員工實施過不同形式的反生產行為,而30%的企業破產是因為這些行為造成的(張永軍等,2010;Mikulay等,2001)。組織公民行為依結構可分為二維、三維、四維、五維等,對組織公民行為的結構最早做出分類的是Smith等(1983),他做出的二維分類包括一般順從和利他行為。被廣泛接納的是Organ提出的五維結構,即利他行為、文明禮貌、運動員精神、責任意識和公民美德。
反生產行為依結構亦可分為二維、三維、五維等,幾乎在Smith對組織公民行為的結構做出分類的同時,Hollinger和Clark等(1983)對反生產行為的結構率先做出分類,他們將反生產行為分為二維:財產偏差、生產偏差。被廣泛接納的是Bennett和Robinson(2000)的理論,他們把反生產行為分為組織偏差和人際偏差。
盡管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對于組織利益的影響截然相反,早期文獻認為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的有兩個相同點:第一,兩者均屬自發行為,即組織合同沒有明確規定員工必須要實施組織公民行為,不能實施反生產行為,兩者均受員工主觀意識的支配,第二,兩者均屬角色外行為,超出工作職責要求(張永軍等,2010)。從這樣的概念定位來看,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顯然受到員工個人道德的規范調節,組織公民行為在道德上是受到鼓勵的,反生產行為在道德上要受到譴責。
無論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是否是嚴格自發的,兩者都是員工個人心理調節過程。工作中積極的事件將觸發組織公民行為,消極的事件將觸發反生產行為。部分文獻對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對員工心理的潛在影響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探討,這部分文獻另辟蹊徑展現組織公民行為的陰暗面和反生產行為的積極面。管理者持續推行組織公民行為將增加員工壓力,影響員工身心健康。而反生產行為有助于員工發泄負面情緒,有利于身心健康。
2 道德許可效應和道德凈化效應
因為做好事而使得自我價值感(self-worth)上升時,人們更偏好實施不道德行為。這一系列補償行為被稱為道德許可效應(moral licensing)。Monin 和 Miller(2001)發現一開始對性別歧視持否定態度的男性更容易在之后的決策中對女性進行歧視。Mazar和Zhong(2010) 發現消費者選擇有機和環境友好型商品后更容易說謊和偷竊。
因為做壞事而使得自我價值感受損時,人們更偏好做符合道德觀念的行為來彌補受損的自我價值。這一系列補償行為被稱為道德凈化效應(moral cleansing)。Carlsmith和Gross (1969) 讓被試電擊“犯錯誤”的實驗助手。他們在對比4組實驗結果后發現,補償和同情對于解釋之后順從的增加都不是必要的,暗示自我價值的受損對于之后的友善行為有支持作用。
Sachdeva等[1]發現道德凈化效應和道德許可效應有相同的觸發機制。他們發現對于自我的道德選擇的反思才會觸發道德凈化效應和道德許可效應,而對他人道德選擇的認知不會觸發上述2個效應。
個體的道德自我價值存在一個均衡。道德凈化效應和道德許可效應是自我價值感認知的負反饋效應,兩者使得偏離均衡的自我價值感向均衡方向移動:當符合道德的行為使得自我價值感上升時,觸發道德許可效應,個體更偏向于實施不道德行為使得高于均衡的自我道德價值回到均衡;當不道德的行為使得自我價值感下降時,觸發道德凈化效應,個體更偏向于實施符合道德的行為使得低于均衡的自我道德價值回到均衡[1](Zhong,2009; Zhong,2010)。
道德許可效應和道德凈化效應因此被一并歸類為道德平衡過程(moral balancing),和道德一致過程(moral consistency)相對,后者表示前后兩個道德行為的選擇一致。Mulder等[2]認為自我系統的全部目標在于保持自我完整性,和道德與環境適應的充分性。
道德許可效應被廣泛應用于管理學用于解釋個體前后道德選擇不一致。Klotz等從道德許可效應的角度闡述了個體實施組織公民行為最終導致繼續實施反生產行為的原因。
道德許可效應和道德凈化效應和兩者所指向的道德自我價值均衡,為解釋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的適度正相關關系提供了理論支撐。許多試圖解釋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之間的適度正相關的文獻所使用的邏輯都可以歸納到道德自我價值均衡中來[3]。
3 模型設計
組織公民行為的利他性決定了實施者犧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使得他人或組織獲益,而反生產行為恰好相反。為了使自己獲益不惜犧牲他人或組織的利益,本文的理論模型把利益量化為金錢激勵。
設第t期即時自我道德價值(moral self-worth)增量為

本模型在Gneezy等[9]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新增兩個參數θ和β。其中θ∈[0,+∞),θ越小,道德選擇次數相對于每次選擇涉及的收益額度對it的影響越大,當θ=0時,收益額度對it沒有影響。當θ<1時,道德選擇次數相對于收益額度對it的影響較大;當θ=1時,道德選擇次數相對于收益額度對it的影響相當;θ>1,選擇次數相對于收益額度對it的影響較小。
β∈[0,+∞),給定πt,y,it隨β遞增。當θ=1,β=0時,模型與Gneezy等[9]相同。
設第t期累計自我道德價值為at,
其中,δ∈(0,1),t-1期1單位的累計自我道德價值積累到t期為δ單位;it在時間上累計進入at,故稱it為即時的自我道德價值,at為累計的自我道德價值。
由于β的存在,at可正可負,與Gneezy等[9]不同。設第t期一個人的效用函數為
其中,mt是第t期金錢激勵對效用的影響,
πt,x是自己的金錢收益。
it是第t期即時自我道德價值增量,
在Gneezy等[9]的模型中,it不進入函數ut,當期的在道德問題上的選擇帶來的負罪感對當期沒有影響。而本文的模型中當期的道德問題上的選擇同時通過金錢激勵和自我道德價值的增減兩個方面對當期效用產生影響,一個人面臨當期的金錢和由道德選擇產生的即時自我道德價值增量兩者的權衡取舍。
雙方金錢收益滿足
其中,λ∈(0,+∞),λ是個體與他人或組織間的邊際收益替代率:犧牲個體1單位的收益,可以給他人或組織帶來1/λ單位的收益,b是常數。
在極端的情況下,如果個體在第t期完全不關心他人的金錢收益,則他做道德選擇時最大化自己的金錢收益而將他人的金錢收益降到最小,此時他實施了反生產行為,it必定為負;如果個體在第t期完全不關心自己的金錢收益,則他做道德選擇時把自己的金錢收益降到最低而使他人的金錢收益最大化,此時他實施組織公民行為,it必定為正。
作如下假設:

假設(2)說明上一期累計自我道德價值對金錢激勵沒有影響;假設(3)說明上一期累計自我道德價值越大,當期即時自我道德價值增量對效用影響越小。
根據如上假設,注意到


當πx<πx*時,a>a*(累計自我道德價值大于均衡值),再多增加一單位的金錢收益所產生的即時自我道德價值減少量的影響小于金錢激勵的影響,使得πx增加,累計自我道德價值a變小,趨于均衡的累計自我道德價值a*;反之,當πx>πx*時,a 圖1 不同的累計、自我道德價值均衡 故在給定假設下,πx*,以及與πx*對應的i*,a*是唯一的累計自我道德價值均衡。 當a*>0時,在均衡狀態下,一個人每一期在自我道德價值中投入,實施組織公民行為來使a=a*,自我道德價值處于盈余狀態,當a*<0時,在均衡狀態下,一個人每一期從自我道德價值中支出,實施反生產行為來使a=a*,自我道德價值處于赤字狀態。 在個體的道德調節系統中存在既定的自我道德價值均衡,當實施組織公民行為使得自我價值感上升時,觸發道德許可效應,個體更偏好實施反生產行為,使得自我道德價值降低到均衡水平;當反生產行為使得自我價值感下降時,觸發道德凈化效應,個體更偏向于實施組織公民行為使得自我道德價值上升到均衡。 道德選擇實驗可以讓被試自發地在實施組織公民行為和實施反生產行為之間做出選擇。 本文實驗設計的目的在于檢驗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之間的相關關系,實驗分為基準組和實驗組。在基準組中,決策者需要做出一次選擇,實施反生產行為可以使得決策者額外獲得4元人民幣,而實施組織公民行為可以使得和決策者配對的一方額外獲得4元;而在實驗組中,決策者需要先后做出二次選擇,每次選擇實施反生產行為可以使得被試額外獲得2元,而每次實施組織公民行為可以使得和被試配對的一方額外獲得2元。決策者第一次做選擇時不知道還有第二次選擇,這樣的設計是為了避免決策時其他策略性的考慮。 所有實驗都在上海交通大學Smith實驗室進行,共舉行9場實驗,其中4場基準組實驗,5場實驗組,每場24人,基準組96人,其中決策者48人,接收者48人,實驗組120人,其中決策者60人,接收者60人。全部被試均為上海交通大學學生。實驗收益使用人民幣結算。被試不能重復參與2場實驗。 所有被試共216人,其中男性142人(65.7%),女性74人(34.3%)。其中,基準組96人,其中男性66人(68.8%),女性30人(31.3%);實驗組120人,其中男性76人(63.3%),女性44人(36.7%)。有如下實驗結果: (1) 基準組中68.6%的男性和76.9%的女性決策者選擇反生產行為(Z=-0.560,p=0.288)*本文比例數據之間相互比較均使用Mann Whitney U檢驗,Z統計量,顯示漸進單側顯著性;實驗組中78.4%的男性和78.3%女性決策者第一次選擇反生產行為(Z=-0.011,p=0.496);實驗組中73.0%的男性和65.2%女性決策者第二次選擇反生產行為(Z=-0.632,p=0.264);實驗組中62.2%男性和52.2%女性決策者先后二次選擇反生產行為(Z=-0.757,p=0.225);實驗組中10.8%男性和8.7%女性決策者先后二次選擇組織公民行為(Z=-0.263,p=0.396);實驗組中27.0%男性和39.1%女性決策者改變前后二次道德選擇(Z=-0.972,p=0.166)。 無論在基準組中還是在實驗組中,性別對于被試在自發性道德選擇中沒有顯著差異。 (2) 實驗組中第一次選擇反生產行為的決策者的比例78.33%(47/60)和在基準組中選擇反生產行為的比例70.83%(34/48)比較(Z=-0.890,p=0.187)沒有顯著差異。 在實驗組中,在完成第一次道德選擇前,因為被試不知道有第二次道德選擇,故實驗組中第一次道德選擇和基準組中的道德選擇具有可比性。實驗組中第一次道德選擇涉及的金額為2元,基準組中道德選擇涉及的金額為4元,兩個設計中道德選擇沒有檢測到差異說明涉及金額對道德選擇的影響有限。 (3) 在實驗組中,第一次選擇組織公民行為的決策者中第二次選擇反生產行為的比例53.85%(7/13)顯著少于第一次選擇反生產行為的決策者中第二次繼續選擇反生產行為的比例74.47%(35/47)。(Z=-1.424,p=0.077) 測得第一次選擇組織公民行為和第二次選擇反生產行為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185(p=0.078,單側顯著性),呈弱負相關性。本文實驗結果與Dalal(2005)測得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測得的相關系數-0.16,Spector等[4]測得的-0.13較為接近。 (4) 在基準組中,選擇反生產行為的決策者的比例70.83%(34/48)顯著多于在實驗組中,先后2次選擇反生產行為的決策者的比例58.33%(35/60)(Z=-0.890,p=0.091)。 在基準組中,選擇組織公民行為的決策者的比例29.17%(14/48)顯著多于在實驗組中,先后2次選擇組織公民行為的決策者的比例10%(6/60)(Z=-0.890,p=0.006)。 注意到結果(2)發現基準組和實驗組間第一次道德選擇沒有顯著差異,在結果(3)觀察到有31.67%在兩次道德選擇之間不一致:有20%的決策者第一次選擇組織公民行為,第二次選擇反生產行為;有11.67%的決策者第一次選擇反生產行為,第二次選擇組織公民行為。這兩部分人共同導致了從結果2到結果4的轉變,這表明在模型中拒絕參數θ=1,接受θ<1,即選擇次數相對每次選擇設計的收益額度更容易對個體的自我道德價值產生影響。 (5) 在實驗組中,第一次選擇組織公民行為的決策者中第二次選擇反生產行為的比例53.85%(7/13)顯著高于比第一次選擇反生產行為的決策者中第二次選擇組織公民行為的比例25.53%(12/47)。(Z=-1.926,p=0.027) 首先,選擇組織公民行為的決策者中,改變道德選擇的轉而選擇反生產行為的比例要顯著高于首先選擇反生產行為的決策者中,轉而選擇組織公民行為的比例。這表明我們在模型中拒絕β=1,接受β>1,即選擇道德行為相對于選擇不道德行為而言更容易在道德價值上進行積累,先選擇道德行為的個體更容易觸發道德平衡的過程。 通過結果(2)看到在沒有懲罰或獎勵的條件下,反生產行為發生的可能性要大于組織公民行為發生的可能,所以,在企業內部單單依靠員工自發的道德調節可能會對企業運轉產生不利影響。這就需要管理者營造良好的企業組織內部的倫理氣氛[6]。 結果(3)說明道德一致過程發生的可能大于道德平衡過程,這使得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呈負相關性,但道德平衡過程使得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之間僅存在較弱的負相關性。這表明提倡和宣傳組織公民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組織運轉,但是這種改善受到道德平衡過程的限制。 結果(4)和結果(2)的對比可以發現,在道德許可效應和道德凈化效應的共同作用下,有相當一部分比例(31.67%)的個體的道德選擇發生了變化。 研究反生產行為和組織公民行為的文獻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注重研究誠信度測試,從而給組織招募人員提供測試標準,把偏向于實施反生產行為的應聘者堵在門外。這些研究的局限性在于過度強調個體差異因素,忽視了兩種自愿行為的環境基礎和個體共同因素。21世紀以來,研究逐漸深入到探究兩種行為發生的條件。Fox等(2001)提出反生產行為的情緒模型,通過實證檢驗發現消極情緒和反生產行為具有顯著的相關性,研究得到廣泛認可。 另一部分文獻著重研究兩者行為的前因變量,這些研究的目的在于給組織控制兩種行為的發生,減少反生產行為,增加組織公民行為提供依據。然而,在Dalal(2005)利用大量數據得出反生產行為和組織公民行為僅存在弱負相關關系之后,研究者不禁提出反思:如果在短時間內在同一個體中發現反生產行為和組織公民行為Dalal(2009),對于具體某一個前因變量的控制是否能夠推動組織向有利的方向發展?某個前因變量是否會在抑制反生產行為的同時抑制組織公民行為?或者在鼓勵組織公民行為的同時促成了反生產行為? Spector等[4]進一步發展情緒模型以應對前因變量的局限性。他們指出,憤怒情緒會導致反生產行為的發生,負罪情緒會導致組織公民行為的發生,而強迫性的組織公民行為會帶來憤怒情緒,反生產行為會導致負罪情緒,從而使得兩種行為在短時間內相互轉化。 本文在實驗中發現,相當比例的被試在兩者行為間相互轉化,與Spector等[4]的理論相互印證。我們進一步從道德調節模型去解釋這種轉化,當組織公民行為使得個體的道德價值高于均衡時,個體感到他們的付出沒有被合理地獎勵,產生憤怒情緒[4],觸發道德許可效應,從而實施反生產行為;當反生產行為使得個體的道德價值低于均衡時,個體發現他們的消極舉動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產生負罪情緒[4],觸發道德凈化效應,從而實施組織公民行為。個體在短時間內同時實施反生產行為和組織公民行為使得個體的道德價值在其均衡附近波動。 由結果(5)可知,道德許可效應作為自我道德調節的一環給組織帶來了消極效應,53.85%的決策者在實施組織公民行為后,反過來實施反生產行為;而只有25.53%的決策者在選擇實施反生產行為后,心生愧疚,觸發道德凈化效應,在第二次道德選擇中選擇實施組織公民行為。道德許可效應發生的可能超過了道德凈化效應發生的可能,預示著如果管理者放任組織環境不管,員工自發的道德系統調節最終將使反生產行為主導企業文化,可能給企業帶來負面影響。 本文首先建立了理論模型,以探究個體如何在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間做出選擇;隨后通過實驗檢驗了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的相關關系,系統歸納并驗證了部分文獻關于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弱負相關關系并給出了解釋。 基于本文的理論和實驗結果可以發現,企業應該從道德許可效應和道德凈化效應入手,去控制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我們的實驗結果表明,在短時間內企業員工就有可能會切換道德選擇,這說明如果僅僅利用控制前因變量來達到促成組織公民行為,抑制反生產行為并不一定可行。 本文提供了中國本土的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的實驗數據。集體主義和功利主義在我國市場經濟的舞臺上注定要擦出火花,而組織公民行為和反生產行為是舞臺上不可或缺的主角。中西方文化存異,中國文化以德為首,道德性對于這二類相對的行為應受到充分重視[7]。我國盛行“面子文化”“圈子文化”,個體道德系統的自我調節對兩類行為的發生有重要影響。對兩類行為的進行本土化研究,深入探討兩類行為的決策機制對于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非常有現實意義。 在組織內部,通過營造良好的組織文化氛圍,或可擴大員工的道德許可效應,使得實施反生產行為的員工能夠回頭,轉而實施組織公民行為,縮小道德凈化效應,使得實施組織公民行為的員工繼續發揮其良好的品行,無怨無悔。繼而,如何營造良好氛圍以干預組織內部員工的道德許可效應和道德凈化效應是未來的研究方向之一。 [1] Sachdeva S, Iliev R, Medin D L. Sinning saints and saintly sinners the paradox of moral self-regulation[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20(4): 523-528. [2] Mulder L B, Aquino K. The role of moral identity in the aftermath of dishonesty[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3, 121(2): 219-230. [3] Spector P E, Fox S.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 and organis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re they opposite forms of active behavior?[J]. Applied Psychology, 2010, 59(1): 21-39. [4] Spector P E, Fox S. Theorizing about the deviant citizen: An attributional explanation of the interplay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and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10, 20(2): 132-143. [5] 張小林, 戚振江. 組織公民行為理論及其應用研究[J]. 心理學動態, 2001, 9(4): 352-360. [6] 劉文彬, 井潤田. 組織文化影響員工反生產行為的實證研究——基于組織倫理氣氛的視角[J]. 中國軟科學, 2010(9): 118-129. [7] 彭賀. 中國知識員工反生產行為分類的探索性研究[J]. 管理科學, 2010(2): 86-93. [8] Erat S, Gneezy U. White lies[J]. Management Science, 2012, 58(4): 723-733. [9] Gneezy U, Imas A, Madarász K. Conscience accounting: emotion dynamics and social behavior[J]. Management Science, 2014, 60(11): 2645-2658.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itizen Behavior and Counterproductive Working Behavior——An Experimental Study Based on Chinese Data QIANKun,QINXiangdong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Many existing studies focus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itizen behavior and counterproductive working behavior. Meta-analysis have shown that organizational citizen behavior and counterproductive working behavior are only moderately negatively related. We first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model to illustrate how individual makes tradeoff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itizen behavior and counterproductive working behavior. We then use lab experiments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ose two behaviors. Our experimental results support the finding of the Meta analysis. Some subjects were found changing their moral choices even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e use moral licensing and moral cleansing to explain our main findings. We further point out that the damage moral licensing brings to an organization may be greater than the benefit moral cleansing brings in. We recommend that the manager should intervene in the voluntary behaviors in the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al citizen behavior; counterproductive working behavior; moral self-regulation 2017-02-28 錢 坤(1992-),碩士生,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學,實驗經濟學。Email:fredqian@sjtu.edu.cn。秦向東,教授,研究方向: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 1005-9679(2017)03-0100-06 F 016; F 270 A
4 實驗設計
5 實驗結果
6 實驗結果分析
7 結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