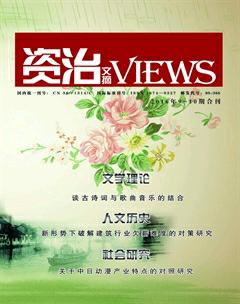淺析迎福鐘馗與紫砂雕塑
張斌
【摘要】紫砂雕塑作為我國優(yōu)秀的磚統(tǒng)文化藝術(shù)之一,它體現(xiàn)了中國人民的智慧所在,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瑰寶。紫砂雕塑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而且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紫砂雕塑的形式越來越豐富多彩,紫砂陶藝以手工完成雕塑人像藝術(shù),相相如生的人像雕塑維妙維肖也因紫砂泥的觸摸富有彈性感,使得紫砂雕塑更富有一番逼真性現(xiàn)代紫砂雕塑的發(fā)展不僅要吸收磚統(tǒng),在民族文化發(fā)展長河中,雕塑以各種材質(zhì)不同而形意相同的形式,以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為背景,用樸素易懂的表現(xiàn)手法來實現(xiàn)藝術(shù)價值。在雕塑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前人采用了各種制作雕塑的材料,如早期的石雕、骨雕、泥雕、金屬雕塑、陶瓷雕塑等等。而宜興紫砂陶雕制而成的紫砂雕塑尤為精美,至今已成為我國民間傳統(tǒng)雕塑中獨(dú)特的藝術(shù)品,已被越來越多的藝術(shù)愛好者接受。
【關(guān)鍵詞】紫砂陶;雕塑、鐘馗;民間藝術(shù)
鐘馗形象作為我國傳統(tǒng)藝術(shù)中的一個獨(dú)特的圖像符名在《尚書》、《左傳》、《茍子》中又作“仲虺”、“中歸”、“中壘”,號,有著悠久歷史和豐富的內(nèi)涵,鐘馗形象的演變是在歷代此或為后世鐘馗或是門畫中的“郁壘”之原型。人們的崇拜和信仰過程中逐漸完成的。鐘馗原型出自上古儺儀,鐘馗傳說的形成是在漢魏之際,隨著唐代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和民俗文化的生動化、世俗化。鐘馗這一形象徹底完成了從原型到傳說的轉(zhuǎn)變,鐘馗信仰中的神圣性逐漸減弱。世俗性不斷加強(qiáng),并出現(xiàn)了各種各樣的演義故事。宋代經(jīng)濟(jì)進(jìn)一步繁榮,文化高度發(fā)展,民間藝術(shù)、宮廷藝術(shù)與文人藝術(shù)互相影響聯(lián)系密切,鐘馗形象也在這種交流中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元代以后,文人開始從自己的特殊視角理解鐘馗這一形象,鐘馗信仰至此真正完成了文人化的過程。
鐘馗是打鬼驅(qū)除邪祟的神,鎮(zhèn)宅辟邪,還是萬應(yīng)之神,要福得福,要財?shù)秘敚星蟊貞?yīng),《迎福鐘馗》作品大膽取舍、適度夸張、以及重神態(tài)、情節(jié)、氣韻、尤其是不拘泥于自然真實性,不過分追求生理解剖的準(zhǔn)確性,以意境為主的創(chuàng)作方式,而且根據(jù)表達(dá)意圖之需要和藝術(shù)效果,惟妙惟肖的《迎福鐘馗》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臉部表情夸張但不失真,臉部的肌肉凹凸有致,二條上翹的眉毛,胡須與鬢發(fā)根根清晰,凸起的眼睛已經(jīng)成為任何一款鐘馗的象征,列開的嘴讓人看到了笑容,右手托著一把折扇,一只大大的蝙蝠附在上面,左手拿著那邊永遠(yuǎn)不離身的劍,整昂首闊步的走向人間為人們送福,值得一提的是整件作品的裝飾,作品大膽運(yùn)用了紫砂與黃金、玉搭配,鐘馗官帽的帽沿、腰帶、鞋子、還有那只停留在折扇的大蝙蝠巧妙的運(yùn)用描金,更體現(xiàn)出富貴,鐘馗微凸的大肚子上鑲嵌一塊雕工非常精致的玉佩更顯示出高貴,遠(yuǎn)看鐘馗身披黃金手托金蝙蝠,整滿臉微笑的到人間送福,所到之處洋溢著幸福美滿,這正是《迎福鐘馗》作品所要表現(xiàn)出的意境。
紫砂陶雕塑能成為我國民間傳統(tǒng)工藝的一朵奇葩,是由于紫砂陶材質(zhì)細(xì)膩、可塑性好、色澤古樸、具有很濃郁的古文化內(nèi)涵,燒制后其深沉的韻味非常符合東方人的審美觀念。最早的紫砂雕塑可追溯至明、清時期,要比佛山公仔陶、德化瓷雕塑晚一些,而至上世紀(jì)中葉發(fā)展較快。目前不論從經(jīng)濟(jì)和藝術(shù)來說都有較大的發(fā)展,似有超過前者之勢,敢為厚積薄發(fā)而來,由于紫砂泥質(zhì)穩(wěn)定性好、易成形、不易變形,塑造的物體可精細(xì)、可粗獷,燒成后呈色均勻、純正,有珠圓玉潤之感再加上與其他材質(zhì)的裝飾增加了其的可看性,具有美好的發(fā)展前景。
紫砂雕塑從初創(chuàng)走到今天,就與融貫一切的傳統(tǒng)文化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它的開始孕育發(fā)展與壺以文化一樣,同樣經(jīng)歷了漫長的過程,其間一代又一代的從一人員從養(yǎng)家糊口到志趣追求,向傳統(tǒng)學(xué)習(xí)又向傳統(tǒng)挑戰(zhàn),逐步地融入世界陶藝,明初時大彬的第一尊佛像(相傳)到清代陳鳴遠(yuǎn)的瓜、果、菱、藕,其泥質(zhì)、泥色的選擇與掌控,形體骨架的捏塑與構(gòu)架,甚至到施于行外的肌理紋飾都傳遞出雅而不俗、品味高遠(yuǎn)的格調(diào)和境界。在千千萬萬的壺藝中,紫砂雕塑不段繁衍出新的樣式與生命,大眾審美情趣、火熱的收藏市場及業(yè)內(nèi)人士的不懈努力構(gòu)成其必要的發(fā)展要素。而作者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人文環(huán)境中得以錘煉,也在茶文化的普及、深入發(fā)展中,在品壺、賞壺、玩壺中找到了再現(xiàn)紫砂雕塑的又一番天地,也為手中一廂情愿的捏塑找到了變與不變常態(tài)中的最好歸宿。一種藝術(shù)樣式的派生,一定有其適合的土壤,一定有其合適情感表達(dá)的人文環(huán)境,尤其是作者的眼界、學(xué)識、技能等綜合因素的考量以及創(chuàng)新求異、突破禁忌的沖動,才能有共融的藝術(shù)樣式不斷的涌出。紫砂雕塑雖說是眾多造型藝術(shù)的一脈,但它的獨(dú)特性(泥質(zhì)、成形、明針工夫、摻砂及燒制后把玩)是顯而易見的,也是其他雕塑門類所不具備的,另外,壺中天地也為紫砂雕塑廣義上的布局、點(diǎn)化甚至化平庸為神奇而創(chuàng)造了變與不變的機(jī)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