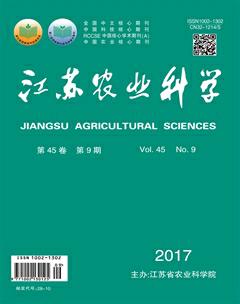農村金融發展、農業勞動力轉移與農民增收
鐘潤濤++馬強



摘要:基于2000—2015年的數據,從理論和實證2個方面分析農村金融發展、農業勞動力轉移與農民增收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農民收入是農村金融規模、政府財政支農的格蘭杰原因,反之不是,農業信貸比率、農村外出務工人數是農民收入的格蘭杰原因,反之不是。 誤差修正模型結果顯示,農民收入表現出較弱的對長期均衡關系的誤差修正效應。脈沖響應分析結果顯示,農民收入受到農村信貸比率、外出務工人數、自身的正向沖擊后,會有所提高;金融規模對農民收入沖擊的影響有限,財政支農的沖擊會抑制農民增收。最后針對結論,提出可通過創新農村金融服務體系、整合拓展農村金融服務領域、提高農業財政補貼效率、創造當地就業機會以提高農民收入的建議。
關鍵詞:農村金融服務;農民收入;農業勞動力轉移;格蘭杰因果檢驗
中圖分類號: F830.34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17)09-0271-05
“三農”問題是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農民收入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得不面對的難題,我國農業人口眾多,廣大農民不能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也就難以實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收入雖大幅提升,但相比城鎮居民收入仍存在較大差距。影響農民收入的因素有很多,依照林毅夫的觀點,從長遠看,發展普惠金融,發展農村金融的作用會越來越明顯,農村金融發展會優化農村地區的產業結構,進而提高農民收入[1-2]。
我國農村地區人口基數較大,穩步提升農民收入是農村工作的重點,事關農村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大局。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居民收入大幅提升,由1978年的134元增長到2015年的10 000元以上(圖1),預計到2020年,將達到 15 000 元。但從絕對收入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民收入水平雖大幅提高,但和城鎮居民相比,農民收入的增速、增幅仍然較低,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不僅體現在城鄉經濟發展水平的差別,更體現在收入水平的差別上。1990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為824元,截至2015年年底,城鄉收入差距已擴大為19 773元,除了可統計到的收入外,城鎮居民在教育、醫療、交通等社會公共服務方面享受到的隱性收入更是遠高于農村居民。
增加農民收入、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消除貧困是我國長期以來農村改革的基本目標,如何提高農民收入也是學者研究的重點課題之一。我國學者從財政政策、經濟結構、農業勞動力轉移等多個角度分析了影響農民收入的因素,然而無論何種措施都需要資金的支持,目前我國農村發展所需資金的供給遠遠不足。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金融在政府主導下得到了較快發展,但和我國總體經濟和金融發展水平相比,農村金融發展仍較為緩慢。我國的改革最早始于農村,但是農村的金融改革相對滯后,甚至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制約,農村金融非但沒有提供農村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反而將農村儲蓄用于城市發展,這對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形成了一定制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量剩余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城鎮建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增加了自身的收入。本研究基于農業勞動力轉移的視角,嘗試通過分析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二者之間的關系,找到提高農民收入的途徑。
1文獻回顧
一個經濟體可以通過優化其金融結構來促進經濟發展,經濟的發展又可以使居民收入提高,農村金融也是如此,作為金融體系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農村金融可以通過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農民收入[3]。Greenwood等通過建立動態模型對經濟增長、金融優化、居民收入關系進行了研究,認為金融優化和居民收入增長并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先大后小的倒“U”形關系[4]。Banerjee等通過實證分析發現,金融深化、經濟發展不一定都能促進收入的增長,當金融市場不夠成熟時,金融深化和經濟增長甚至可能抑制收入增長,他們認為成熟的金融市場才能通過促進經濟發展來增加收入[5]。Clark等基于多個國家數據分析了金融深化與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認為經濟結構會影響收入分配,從而間接影響居民收入[6]。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經濟和金融存在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我國學者針對農村金融發展與提高農民收入關系的研究有很多。林毅夫認為不同于城市金融,農村金融存在一定的弱質性,且發展落后于城市金融,這導致了農村地區經濟增長緩慢、收入差距較大、貧窮現象較為明顯[7]。許崇正等從農村信貸、農民受教育水平、農產品價格等方面實證分析了影響農民收入的因素以及這些因素和農村金融發展水平的關系,提出可以通過提升農村信貸水平、農民受教育程度、農產品價格來提高農民收入[8]。溫濤等以1952—2003年度數據為基礎,對我國金融整體發展狀況、農村金融發展和農民收入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我國和其他國家不同,金融發展對提高農民收入產生顯著負向影響,我國農村金融發展過程中存在明顯的結構失衡[9]。楊小玲基于農民收入來源結構,研究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金融服務的發展對提升農民收入的影響認為,農村金融的發展與農民家庭收入具有一定的負相關性,且二者互不為格蘭杰因果關系,農村金融效率能顯著影響農民收入[10]。譚燕芝以1978—2007年數據為基礎,對我國農村金融的發展與農民收入關系進行實證分析,認為農民收入對農村金融發展能產生顯著正向影響,農村金融發展對提高農民收入沒有影響,造成此問題的原因是農村地區金融機構會把當地的儲蓄用于外地發展,而非服務于本地經濟[11]。余新平等以1978—2008年數據為基礎,對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與提高農民收入關系進行實證分析認為,農村存款、農業保險賠付能對農民收入產生顯著正向影響,農村貸款、農業保險收入能對農民收入產生顯著負向影響,農村企業的貸款對農民收入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12]。李明賢等以1990—2009年數據為基礎,使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我國農村金融與農民人均收入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農村金融機構存貸比、農村金融機構從業人數能夠顯著正向影響農民收入[13]。劉玉春等以1978—2012年我國數據為基礎,基于C-D生產函數對農村金融發展與提高農民收入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農村金融發展能夠對農民收入產生顯著正向影響,農村金融規模以及金融效率也能夠對農民收入產生顯著正向影響[14]。
2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民增收的相互影響機制
農村金融發展和農民增收之間可以相互影響,互相促進。農村金融可以為農業生產提供資金來源及金融服務,有利于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帶動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農民收入提高對農村金融發展又具有促進作用,農民收入提高后,儲蓄也會相應增加,有利于提升農村金融機構的資本實力,進而更好地為農民和農村經濟服務,進一步提升農民收入,形成良性循環。
2.1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民增收的影響機制
(1)農村金融的發展可以拓寬農業生產的融資渠道,使農村居民獲得發展規模化、集約化農業的大量資金。由于農業生產周期較長,收益率較低,金融機構開展農業信貸業務的意愿較低,擴大農業生產規模,發展專業化、集約化經營需要大量的資金,農村金融的發展可以通過向農戶融資,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增加農民收入。(2)農村金融的發展可以在改善農業生產基礎設施的同時,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增加農民收入。農村金融服務可以通過為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貸款和保險服務,比如為水力工程提供長期貸款,為大型農具提供質押服務,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提高農民收入。(3)農村金融的發展可以通過為鄉鎮企業提供金融資訊和服務,促進農民非農就業和就近務工,增加農民收入。(4)越來越多的農民選擇從農村金融機構獲得貸款,用于提升自身農業生產技能和知識,進而提高農民人力資源素質。農民素質的提高會產生長期的回報,通過掌握農產品市場動態,使用先進的生產技術,加快農業現代化發展并提高自身收入。
2.2農民增收對農村金融發展的影響機制
農民收入水平較低時,農民有限的收入只能用于維持日常生計,手中的閑置資金較少,對金融服務的需求較小,使得金融機構的涉農業務量較小,農村金融機構的儲蓄量也不高。農村金融機構會選擇減少營業網點和服務人員數量以降低成本,網絡覆蓋率下降和服務水平也會相應下降。農民收入水平提高后,農民手里的閑置資金增多,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增加,使農村金融機構網點數量、工作人員數量增加,農村金融機構得到發展。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時使得農民對保險、理財等金融產品的需求增加,進一步促進了農村金融服務的發展。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還可以增加農村金融機構的吸儲量,增加農村金融機構的資本實力,促進金融機構自身的發展。
由以上分析可知,農村金融發展和農民增收可以互相促進,互相影響,共同帶動農村經濟的發展。
3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民增收關系的實證分析
3.1變量選擇與模型構建
本研究通過引入C-D生產函數來分析農村金融發展和農民收入間的關系,農村的金融發展水平被作為一項投入要素,農民收入作為產出。其表達式如下:
2邊同時取對數處理得到下式:
本研究所建立模型涉及2個方面的指標:(1)農民收入指標;(2)農村金融發展指標。為進一步分析勞動力轉移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將外出務工人員數量作為解釋變量引入模型,最終根據本研究的內容,將以上雙對數模型寫成如下形式:
式中:C為常數項,β表示各自變量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程度,ε為不能被模型解釋的隨機波動。
選取農民人均收入作為收入指標。農村金融發展指標通過農村金融規模、農村金融效率、政府對“三農”的財政支持力度幾個方面加以描述。
(1)農村金融規模。金融的發展與經濟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金融機構的經營運作可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為經濟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和金融服務,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一個地區的金融規模越大,通常這個地區的經濟越發達,居民收入也越高。本研究使用胡俊等的方法[15],用農村地區存貸款之和占第一產業產值比重表示金融規模。
(2)農村信貸比率。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資金的支持,農村也是如此,因此,本研究把農村信貸比率作為農村金融指標之一,用涉農貸款與第一產業產值之比表示。
(3)財政支農力度。由于農業具有低產值、高風險,但對國家不可或缺的特殊性,大多數國家對農業都采取補貼政策。朱湖根等認為,政府的財政支持能夠提高農民收入[16]。本研究將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與第一產業產值之比表示財政支農力度。
(4)農業勞動力轉移情況。農民外出務工現象在我國較為普遍,是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杜婕等選取農村人口總數與第一產業就業人口數之差表示沒有從事農業的農村人口,綜合考慮年齡因素后,使用農村未從事農業生產人口數的一半代表外出務工人數,認為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短期內可以提高農民收入[17]。但該統計方法主觀性太強,因此本研究使用國家權威統計數據,2008年之前的農民工數量來自農業部抽樣調查數據,2008年及之后的農民工數量來自國家統計局數據。雖然外出務工能獲得更多收入,但必須也要意識到農民外出務工會帶來留守兒童、空巢老人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不一定利于社會發展[18]。各變量的說明和標記如表1所示。
本研究以2000—2015年年度數據為研究對象。農民工數據來自農業部和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其他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其中農民人均純收入、農村外出務工人員數量取對數。數據處理使用Excel軟件完成,模型回歸使用Eviews軟件完成。
3.2平穩性檢驗
為保證結果的準確性,防止出現偽回歸,建模前須檢驗數據的平穩性,本研究使用單位根檢驗以驗證數據的平穩性,按照趙進文的觀點[19],分別使用ADF檢驗、PP檢驗做單位根檢驗,兩者結果不一致時,以PP檢驗為準。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
由單位根檢驗結果(表2)可知,原序列在0.05水平上差異均不顯著,各變量的原序列數據不平穩,各變量的一階差分序列均在0.05或者0.01的顯著水平上通過了平穩性檢驗,說明各變量的一階差分序列均為平穩序列,可以進行下一步分析。
3.3協整檢驗
協整檢驗前,使用AIC準則、SC準則配合LR檢驗來判斷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經檢驗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2。本研究使用Johansen方法進行協整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由Johansen檢驗結果可知,特征根的趨勢值、最大值在0.05的統計水平上均存在4個協整關系,因此模型存在協整,各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共關系,可以進行下一步分析,各變量與農民收入關系的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
由回歸結果(表4)可知,農村地區金融規模的系數為正且在0.10統計水平上顯著,農村金融規模(GM)能夠對農民收入(SR)產生正向影響,但效果不明顯。財政支農力度系數(ZN)為正,但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農村信貸比率(XD)和農村外出務工人員(WC)系數為正且在0.01統計水平上顯著,說明農村信貸比率和農村外出務工人數能夠對農民收入產生極顯著正向影響。
3.4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為進一步分析各變量和農民收入間的相互關系,分別用各變量和農民收入作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格蘭杰檢驗可以從統計學的角度來分析2個平穩時間序列的因果關系。各變量與農民收入的格蘭杰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
由表5格蘭杰檢驗結果可以看出,農村金融規模不是農民收入的格蘭杰原因,農民收入是農村金融規模的格蘭杰原因;農村信貸比率是農民收入的格蘭杰原因,農民收入不是農村信貸比率的格蘭杰原因;農業財政支出不是農民收入的格蘭杰原因,農民收入是農業財政支出的格蘭杰原因;外出務工人數是農民收入的格蘭杰原因,農民收入不是外出務工人數的格蘭杰原因。
3.5動態分析
考察完畢各因素和農民收入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后,使用誤差修正模型(ECM)研究各變量的短期波動對農民收入長期均衡的影響。根據前面的分析結果,得到誤差修正項ecm:
誤差修正項ADF平穩性檢驗結果為-5.681,結果通過了0.01統計水平上的顯著性檢驗,因此ecm平穩,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為:
根據誤差修正模型的概念,為保障模型收斂,誤差修正項的系數λ應小于零,ut為白噪音過程。誤差修正分析的估計結果為:
由結果可知,短期內,農村金融規模、農村信貸比率、外出務工人數的變動能對農民收入產生正向顯著影響,財政支農力度對農民收入影響不明顯。均衡誤差項ecmt-1表示一旦農民收入遇到外部沖擊偏離長期均衡狀態后,在隨后若干時期內自動回歸長期均衡水平的機制,均衡誤差項的系數為 -0.104,說明農民收入回到長期均衡狀態的速度為0.104個單位,表現出較弱的對長期均衡關系的誤差修正效應。當ecmt-1<0,農民收入向下偏離長期均衡水平時,ΔSR會大于零,導致SR變大,從而向長期均衡值回歸;當ecmt-1>0,農民收入向上偏離長期均衡水平時,ΔSR會小于零,導致SRt變小,從而也向長期均衡值回歸。
分析完長期均衡關系后,使用脈沖響應函數研究農民收入受到外部沖擊后的變化情況。脈沖響應函數描述的是給系統1個單位的正向沖擊后,系統所做出的動態反應。本研究分別研究了農民收入受到自身以及各自變量1個單位沖擊后的反應,脈沖效應的輸出結果如圖2至圖6所示。其中橫軸表示沖擊的滯后期,縱軸表示農民收入對沖擊的反應程度,實線表示農民收入對沖擊的反應路徑。
由圖2至圖6可知,農民收入受到農村信貸比率、外出務工人數、自身的正向沖擊后,會有所提高。農民收入受到自身沖擊后,當期即做出反應,有所提高,隨后開始調整,幅度減弱,在第2期后逐漸趨于穩定并在高于初始水平的位置穩態運行。農民收入受到農村金融規模正向沖擊后,當期即有所提高,但隨后沖擊影響振蕩減弱,最終回到初始水平,農村金融規模變動對農民增收幾乎沒有影響。農民收入受到農村信貸比率沖擊后,即期沒有響應,隨后逐漸調整,在4期之后逐步達到穩態,在高于初始水平的位置穩態運行,農業生產通常周期較長,從農村信貸比率的提高到農業產值增加、收益提高,最終到農民收入的提高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農民收入受到財政支農沖擊后,除即期有所改善外,之后并不利于農民收入的提高,說明我國財政支農的效果不佳。外出務工人數對農民收入的沖擊類似于信貸比率,受到沖擊后,逐步調整到高于初始水平的位置穩態運行,說明外出務工人員的工作熟練度直接影響他們的收入水平,工作熟練度越高,收入水平越高。
5結論及對策
本研究選取2000—2015年我國農村相關數據作為研究對象,從理論和實證2個方面分析了農村金融發展、農業勞動力轉移與農民增收間的關系,實證結果與理論分析一致,農村金融的發展和農民增收能夠相互影響,具體結論如下:
(1)農村金融規模的變動對農民增收影響有限,農民收入是農村金融規模的格蘭杰原因,反之不是。農民收入提高,其儲蓄也會隨之增加,使農村金融規模變大,但農村金融規模的變動對農民增收作用有限,這說明我國農村存在資金外流現象,金融機構吸收當地農民存款后,主要用于外地的發展。
(2)農村信貸比率的增加對農民增收能產生顯著正向影響,農村信貸比率是農民收入的格蘭杰原因,農村信貸比率的增加能夠推動農村經濟發展,進而增加農民收入。但農民收入并不是信貸水平的格蘭杰原因,說明農業信貸并不會因為農民收入水平較低而增加,我國農村信貸仍存在區域不均衡現象。
(3)財政支農力度對于農民收入不產生顯著影響,農民收入是財政支農力度的格蘭杰原因,反之不是。近年來,我國對農村的財政支持力度加大,但從本研究結果看,對于提升農民收入的效果不明顯,國家雖然對收入較低的貧困地區給予了大量財政支持,但并沒有顯著提高農民收入,政府通常因為一個地區過于貧困而給予財政扶持,但財政扶持對于農民增收效果不佳。
(4)外出務工人數對農民收入能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外出務工人數是農民收入的格蘭杰原因,反之不是。通常低收入地區的農民會因為本地區的工作機會少,收入水平低選擇外出務工來提高收入,高收入地區的農民通常外出務工人數較少。
(5)農民收入遇到外部沖擊偏離長期均衡狀態后,表現出較弱的誤差修正效應。農民收入受到農村信貸水平、外出務工人數和自身的正向沖擊后,會有所提高。農民收入受到財政支農的沖擊后,當期有所改善,但長期不利于農民收入的提高。農民收入受到農村金融規模的沖擊后,當期有所改善,長期效果不明顯。
針對本研究結論,為促進農村地區經濟發展,提高農民收入,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1)創新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第一,根據各地實際情況,拓寬金融服務范圍和領域,簡化質押、信貸、放款流程,創新農村金融服務。第二,構建新型農村金融服務網絡,不斷完善金融服務設施,制定科學合理的農村金融機構布局規劃,支持金融機構進駐農村,增加惠農服務范圍和民生金融產品,利用稅收、財政等多種手段,建設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加快農村金融服務設施建設,根據居民分布等實際情況,增加自助服務設備。第三,統籌推進布局合理、高效有序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不斷建設符合我國國情的農村新型金融機構,探索、創新符合農村地區的金融經營管理機制,充分發揮各涉農金融機構的比較優勢,打造布局合理、競爭有序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
(2)整合拓展農村金融服務領域。第一,以我國目前農村現狀為基礎,加強農村金融發展對提高農民收入的促進作用,出臺涉農信貸的財政扶持政策,使政府財政和農村金融機構共同支持涉農信貸的發展。第二,創新惠農服務及金融產品的研發,農村金融機構可廣泛吸收農民的閑置資金、社會投資進入農村金融市場,壯大自身資金實力的同時,激發農村地區金融市場的競爭活力,通過增強惠農支持力度,促進農村金融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提高。第三,大力發展和推進農村高科技及信息技術的開發應用,移動通訊技術、在線支付業務在農村金融領域的應用和普及,可以為農村金融和經濟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農村金融機構可以通過開展網上銀行及信貸業務,實行一體化網絡化經營,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各金融機構重復建設、分布不對稱、無效率運營、金融服務嚴重缺位的矛盾,同時也減少了農民對機構網點的過度依賴,足不出戶即可享受金融服務。
(3)提高農業財政補貼效率。第一,加大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農業財政投入力度,優化農業財政支出結構,增加基礎設施以及農業現代化技術的投入,加大農業現代化、規模化、集約化的投入,加快從小農經濟向農業現代化轉變的進程,提升第一產業全要素生產率。第二,減少農業財政支出及補貼的中間環節,改變現有分散的農業投入機制,整合各項支付支出,提高政府農業支出的使用效率,加強農業支出資金的監管,切實做到每一筆資金去向的透明。第三,建立農業財政支出效果評價體系,通過科學合理的評價指標提升資金使用效率,切實保證每一筆農業財政支出都能用到刀刃上。
(4)創造當地就業機會,提高農民當地就業積極性。第一,政府完善扶持政策,加大扶持力度,通過市場化運作建立起促進農民當地就業的長效機制,提高農民當地就業的積極性。第二,打造解決農民當地就業問題的服務平臺,方便農民就地找到工作機會,可通過定期舉辦招聘會,建立專門的農民農業人力資源市場,開通農民就業信息網,開設當地農民就業微信平臺等方法,為農民就業提供便利。第三,建立和完善農民維權服務和維權監督機制,對于侵害農民權益的現象絕不姑息,通過營造良好的就業環境解決農民后顧之憂,吸引當地乃至外地農民前來就業。第四,政府應加強農民創業培訓,響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號召,鼓勵有技術、有想法、有資金實力的農民創業,并給予一定的政策、稅收優惠。通過鼓勵農民創業,創造就業崗位,解決當地農民就業問題。通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領其他人共同走向富裕。
參考文獻:
[1]林毅夫. “三農”問題與我國農村的未來發展[J]. 求知,2003(3):23-26.[LM]
[2]白欽先. 金融結構、金融功能演進與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歷程[J]. 經濟評論,2005(3):39-45.
[3]高艷. 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績效分析[J]. 金融研究,2007(12):242-246.
[4]Greenwood J,Jovanovic B. Financial development,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1076-1107.
[5]Banerjee A V,Newman A F.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3,101(2):274-298.
[6]Clarke G R G,Xu L C,Zou H F. Finance and income inequality:test of alternative theories[J]. Ssm Electronic Journal,2003,72(3):578-596.
[7]林毅夫. 金融改革與農村經濟發展[R]. 北京: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2003.
[8]許崇正,高希武. 農村金融對增加農民收入支持狀況的實證分析[J]. 金融研究,2005(9):173-185.
[9]溫濤,冉光和,熊德平. 中國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J]. 經濟研究,2005(9):30-43.
[10]楊小玲. 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結構的實證研究[J]. 經濟問題探索,2009(12):71-77.
[11]譚燕芝. 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之關系的實證分析[J]. 上海經濟研究,2009(4):50-57.
[12]余新平,熊皛白,熊德平. 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J]. 中國農村經濟,2010(6):77-96.
[13]李明賢,葉慧敏. 我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的實證研究[J]. 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14(4):88-97.
[14]劉玉春,修長柏,賈鳳菊.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的實證分析[J]. 農村經濟研究,2016(2):63-67.
[15]胡俊,許正松. 農村金融規模、金融結構與農民收入——基于中部六省的實證研究[J]. 企業經濟,2015(11):188-192.
[16]朱湖根,萬倫來,金炎. 中國財政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項目對農民收入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J]. 中國農村經濟,2007(12):28-34.
[17]杜 婕,霍 焰.農村金融發展對農民增收的影響與沖擊[J]. 經濟問題,2013(3):97-102.
[18]段成榮,楊舸. 我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研究[J]. 人口研究,2008,32(5):15-25.
[19]趙進文. 面板數據建模理論的過去、現在與未來[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9(9):149-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