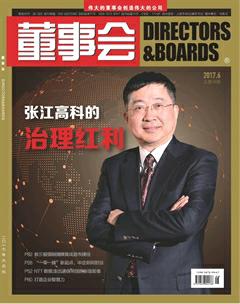淘金全球公用事業并購潮
陸浩文
中國公用事業行業應實現從化石燃料到可再生能源的資產多樣化轉型,同時需要調整商業模式以適應正在緩慢放松管制的市場
2016年,全球公用事業與能源基礎設施領域的并購交易總額創下歷史新高,交易總額達到3290億歐元。其中,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并購活動是主要驅動力之一。在美國和加拿大,行業的整合帶動了幾筆大型兼并。而亞洲的公用事業企業在跨境并購中的表現越來越活躍。在未來幾年,七大根本原因將引發買家和賣家之間的并購交易:綜合公用事業公司產品組合協同效應的下降導致資產剝離;國有企業的財務需求觸發資產剝離;金融投資者的首輪撤資(達到了投資周期的末端);公用事業公司產品組合變化(比如受脫碳趨勢和可再生能源增長推動);持續走低的資本成本刺激金融投資者更強地走向市場;主權財富基金和國有企業越來越注重地緣戰略;新能源業務領域的風險投資和增長型投資。
投資者和公用事業公司都需要做出艱難的選擇,利用并購活動開發新的業務模式,推動監管和競爭壓力日益增加的能源市場的價值。
其中,由于交易價值鏈各環節之間的協同效應有限,因此,公用事業公司紛紛轉變原有的投資組合,專注于某些業務(通常是無碳業務)或地區(通常是公司的核心地區或本地區,但是中國企業熱衷于將資金轉移到國際基礎設施資產上)。非常正確的是公用事業行業正專注于那些擁有更強未來成長潛力的領域,如零售或可再生能源,這些領域的交易率正在顯著提升。
金融投資者作為公用事業行業戰略和管理具有影響力的股東,他們對客戶資金的投資期通常為2至5年,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也可能延長到10年。這些金融投資者更追求短期或中期的戰略。他們對能源基礎設施的早期投資已經達到投資周期的末端,將促使第一波投資退出潮的出現。
實際上,投資者在公用事業行業重塑過程中越來越發揮著積極作用。受金融投資機構影響,全球公用事業與能源基礎設施領域正因各種不同原因經歷巨大變化。這一趨勢在歐洲尤為顯著。在歐洲,金融投資機構對并購交易的參與與日俱增,打破了歐洲原本比較完整的電力市場產業鏈。而與之相反,在美國,公用事業企業市值的反彈激起了新的兼并與整合浪潮。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能源計劃可能重新將重點轉移到傳統能源基礎設施上,從而可能進一步強化現有公用事業企業和基礎設施公司的市場價值。在中東、印度和中國,跨境交易逐漸增加,原因是當地政府致力于打造全球性的基礎設施資產組合。
受到全球公用事業企業領域這種新的兼并與整合浪潮的影響,亞洲在相關跨境并購中也會越來越活躍。這一并購趨勢將給中國公用事業企業帶來怎樣的影響?
自2013年以來,中國對歐盟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增長了三倍。歐洲開始成為中國的主要投資目的地;在對公用事業基礎設施進行投資的同時,中國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服務合同,比如英國的Hinkely Poiint C核電廠、羅馬尼亞的發電廠。
對中國而言,中國公用事業行業應實現從化石燃料到可再生能源的資產多樣化轉型,同時需要調整商業模式以適應正在緩慢放松管制的市場。傳統的中國公用事業企業已經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是,由于空氣質量和環境的挑戰,還有更多需要做的。除了陸上風電(目前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資領域)之外,還要擴展到太陽能發電、海上風電、增加核電與水電等領域的占比。隨著與客戶接觸的增加,中國企業銷售及交易能力需要得到增強。這意味著他們需要通過數字化來優化流程和成本,提高與客戶互動的有效性。同時,著眼于全球并購交易將能夠接觸到國際領先的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