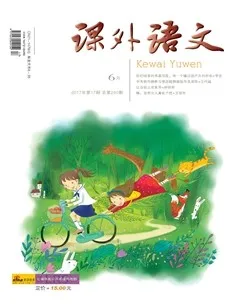未登山頂
郭響文
林清玄說過:“見地是為了提升境界,實踐是為了印證境界,前者是未登山頂而知道山頂有好風光,后者是一步一步地登山,一定要爬上山頂的時候,才能同時匯流,豁然貫通!”他的意思是:學識需要自己的實踐和感知才有分量。
比如兩個人去登山,第一個人見到山中都是石子路就退了回去,對朋友美其名曰“登山了”。第二個人進入山林后,便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不知何時,人們突然發現,萬丈山巔上有一個偉岸的身影在眺望遠方。第一個人得到了虛偽的光榮,第二個人獲得了心靈的充實。
以此來比喻世上的學者,一批人悶著頭朝山頂沖,另一批人卻在途中,要么返回山下,要么和身后的山景合影算是見證。第一批學者將自己的身心全部浸到了學術的海洋中,提升并印證了自己所學,因而他們的人生富有幸福,途中的坎坷也就輕如浮云了。博學如陳寅恪,游學歐美無一個學位,卻位列清華四大導師之一,狂狷的劉文典,對陳寅恪也是“十二萬分的敬佩”。他潛心治學,提攜后進,晚年眼盲,右腿骨折,但依然一心向學,只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學術精神,先生用其一生的事跡很好地闡釋了實踐的價值。
反觀當代某些所謂的知名學術專家,為了浮名而弄虛作假,為了利益而頻繁推出學術著作。即使登上了山頂,狹窄的視野也會被浮云所充斥,生來死去,靈魂不變的深邃,豈不是很可笑么?“固時俗之工巧兮,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為度。”本來淳樸干凈的學術領域就這樣被這些蛀蟲搞得烏煙瘴氣,竟使一些本欲潛心登山的年輕人迷失在浮云里,茫茫然一片混亂。這時,原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唯昭質其猶未虧”“獨好修以為常”的品性就更難能可貴。
未登山頂,傾于登山之道,即使身處淤泥,依然隨心意,樂觀的精神又給登山者提供了精神的支柱。“文革”期間,王大珩被打成“特務”,核專家變成了掃廁所的大爺。鄧小平同志為其平反后,他丟下掃把,第一時間沖進了圖書館。他說:“功課丟下的太多。”因為傾心于山路,所以能帶領追隨的心靈遨游。《亮劍》之所以成功,不同于其他抗戰神劇,在于它的情真意真,在于人真物真,更在于劇組演員、攝影、監制等所有工作人員“舍己入真”的精神。
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正如《口袋妖怪》創作人表述的:山頂上仍有階梯,通向那更巔絕的旅程。
(指導老師:陸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