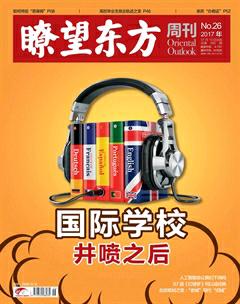杭州問茶
林之
一桌一椅一杯茶,草木之間天地寬
5月初的一天,西湖的茶山上,一字排開幾十只大鐵鍋,茶村的炒茶高手們在這里一決高下,展示手工炒茶的傳統技藝。
這已經成了春天里約定俗成的儀式,成了杭州茶山上的標志性場景。
龍井茶是手工炒出來的,幾百年來一直如此。
西湖龍井茶要求每片茶葉都必須“直、平、扁、光”,這種特殊的形態就是靠炒茶人一雙粗糙的大手調制出來的。而龍井茶四絕“色翠、香郁、味醇、形美”中的色與形,就取決于炒制工藝,同樣的新鮮茶葉,不同的炒制手藝,結果會大不相同。

采茶工人在杭州梅家塢村一茶園里采摘龍井茶
問茶古道
龍井古寺名留史冊,龍井泉水依然清澈,而十八棵御茶樹就像一部熱鬧的古裝劇。
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曾六次到杭州,其中四次親臨茶山,觀看采茶、炒茶。乾隆喝了龍井茶,高興,就要寫詩,這位愛寫詩的皇帝居然寫了30多首關于龍井的詩。
據說第四次來時,他還親自下馬,在溪邊的茶樹上采摘茶葉。皇帝采過的茶樹,自然要保護起來,把那十八棵茶樹圈起來,人稱“御茶園”。這塊茶園至今仍保留著,成了旅游景點。
每次去龍井,下山必走“問茶古道”。
如今去龍井的道路四通八達,汽車可直抵十八棵御樹。當年龍井山深林密,嶺高路險,乾隆皇帝去時雖有十八抬大轎,可也不會舒坦。
龍井茶室外公路旁斜下一條山徑,林茂草盛,濕漉漉的青石板上,青苔畫出縫隙。一拐彎,便不聞車囂,只有水聲,山徑旁一條小溪,叮咚擊石而下,古稱“虎溪”。
不一會便下到山谷,有一跨徑古亭,名“過溪亭”。當年乾隆游龍井,喝過茶作完詩又提寫“龍井八景”,其中就有“過溪亭”。
關于“過溪亭”,還有一個雅致的故事。
900多年前,龍井寺來了一位辨才法師,他建了一間遠心庵,周圍種滿竹子,獨處其中取靜,人們尊稱“遠公”。
辨才原本是想在此靜度晚年,可是擋不住眾人膜拜,人們慕辨才大名,不辭勞苦跋山涉水地前往龍井,龍井寺就此被“開發”。辨才好靜,可是又不便將人拒之門外,就立了一條規矩:殿上閑談,最久不過三炷香;山門送客,最遠不過虎溪。
不久后,蘇東坡來杭州做太守,聽了辨才大名就來探訪,兩人相見恨晚,留宿長談何止三炷香。
第二天,辨才將蘇東坡送出山門,邊談邊沿著虎溪下山,談到快心處,不覺過了虎溪橋,旁邊人大急:“遠公遠公,送客已過虎溪矣!”兩人駐足,相顧大笑。這就是:虎溪留一笑,千載尚聞聲。
為將此佳話記錄在案,后人特地在虎溪上建一亭,名為“過溪亭”。
小溪繼續向下流淌,兩旁山峰環峙,山谷里愈發幽靜。一條石板古道,一邊是清澈山澗,一邊是漫坡茶園,這“問茶古道”,連杭州本地人都鮮少知道,一路走來,只碰到一位茶農,正在整理茶樹。
茶為國飲
龍井茶清淡悠遠,茶鄉的茶味卻越來越濃。
問茶古道的盡頭,有西湖雙峰村的幾百畝茶園,春天里,大片茶園百般蔥蘢。
茶園深處有中國茶葉博物館,磚紅色的屋頂點染在茶樹間,江南民居的建筑風格融入周圍環境,顯現出一種中國傳統文化的隨意與清雅。2005年,中國國際茶文化研究會授予杭州“中國茶都”稱號,此后,每年春天杭州都要舉辦西湖國際茶文化博覽會,“茶為國飲,杭為茶都”成為春天的主題。

炒茶師傅在“西湖龍井茶炒茶王大賽”上競技
上世紀80年代以前,還少有人說起“茶文化”這個詞,而今天,“茶文化”成了杭州人嘴里的普通詞匯,人人能說上幾句茶是什么。
茶是什么?這也是中國茶葉博物館講述的故事題目。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在喝茶;白宮有一官職專事品茶以鑒定各類進口茶葉,那官員的熟練程度令人驚嘆;英國為維護其茶葉專利而制定的茶葉條例,曾促發波士頓茶黨案和美國獨立戰爭;17世紀凱瑟琳皇后成為英國第一位飲茶的皇后,200年后,英國人午后用茶點成為習慣;日本人的茶道,至今仍是引人注意的儀式。而茶的源頭,在中國。
《茶經》里說,“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傳說神農氏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有山泉順著茶樹的枝葉滴下,神農喝下得以解毒。這個傳奇故事記載于中國的一本古藥物書《神農本草》上,那是茶葉在中國歷史上的首度亮相,從藥用開始,進入中國人的生活。
唐朝開元年間,湖北某寺廟里有一個小和尚逃走了,他就是后來成為中國茶圣的陸羽。他如果不是自小在寺廟里煮茶,很難說必定會拒絕仕途一心事茶;倘若他不做茶學問,恐怕中國的茶文化將無人可道。
陸羽的《茶經》是第一部茶著,第一次將飲茶提升到審美的、文化的境界,從那以后有了100多種各類茶書。
唐宋600年是茶葉生產與消費最興盛的時期,飲茶成了文人雅士的風尚。飲茶要講究環境,苛于對象,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風清日和之時,備幾樣精致典雅的茶具,當然此中更重要的是茶葉清淡悠遠的自然屬性,于是便造就了一種脫俗而深幽的意境,詩由此出、文以此潤便不奇怪了。
飲茶小史
起初,茶是煮著喝的,古人在茶里加上姜、棗、鹽等一起煮,那時的茶是一種食品。唐以后去掉了其他東西,單單煮茶,茶才成了飲料。
而茶的喝法也越來越講究,陸羽的《茶經》讓我們知道了古人是怎么喝茶的。煮之前先要烤茶餅,把水氣蒸發了,再將茶餅碾成細末,然后才是煮,煮完了還得濾,很麻煩。
在陸羽的書里,光是煮茶飲茶的用具就寫了一章,古代詩人邀朋友去郊游飲茶,要提一個大竹籃,里面都是喝茶的物什,古人對煮茶的講究令人望洋興嘆。
到了宋朝,這茶又喝出了游戲,名曰“斗茶”和“分茶”。宋代的茶已經不是煮著喝了,而是將茶葉研成碎末后,裝在大瓷碗里用開水沖,這一沖沖出了技術,沖出了藝術。一手向碗里注水,一手拿一柄竹制的茶筅攪動,配以動作的輕重緩急,茶水的形色各不相同,這就分出了茶葉和技藝的優劣,于是有了“斗茶”,從官家一直斗到民間,等到了禪院,這斗茶就成了一套程式化的禮儀。
到了南宋,杭州街頭則流行“分茶”,是純粹的消遣游戲了。那時的杭州,茶不僅是喝的,還是玩的。
1186年春天,詩人陸游來到京城臨安(今杭州),原本以為這下有了殺敵立功報效國家的機會,也不知道是他的詩名太大了,還是皇帝根本就沒想抗擊外敵收復國土,總之他來到京城后無事可做,整日里也就是寫詩戲茶,他在詩里不無牢騷地寫道:“矮紙斜行閑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細乳指的就是茶湯,所謂分茶,就是對茶湯的一種玩賞,沸水沖擊茶葉,再經竹筅攪拌,茶水表面便會變換出形形色色的水紋,似花鳥、山水、人物等等,技術好的人可以隨意分出各種形象。
那時的臨安城,分茶不僅是文人的游戲,民間也玩分茶,甚至一些雜耍藝人也練有一手分茶的手藝,作為節目當眾表演。
明代以后的喝茶就和今天差不多了,抓一撮茶葉放入茶杯,開水沖泡。但是泡茶時很注重禮儀,比如“鳳凰三點頭”,水壺上下高低舉三回,以示敬意。
喝茶講究慢慢品,俗話說,“三分解渴七分品”。《紅樓夢》里妙玉用5年前落入梅花花瓣的雪水精制的茶,只肯施于知音黛玉寶玉,那是品嘗其精妙。
涼茶能解渴的功能也十分重要,《水滸》中,宋江坐在路邊茶館里大喊:“茶博士,將兩杯茶來!”這是海飲解渴的。
這茶喝到這會兒,形式越來越簡單,內容卻越來越深邃,茶與禪、儒、文學、風俗都有了密切關系,中國人喝茶,喝出了精神,喝出了文化。
一桌一椅一杯茶
杭州人一有空閑就喜歡“坐茶室”,或呼朋喚友,或兩兩相對,甚至一人發呆也是好的。
西湖邊到處是茶室,龍井茶的主要產地龍井村、梅家塢,沿街村民幾乎家家開了茶室,西湖周邊茶山上,只要足跡能到之處,就有茶室。
杭州老街河坊街上有老茶館,不是店老,是喝茶的方式老、環境老。從街上走過,那老茶館門口一把巨型大茶壺最引人注目,古色古香的造型,微微傾斜地注下水來,一時古意飛濺,不用吆喝就進門了。
木結構,二層樓,臨街,坐在八仙桌旁,打開木格子窗戶,街上的一切都在眼里。“茶博士”過來了,對襟布衫,瓜皮小帽,一把銅茶壺嘴長一米多,“關公巡營”、“韓信點兵”,那壺里的水高沖入杯,竟然滴水不落杯外。然后,悠然一句“客人慢用”,一個轉身飄然下樓。聞著茶香,看著街景,十分愜意,全然一幅老杭州的寫意畫,端的是民風淳淳。
早在明代,杭州的大街坊巷就遍布茶館,據《杭州府志》記載,明嘉靖年間,有姓李者,旬月之間就開了五十余所茶館,且生意好得不得了。
清代吳敬梓《儒林外史》中寫到吳山,“一條街,單是賣茶的,就有三十多處”。這樣的茶館是屬于老街坊的,茶館里的方桌很舊了,但擦拭得很干凈,發出老木頭的光澤。茶館老板認識幾乎每一位客人,知道他們的喜好,知道他們的習慣,甚至知道他們邊喝茶邊聊些什么。在綿長的日子里,這樣的茶館一直點綴著杭州人的生活。
吳山上至今多茶室,且多露天茶室,每天聚滿老年人,五塊錢一杯茶,可以坐一天。這里的茶客都是每天見面的老熟人了,大家在一起一邊搓麻將,一邊說著“老底子如何如何”。他們說著道地的杭州話,有些字詞在高層辦公樓里已經消失了,只在這樣的茶館里還活著。老人們就在這些簡易實惠的老茶館里,安逸地消磨著夕陽時光。
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杭州突然冒出了許多精致優雅的新茶館,這些茶館裝修講究,大多是溫柔敦厚的傳統模樣,再綴以玲瓏的江南景物,有輕輕的古箏伴隨,穿中式裙衫的女孩端茶走過就像一道風景,明明都是年輕熱鬧的茶客,卻透著古典江南的氣息。
這些新茶館,有的擅長茶藝表演,講究泡茶的技藝,推崇茶文化;有的裝飾喜好古物,古家具古茶具古瓷器古飾物,在溫暖的柔光下靜默;有的則是一派庭院氛圍,備上文房四寶,到此品茗之暇還可即興潑墨……但是,人們還是更喜歡西湖邊的茶室,別的不說,就這么臨湖一坐,就什么都不用想了。
坐在西湖邊喝茶,是杭州人最普通也是最熱愛的休閑方式。無論哪一天,你走過西湖邊的茶座,都可以看到茶客:一桌一椅一杯茶,草木之間天地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