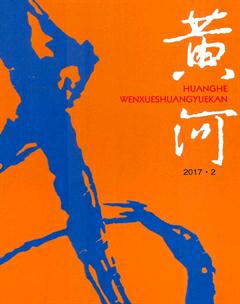與詞語搏斗
趙勇
《虛掩的門》(北岳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是山西青年詩人悅芳的第一部詩集。讀里面的詩之前,我先翻閱的是她為這本詩集寫成散文的后記。她說:“我曾不止一次,迷失于文字的叢林。不知是把瑣屑的生活寫成詩,還是把詩變成實(shí)實(shí)在在的生活。我時(shí)常發(fā)現(xiàn)一種緊迫感旋轉(zhuǎn)在我的指尖,不停地跳躍,我知道,美在用這種方式召喚我。”——這是一個(gè)不斷被詩神眷顧的人,我想。滾滾紅塵中,還能與詩神為伍,至少說明她的頑強(qiáng)和執(zhí)著,她還堅(jiān)守著心中的那份詩意。再往下看,就發(fā)現(xiàn)了她寫下的這段文字:“詩,不過是每個(gè)人靈魂深處的一個(gè)固有情結(jié),每個(gè)人身上都縈繞著一種天生的自然的詩意。只是在人生的路上,有的人放逐了詩歌,有的人卻堅(jiān)定地要抵達(dá)詩歌的本質(zhì)。詩與我們,近在咫尺卻遠(yuǎn)在天涯。它在時(shí)間之中,和我們平行,之間的距離肉眼看不見、摸不著,只能感應(yīng),語言是它的本質(zhì)。通往語言之途,就是和經(jīng)驗(yàn)搏斗之途,每個(gè)詩人都筋疲力盡。”
說得真好!而我也從中讀出了弗洛伊德和海德格爾的某些意味。因?yàn)榍罢咴?jīng)說過一句名言:“每一個(gè)人在內(nèi)心都是一個(gè)詩人,直到最后一個(gè)人死去,最后一個(gè)詩人才死去。”后者則寫過《在通向語言的途中》一書,里面探討的是語言、經(jīng)驗(yàn)與詩歌的關(guān)系。那句廣為人知的命題——“語言是存在之家”——就是他在此書中思考的一個(gè)結(jié)晶。
這么說,悅芳讀過海德格爾?我覺得應(yīng)該讀過。或者至少,她是熟悉海德格爾的許多論述的。帶著這樣一種“前理解”走進(jìn)這本詩集,果然也就發(fā)現(xiàn)了海德格爾所謂的“思”與“詩”的許多痕跡。
這部詩集分為五輯,分別命名為“囚禁”、“對(duì)話”、“時(shí)光”、“存在”與“幻象”,把它們串在一起看,那里面就有了一種濃濃的哲學(xué)意味。或者也可以說,她選中的每個(gè)詞語似乎都是那些大思想家(比如加繆、巴赫金、伯格森、海德格爾、薩特、拉康、貢布里希等等)須窮其一生苦思冥想的重要范疇。在這些范疇之下,是詩人時(shí)而寫得顯豁但更多的時(shí)候卻讓人略感神秘的詩句。顯豁者中,我首選《我哭了》:
八歲那年。父親對(duì)我說/你該上學(xué)了/我從他手中接過書本、鉛筆、三角板/我上學(xué)了。父親卻走了/我沒有哭
二十八歲那年。母親對(duì)我說/你該成家了/我從她手里接過尺子、剪刀、針和線/我成家了。母親也走了/我沒有哭
今天,我三十八歲了/沒有人再對(duì)我說什么/家鄉(xiāng)的紫荊芥也該成熟了吧/想著想著/我哭了
這是一首明白如話的詩。在這種樸素的表達(dá)中,我們除能讀出一種無法遣懷之情外,還能讀出詩人的一種創(chuàng)傷經(jīng)歷和傷痛體驗(yàn)。記住她的這種經(jīng)歷與體驗(yàn),我們?cè)偃プx她的一些詩時(shí)便不會(huì)感到突兀。那是作者創(chuàng)傷記憶的一次次發(fā)作,以及發(fā)作之后借助于詩歌的一次次治療。例如:“春天也長(zhǎng)不出嘴唇/雨,是清明最憂傷的語言/把耳朵貼近墓碑,期待一場(chǎng)/隔世的對(duì)話。飛舞的黑蝶/喚醒過往的歲月”(《隔世的對(duì)話》)。
我從悅芳的創(chuàng)傷記憶談起,是想說明我對(duì)這部詩集的一個(gè)總體感受。在許多首詩中,無論她寫到了什么,那種語調(diào)都是低回甚至壓抑的,它們仿佛帶人走向一個(gè)下行的礦井之中,眼前是越來越濃的黑暗,還有黑暗帶來的各種生理反應(yīng)和心理感受。于是,她的詩中常常出現(xiàn)孤獨(dú)、憂傷、黑夜、死亡、緊張等等心緒或意象,它們相互指涉又彼此映照,讓這本詩集呈現(xiàn)出一種特殊的現(xiàn)代性意味。如此想來,創(chuàng)傷記憶是不是它們的發(fā)動(dòng)機(jī)?或者,它們是不是創(chuàng)傷記憶結(jié)出的一枚枚青澀或成熟的果實(shí)?
這是我所無法確定的。我能確定的是,為了這種心緒和意象,詩人似乎一直處在一種焦灼和搏斗之中——因焦灼而搏斗,或者是為搏斗而焦灼。而這種搏斗感又突出地體現(xiàn)在她與語言、詞語、文字的較量中。
可以以她的幾首詩略作說明。
有一首詩名為《詞語即夢(mèng)境》。詩人寫道:“總想將你植入詩歌,種進(jìn)夢(mèng)里/又一次次把你剔除/驅(qū)逐出夢(mèng)。語言與情感的角力/難分勝負(fù),緊張、對(duì)立/無休無止。拒絕你又親近你/你的誘惑在我的耳畔/低語。它越過界線的黑暗/發(fā)出呼叫、呻吟、歡唱、傾訴/在無法觸及的地方閃爍,無處不在/又無跡可尋”。按照我的理解,這里記錄的是一次詩人與詞語搏斗的過程。在她的描述中,詞語就像夢(mèng)境那樣似有若無,朦朧美妙,她在用力地捕捉著,以便尋找到情感的對(duì)應(yīng)物,卻又不斷撲空。最終,“在一個(gè)很稀有的時(shí)刻/有一行詩的第一個(gè)字/在它們中心,形成/詞與夢(mèng)堅(jiān)硬的內(nèi)核/脫穎而出”。這就意味著經(jīng)過這番較量,語詞終于浮出水面,而詩人也成了勝利者。
還有一首叫做《傾聽一種聲音》,我把它全部征引如下:
在時(shí)光黑下來的時(shí)候/低伏于蟲鳴花香,傾聽/一些故事情節(jié)/與某個(gè)詞語相遇的聲音/這是柳林的夜晚/幸福就像那些花兒/我叫不出名字,但它們一直在生長(zhǎng)
明月高高在上。小路沒入灌木叢/我們走著,說著/重新安排內(nèi)心的秩序/語言在路上,追逐或逃逸/呼吸一陣緊似一陣。石頭沉默/風(fēng),仿佛是今夜的中心/輕輕啃噬我寄居的身體/時(shí)光突然黑下來的時(shí)候/在一種聲音里/我找到了落葉一般的存在
詩中呈現(xiàn)出一種奇特的感覺。可以想象這是詩人與友人在一次漫游之中的閑聊。詩人在傾聽著故事的講述,但是故事情節(jié)又撞擊到了某個(gè)詞語。在這里,詩人顯然是通過特定的語詞感受著那個(gè)故事的脈絡(luò)或走向。而一旦語詞乃至語象被喚醒,故事便有了新的理路。大概這便是“內(nèi)心的秩序”需要重新安排的緣由。“語言在路上,追逐或逃逸”一句,表達(dá)得尤其奇妙。它既可以理解成講述者的語言,更可以理解成是不斷被激活或喚醒的詩人的內(nèi)心語言,就像魯利亞描述的“句法關(guān)系較為松散、結(jié)構(gòu)殘缺但都黏附著豐富心理表現(xiàn)、充滿生命活力的內(nèi)部言語”那樣。在對(duì)他者故事與自己心音的不斷傾聽中,“我”找到了自己的“存在”。但這種存在又很不穩(wěn)定,因?yàn)樗瓮淙~,是一種飄零的意象。至此為止,詩人似又完成了一次通過語詞捕獲詩意的過程。
我還想提到一首名為《文字三部曲》的詩歌。在這首詩中,詩人先是感受著“文字的溫度”,其中的詩眼在于,“生命的四季在五指并攏/手心,始終握不住/一把字詞的溫暖”。在這種情境中,詩是人焦灼的。而到第二章中,詩人已可以“借文字取暖”:“在最后,接近輝煌的灰燼中/我必以微弱的喘息/用文字的方式將自己/點(diǎn)燃成/觸痛的火焰”。這似乎可以理解成一種鳳凰涅槃似的放手一搏。而經(jīng)過這番搏斗,文字已“變成呼吸”:“多年前語言的光輝/睜著石頭的眼睛/在向日葵的鏡子里/佇立成喋血的夕陽/以輕描淡寫的面具/深藏唯一的結(jié)局”。或許,“當(dāng)文字變成呼吸”只是詩人的一種想象,但這已是一個(gè)大團(tuán)圓結(jié)局了。因?yàn)槲淖忠只蛘Z言已在自己手中變得馴服,它不再外在于我,不再是抓不住的物件,而是與我的知、情、意融為了一體。
把悅芳的這幾首詩集中呈現(xiàn)如上,是想說明我的一個(gè)感受:許多時(shí)候,我們都生活在一個(gè)庸常的世界,了無詩意。但是,在某個(gè)場(chǎng)合、某個(gè)瞬間或某種情境之下,我們又確乎感到了詩意的襲擊。或許那只是驚鴻一瞥,卻至關(guān)重要,因?yàn)槟菐缀蹙褪俏覀兇嬖诘睦碛伞H欢胀ㄈ藢?duì)這種詩意的光顧是毫無辦法的,他們只能任它來去匆匆,事如春夢(mèng)了無痕。而詩人卻必須抓住這個(gè)瞬間,把它咽染成一片初春的原野。這時(shí)候,語詞便成了關(guān)鍵。也就是說,在日常話語之外,能否找到最適合這種詩意的語詞,以及與此相伴的語象和意象、旋律和節(jié)奏,就成了詩人必然經(jīng)歷的重大事件。從古至今,真正的詩人都在與語詞搏斗,他們上天入地,窮其所有,帶著轉(zhuǎn)瞬即逝的詩意殺入語詞的密林里,尋尋覓覓,披荊斬棘,為的是讓詩意與語詞形成深刻的遇合、完美的對(duì)接,為的是把詩意固定到一個(gè)恰如其分的位置。
悅芳顯然在這一詩歌寫作傳統(tǒng)之中。我甚至覺得,就連她“邂逅策蘭”,“夜讀蘭波”、“遭遇卡夫卡”等等,都不僅是在聆聽一種域外的聲音,而且也是在尋找一種最高端的詩歌語言。要知道,策蘭正是把德語經(jīng)營(yíng)到極致,才寫出了《死亡賦格》那樣的杰作,進(jìn)而打破了阿多諾所謂的“奧斯威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之禁忌。悅芳寫道:“你的詩句在我身體最深刻的地方/不停地發(fā)酵/你死去,我開始呼吸”(《邂逅策蘭》)我想,這里的“呼吸”也應(yīng)該包括文字或語詞的呼吸吧。
因?yàn)閻偡嫉倪@種執(zhí)著,我也就毫無懸念地想到了海德格爾。海氏曾引用斯退芬·格奧爾格的一首題為《詞語》的詩,然后對(duì)最后一行展開了強(qiáng)勁的解讀和分析。在他看來,“詞語破碎處,無物存在(Kein ding sei wo das wort gebricht)”涉及到詞與物的關(guān)系。所謂詞語破碎,也就是詞語缺失。當(dāng)詞語殘缺時(shí),物就處于缺席狀態(tài)。“唯當(dāng)表示物的詞語已被發(fā)現(xiàn)之際,物才是一物。”“唯詞語才使物獲得存在。”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他提出了“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居住于詞語之中”和“語言是存在之家”的著名命題。
把悅芳的所作所為代入到海德格爾的描述之中,似可發(fā)現(xiàn)一個(gè)小小的秘密:她如此執(zhí)著地與語詞搏斗,并非語言潔癖癥或語詞偏執(zhí)狂,而是為了揭示或證明一種存在的可能性。從通常的意義上看,我們似乎都存在著,因?yàn)槲覀儫o疑也居住在詞語之中。但問題是,我們賴以存在的日常語言其實(shí)早已被磨損和污染,就像顧城所說的那樣,那是一種類似于鈔票的語言,它在流通的過程中已被用得又臟又舊。借助于這種語言存在,我們實(shí)際上是存在于不在。詩人的職責(zé)就是要在這種破爛不堪的日常語料庫中翻檢,尋找,如同波德萊爾筆下的拾荒者。他們拯救了語詞,也就拯救了經(jīng)驗(yàn);拯救了經(jīng)驗(yàn),也就拯救了存在。從這個(gè)意義上說,悅芳的語詞勘探工作也就有了特殊的價(jià)值:不僅是鍍亮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也讓人明白了如何才能詩意地存在。她寫詩的時(shí)間雖然不算很長(zhǎng),但一開始就走到了一條正路上。那是海德格爾所謂的“大道”(Ereignis),是用語詞、詩句和詩行正在搭建的一個(gè)存在之家。
走筆至此,我似乎也能對(duì)聶爾為悅芳的這部詩集寫下的序言做一個(gè)回應(yīng)了。聶爾把他這篇序言命名為《在詩之途》,這當(dāng)然是通常意義上的“在詩之途”——詩人走在詩歌寫作的途中。但是,如果把這個(gè)表達(dá)移植到海德格爾的語境里,“在途中”(Unterwegs-sein)馬上就有了一種形而上的意涵。因?yàn)樗f過:“經(jīng)驗(yàn)?zāi)呈乱馕吨涸谕局小⒃谝粭l道路上去獲得某事。從某事上取得一種經(jīng)驗(yàn)意謂:這個(gè)某事——我們?yōu)榱双@得它而正在通向它的途中——關(guān)涉于我們本身、與我們照面、要求我們,因?yàn)樗盐覀冝D(zhuǎn)變而達(dá)乎其本身。”我希望悅芳結(jié)結(jié)實(shí)實(shí)走在海德格爾所描述的這種途中,因?yàn)槟抢镉姓Z詞的詩意經(jīng)驗(yàn),或是有被詩意經(jīng)驗(yàn)浸泡過的語詞。
就像她在《到春天里走走》中所寫的那樣:
一個(gè)詞的咒語。不知
最初被誰脫口而出
剛一言愛,就滿樹花開
這是一種絢麗的意象,但更是一種寫詩的境界。如同蘇東坡所言:“好詩沖口誰能擇,俗子疑人未遣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