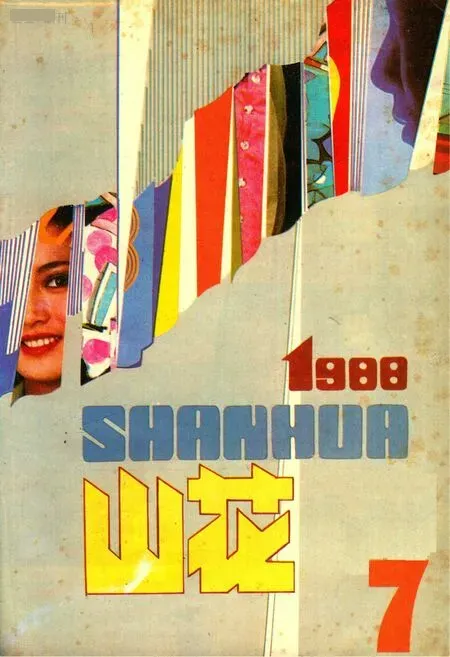花城湖
楊獻(xiàn)平
再向前,就是花城湖。那是一片濕地,水如汪洋。水底盡是淤泥。四周群草茂盛如屏障,野花猶如傳說(shuō)中的仙子。天寶十一年秋天,涼州道營(yíng)田大使朱恩茂的女兒在這里無(wú)故失蹤了,幾天后尸體浮上水面。涼州道行軍總管安思順責(zé)令副官嚴(yán)密追查,弄清真相,嚴(yán)懲兇手。兩年過(guò)去了,副官多方徹查與偵破,但仍舊沒(méi)有找到兇手,甚至連案件的基本線索都沒(méi)掌握。去年秋天,安思順調(diào)任河西節(jié)度副使,帶軍鎮(zhèn)守甘州大斗拔谷;朱恩茂年事已高,再加上失女的打擊,皇上體念他,便回京任職去了。
這個(gè)案件,到現(xiàn)在還是一樁無(wú)頭案。
前天一大早,酒泉郡金塔倉(cāng)庫(kù)的司倉(cāng)派快馬報(bào)告說(shuō),倉(cāng)庫(kù)失竊,但不是庫(kù)銀,而是臨時(shí)存放在那里的一對(duì)白瓷鴛鴦?wù)怼0状梢院颖钡佬现菘樽詈茫擅婀鉂崳瑑?nèi)質(zhì)堅(jiān)硬,造型粗獷而又不失細(xì)膩。更重要的是,這一對(duì)白瓷鴛鴦?wù)硎腔噬弦游鞴?jié)度使王忠嗣作為禮物送給回鶻木波羅可汗的,而且,已經(jīng)事先派人知會(huì)木波羅可汗了。此時(shí),帝國(guó)和回鶻的關(guān)系極其微妙。幾年來(lái),一向和平的雙方在合羅川、馬鬃山一帶爆發(fā)了多次沖突,雖然規(guī)模不大,互有損失,但對(duì)兩國(guó)關(guān)系的影響可謂牽一發(fā)而動(dòng)全身,很多方面都發(fā)生了本質(zhì)上的變化。
本朝皇上送禮物給木波羅可汗的原因,是想緩和日漸緊張的關(guān)系的。可自京城的使團(tuán)還沒(méi)有來(lái)到,白瓷鴛鴦?wù)砭褪Ц`了,這是天大的事情。酒泉太守曹寧遠(yuǎn)一聽(tīng)就慌了,他也知道,如此器物失竊,弄不好,自己的腦殼保不住倒是小事,九族恐怕都難保。
誰(shuí)都知道這是當(dāng)務(wù)之急。
太守派人傳喚我的時(shí)候,我正在西門(mén)外的小院子里磨刀。
我無(wú)比珍愛(ài)這把刀,它不是兵部統(tǒng)一配發(fā)的那種腰刀和長(zhǎng)刀,而有些像匈奴時(shí)代的徑路刀,回鶻騎兵常用,刀身長(zhǎng)一尺五寸,刃寬,刀背厚,無(wú)論是劈斬還是格擋,都很趁手和方便。這把刀,是酒泉郡前任藍(lán)翎侍衛(wèi)趙可安留給我的。
其實(shí),趙可安是我的岳父大人,他女兒名叫趙雪燕,是我的妻子。十一年前,我獨(dú)自一人從河?xùn)|道投軍,憑著一把長(zhǎng)刀,獲得了這從七品下的藍(lán)翎侍衛(wèi)官職。那時(shí)候,帝國(guó)煌煌,四海來(lái)投,諸夷懾服,好一個(gè)太平富貴日子,可在河隴地區(qū)和西域,帝國(guó)與吐蕃、突厥、回紇、薛延陀、鐵勒等部落和國(guó)家時(shí)常發(fā)生摩擦。安西節(jié)度副使岑參是我最喜歡的一位當(dāng)代詩(shī)人。讀了他的《走馬川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之后,我熱血上涌,立即申請(qǐng)到西北邊疆為朝廷效力。
每一個(gè)人心里都住著一個(gè)英雄,每一個(gè)男人都想在馬背上橫行天下,以武功和謀略建立功勛,光耀宗族。名列青史。可當(dāng)我?guī)е齑蟮男坌模簧韥?lái)到肅州郡的時(shí)候,卻被安置為一個(gè)七品藍(lán)翎侍衛(wèi),這與我起初夢(mèng)想的西北軍旅南轅北轍,不上戰(zhàn)場(chǎng),不與敵軍面對(duì)面搏殺,不入百萬(wàn)軍中取上將首級(jí),卻敵于千里之外,怎么可以“上將擁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軍行”?又怎么可以“古來(lái)青史誰(shuí)不見(jiàn),今見(jiàn)功名勝古人”?但人必須接受命運(yùn)的安排,尤其是在皇帝治下,一個(gè)人的反抗和不甘不僅無(wú)效,弄不好會(huì)前功盡棄,甚至還會(huì)無(wú)故失去性命。
幾個(gè)菜,一樽酒,已經(jīng)老了的趙可安在自己家為我接風(fēng)。席間,他語(yǔ)氣沉重而又惋惜地對(duì)我說(shuō),當(dāng)年他從軍西行的時(shí)候,想法也和我一樣,在邊疆之地深入敵軍,為皇上開(kāi)疆拓土,為自己建立功勛,誰(shuí)知道,上司只是給了他一個(gè)藍(lán)翎侍衛(wèi)的職務(wù),常年呆在肅州郡的衙門(mén)中,與一些刀筆吏和官太爺打交道,覺(jué)得實(shí)在窩囊至極,完全不是自己想要的金戈鐵馬、氣吞萬(wàn)里如虎的鐵血生活。慢慢地,他忽然明白,這世上每一個(gè)人,都有自己不可更改的宿命,特別是當(dāng)他娶了當(dāng)?shù)氐钠拮樱辛艘粋€(gè)兒子和兩個(gè)女兒之后,他才發(fā)現(xiàn),邊塞的生活不僅僅是殺戮與謀算,還有家,有自己的親人,盡管名位不顯,報(bào)國(guó)無(wú)門(mén),建功難以,但一家人在一起,安閑度日,有愛(ài)情、親情圍護(hù),又何嘗不是一種人間美事呢?
盡管當(dāng)時(shí)我對(duì)趙可安的說(shuō)法表示認(rèn)同,但在內(nèi)心里還是有些不甘,一有機(jī)會(huì),就想躋身于作戰(zhàn)軍旅;那時(shí)候,高仙芝和封常清,還有哥舒翰,都是河隴地區(qū)和西域名將,關(guān)于他們的奇聞典故到處流傳。我也曾寫(xiě)信給高仙芝和哥舒翰,可一直沒(méi)有回音。如此幾年之后,我和趙可安的女兒趙雪燕結(jié)合為夫妻,一年后有了自己的兒子,天天從公門(mén)出來(lái)便快步回家,妻子做飯菜,我抱孩子,再加上岳父趙可安和岳母,妻哥并小姨一家,我們雖不顯赫,但在肅州這樣的一座小城當(dāng)中,這已經(jīng)是非常不錯(cuò)的生活了。
摯愛(ài)親情暖人心也軟化斗志。漸漸地,我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jīng)沒(méi)有那種躍馬沙場(chǎng)、縱橫戰(zhàn)陣的雄心與抱負(fù)了。但作為一個(gè)武人,武藝不可丟,兵器不可棄。正如我岳父趙可安所說(shuō),武人是我們的宿命,盡管武藝盛世無(wú)法施展,俠客也不足為,但古來(lái)盛世不長(zhǎng)久,即使百無(wú)一用,武藝和兵器,已經(jīng)是我們命中的部分了。
失竊案發(fā)生后,太守曹寧遠(yuǎn)著令我作為牽頭偵破人。這是我到肅州之后,正式領(lǐng)受并具有獨(dú)立職權(quán)的第一個(gè)案件。曹太守下令時(shí)候,我覺(jué)得榮幸,但很快又很沮喪、沉重。這個(gè)案件不同尋常,偵破不了,曹太守的人頭要搬家,我也一樣。最可怕的是《永徽律疏》中的株連法,一個(gè)男人為公無(wú)才而死,是自己的恥辱,倘若恥辱殃及家人,那將是不可饒恕的罪過(guò)。我和曹太守先是騎著快馬到金塔倉(cāng)庫(kù)查看了現(xiàn)場(chǎng)。很奇怪,高墻鐵門(mén),上百士兵看守的倉(cāng)庫(kù),上下內(nèi)外,對(duì)方連一點(diǎn)痕跡都沒(méi)有留下。對(duì)此,我首先想到的是內(nèi)賊;再次想到的是武術(shù)極好的江湖慣偷;第三,此地毗連的回鶻,昭武九姓國(guó)的粟特人,以及西域的薛延陀人、鐵勒人、吐蕃人也很多。
然后分析盜竊此物的動(dòng)機(jī),自然而然的理解當(dāng)然是為財(cái)而鋌而走險(xiǎn),但很快又被否定了。盜賊若是僅僅為了財(cái),為什么只盜走這一對(duì)白瓷鴛鴦?wù)恚瑓s對(duì)大批的金條和銀子視而不見(jiàn)呢?可能是此賊或其雇主垂涎如此珍美之物,并對(duì)此有收藏嗜好;再者,就是除了皇上之外,無(wú)人敢以草率和擔(dān)當(dāng)?shù)恼螁?wèn)題了。帝國(guó)雖然聲威日隆,震懾八方,但西域諸國(guó)和部落在粟特人的操縱下,不時(shí)反叛或挑起戰(zhàn)事,進(jìn)而從中撈取更大的利益。也可能是某個(gè)政治和商團(tuán)為了他們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以盜取白瓷鴛鴦?wù)頌橛深^,進(jìn)而引發(fā)帝國(guó)與回鶻的不信任,那么,這個(gè)事情就不單單是一起盜竊案了,而是一個(gè)牽扯多方敏感神經(jīng)的政治和軍事問(wèn)題的導(dǎo)火索。
事不宜遲。
我當(dāng)即建議曹太守,還是早向河西節(jié)度使王忠嗣報(bào)告的好。曹太守則猶豫不決,捋著胡子在地上轉(zhuǎn)了幾圈之后,厲聲說(shuō),張?jiān)剑澥麦w大,本官限定你在三日之內(nèi)找到失竊之物,不得延誤!我正要開(kāi)口,曹太守又說(shuō),本官會(huì)知會(huì)本郡縣所有的官府兵營(yíng),并上下諸多人等,配合你偵辦此案。另外,你本人有什么要求,盡管向本官開(kāi)口!說(shuō)完,曹太守一甩袖子,出門(mén)上馬回肅州府衙去了。
官大一級(jí)壓死人,我搖搖頭,抓起放在桌上的長(zhǎng)刀,與上戍主范長(zhǎng)春并幾個(gè)兵曹參軍一起走出司庫(kù)衙門(mén),抬頭,天空藍(lán)得有些發(fā)灰,來(lái)自祁連山的鷹隼在空中扶搖或俯沖。我覺(jué)得還應(yīng)當(dāng)從白瓷鴛鴦?wù)淼氖Ц`地點(diǎn)及倉(cāng)庫(kù)周圍尋找蛛絲馬跡。幾個(gè)人再次進(jìn)到倉(cāng)庫(kù),分頭仔細(xì)勘察,許久,一個(gè)軍曹在屋頂上找到了一根黑色的長(zhǎng)發(fā),另一個(gè)軍曹在倉(cāng)庫(kù)后面的戈壁灘上,發(fā)現(xiàn)了一個(gè)穿布鞋的腳印,還有幾個(gè)顯然被樹(shù)枝拖抹過(guò)的馬蹄印,去向應(yīng)當(dāng)是西北方向的花城湖一帶。
花城湖在金塔縣西北方三十里的地方,再向前,就是回鶻領(lǐng)地;這一剽悍嗜血的游牧部族,與突厥一樣,向來(lái)以力為雄,以戰(zhàn)止戰(zhàn),以戰(zhàn)養(yǎng)生,仿佛他們與生俱來(lái)就是和深處農(nóng)耕區(qū)的帝國(guó)作對(duì)似的,深諳利則進(jìn)、不利則退的游擊戰(zhàn)法,好像帝國(guó)就是他們?nèi)≈槐M用之不竭的金庫(kù)糧倉(cāng)。更可惡的是,他們時(shí)常越過(guò)邊界,在我大唐疆土搶掠?jì)D女、糧草和牲畜,我們的婦女在那里可以當(dāng)牲口一樣買賣,比他們最下等的奴隸還要卑賤,當(dāng)然,被擄走的婦女命運(yùn)也很悲慘,被作為奴隸還是好運(yùn),更多的卻被隨意斬殺。
即使那根毛發(fā)是盜賊的,但也無(wú)法判斷是男是女;長(zhǎng)發(fā)不僅帝國(guó)子女皆是,周邊的游牧部落也多是如此。但一個(gè)有經(jīng)驗(yàn)的軍曹說(shuō),這樣的頭發(fā),看起來(lái)不像是男子的,因?yàn)樗浅H峒?xì),上面還有一股淡淡的脂粉味道;再仔細(xì)勘察戈壁灘上的模糊的腳印,也發(fā)現(xiàn)不像是男子所留下的,只是那馬蹄印好像為回鶻獨(dú)有,蹄子大,跨步長(zhǎng),落地有力,這該是那種叫做骨利干的高個(gè)子馬,產(chǎn)自西域昆侖東山峽谷,以速度快、突擊性強(qiáng)著稱;帝國(guó)曾多次以絲綢換取這一種戰(zhàn)馬,但回鶻每次只給予少量,價(jià)格還非常的高。
傍晚回到肅州,我沒(méi)去衙門(mén),到家里,直奔岳父母房間。聽(tīng)了此事,岳父趙可安絲毫沒(méi)有驚訝,坐在沙棗木椅子上,仰頭,看地,思忖了一會(huì)兒,說(shuō),此事蹊蹺,我看盜賊的目的不是為了收藏把玩,一定是想借此來(lái)引發(fā)帝國(guó)與回鶻的沖突。你知道,木波羅可汗為人狡詐多疑,本性貪婪,這么多年來(lái),向西兼并了西突厥、夏戛斯和拔汗那,向北打到了渾河,至少有十幾個(gè)部落被他懾服,并成為他的奴仆。歷來(lái),這些瀚海澤鹵與莽蒼草原上的軍團(tuán),始終以中央帝國(guó)為衣食父母與主要財(cái)富來(lái)源的。現(xiàn)在,皇室驕奢淫逸,僅明皇為安祿山在京城建造的府邸,所用銀兩超過(guò)了邊疆駐軍三年的全部開(kāi)支,富麗堂皇,一點(diǎn)不亞于皇宮;朝中官員斗富成風(fēng),富商巨賈趁機(jī)買官,地方諸多官吏為討得上司乃至皇上歡心,搜羅奇珍異寶、罕世珍物等,用于拍馬逢迎。如此景觀,乃亡國(guó)之兆也。如果我沒(méi)猜錯(cuò)的話,木波羅可汗也看到了我朝這一點(diǎn),想找理由來(lái)鯨吞河山,入主中原。
飯時(shí)忽然回娘家的小姨子趙雪琴聽(tīng)了此事,也認(rèn)為岳父趙可安的分析有道理。她的丈夫是肅州城中的富戶,其公公早年以私賣鹽鐵發(fā)家,有了一大筆的積蓄后,又轉(zhuǎn)為以倒賣皮毛、絹帛、農(nóng)具等正當(dāng)商人的面目重新出現(xiàn)。小姨子趙雪琴的丈夫冉長(zhǎng)安也是一個(gè)學(xué)武之人,一把長(zhǎng)劍舞的是風(fēng)雨不透,在涼州道以內(nèi),鮮有對(duì)手。小姨子趙雪琴為人大方,身為女兒身,但做人處事一點(diǎn)不亞于男人。冉長(zhǎng)安也說(shuō),岳父大人說(shuō)的對(duì),論價(jià)值,一對(duì)白瓷鴛鴦?wù)聿贿^(guò)銀錢十萬(wàn)貫,巨富若要真的喜愛(ài),派人到邢州郡瓷廠再訂做一對(duì),也不是什么難事。我看,此事一定不是錢的事情,就是個(gè)陰謀。
妻子趙雪燕的話倒是與他們不同。晚上睡下,夫妻之事后,妻子說(shuō),我看這個(gè)失竊案未必就是陰謀,說(shuō)不定是一個(gè)惡作劇,還說(shuō)不定是監(jiān)守自盜,誰(shuí)一時(shí)心起,盜出來(lái)做個(gè)模子,更說(shuō)不定,再等幾天,盜賊會(huì)自己送回來(lái)的。我撫摸了一下她的長(zhǎng)發(fā),看著她依舊嬌俏的臉龐說(shuō),你說(shuō)的有道理,任何可能都不排除才是對(duì)的;很多事情,看起來(lái)不起眼、不經(jīng)意的,往往蘊(yùn)藏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但作為朝廷中人,領(lǐng)受任務(wù),盡己所能,為之分憂,也是職責(zé)所在,此后一段時(shí)間,我可能要連日奔波,難得回家了。妻子點(diǎn)點(diǎn)頭,嗯了一聲,轉(zhuǎn)身吹滅了搖搖曳曳的松油燈。
黑暗中,我很久睡不著,腦子里全是那樁失竊案。一對(duì)白瓷鴛鴦?wù)恚瑤讉€(gè)馬蹄印,人的腳印,倉(cāng)庫(kù)屋頂?shù)拈L(zhǎng)發(fā),西北方向,花城湖……這些之間到底是怎樣的一個(gè)聯(lián)系?據(jù)我了解,金塔倉(cāng)庫(kù)內(nèi)外均無(wú)民居,士卒并司庫(kù)也沒(méi)有攜帶女眷在身邊。作為皇上御點(diǎn)的贈(zèng)予外邦的禮物,存放在金塔倉(cāng)庫(kù)這件事,一定是保密的,走漏風(fēng)聲的一定是與此事緊密相關(guān)的人,否則不會(huì)知道得那么清楚,連白瓷鴛鴦?wù)泶娣诺木唧w庫(kù)房都毫厘不差。如此猜測(cè),這樁案件,該是里應(yīng)外合、監(jiān)守自盜的多。
第二天一大早,肅州城還沒(méi)被晨曦覆蓋,我就帶了幾個(gè)軍曹,再次去了金塔倉(cāng)庫(kù)。我先是與司庫(kù)了解情況,司庫(kù)是一個(gè)奸猾的男人,每一句話都說(shuō)得滴水不漏;另一個(gè)看守庫(kù)房的軍曹倒是直率,一上來(lái)就對(duì)我說(shuō),這事兒,肯定有內(nèi)奸,但肯定不是我們倉(cāng)庫(kù)的。我知道他說(shuō)的意思。他說(shuō),好端端的東西被盜了,而且是皇上御點(diǎn)過(guò)的,除了押運(yùn)的人和看倉(cāng)庫(kù)的人知道內(nèi)情,還有誰(shuí)?我點(diǎn)頭稱是,又問(wèn)他有沒(méi)有感覺(jué)或看到異常情況。他則說(shuō),要是帝國(guó)人盜竊的,肯定往花城湖方向跑,然后再折回來(lái),因?yàn)椋I賊既然有那么高的功夫,腦袋肯定也不笨,知道把線索引向最難辦的地方。他說(shuō)的意思我也明白。也覺(jué)得,這個(gè)軍曹雖然說(shuō)話直接,但腦子還是夠用的。另一個(gè)軍曹也很有意思,他說(shuō)他連續(xù)幾個(gè)晚上做夢(mèng),夢(mèng)見(jiàn)自己抱著那對(duì)白瓷鴛鴦?wù)碓诟瓯跒┥蠜](méi)命地跑,他心里最想的就是能遇到一匹回鶻的骨利干馬,實(shí)在不行,有個(gè)駱駝也行。他的話把我逗笑了,只覺(jué)得這個(gè)不到二十歲的小伙子很可愛(ài)。但仔細(xì)一想,他的這個(gè)夢(mèng)如果是真的話,至少告訴我一個(gè)信息,那就是,盜竊白瓷鴛鴦?wù)淼娜诉€沒(méi)有把貨物隱藏起來(lái)或交付雇主。
在路上不僅是動(dòng)態(tài)的,還有無(wú)限的可能性。
我把上戍主范長(zhǎng)春喊來(lái),對(duì)他說(shuō),你們幾個(gè)繼續(xù)在倉(cāng)庫(kù)了解情況,務(wù)必要細(xì)致。我現(xiàn)在向西北方向走一趟,如果次日凌晨我還沒(méi)有回來(lái),你們?cè)偃フ椅摇7堕L(zhǎng)春急切說(shuō),張侍衛(wèi),還是多帶幾個(gè)兄弟去吧?我揚(yáng)了揚(yáng)手中的長(zhǎng)刀,說(shuō),有這把刀,即使遇到十個(gè)八個(gè)回鶻騎兵也不怕!然后跨上馬背,向花城湖方向奔騰而去。
馬蹄揚(yáng)起白土,幾座村莊之后,就是一望無(wú)際的戈壁灘了。向北是巨大的沙漠,其中有一條名聞遐邇的河流——弱水河,一直流入合羅川和回鶻的領(lǐng)地。從這里,穿過(guò)回鶻全境,可以通往西域、身毒和條枝等國(guó)家。大約三個(gè)多時(shí)辰,越走越荒無(wú)人煙,即使頭頂偌大的太陽(yáng),也覺(jué)得身體內(nèi)外空蕩蕩的,充滿了敵意和不安全感。遠(yuǎn)遠(yuǎn)看到花城湖時(shí)候,我的心咯噔了一下,驀然想起前兩年無(wú)故在這里死去的朱恩茂的女兒。
那個(gè)女子我見(jiàn)過(guò)。
朱恩茂原為肅州太守,還當(dāng)過(guò)涼州道屯田大使。我來(lái)到肅州時(shí)候,他還是太守。作為七品藍(lán)翎侍衛(wèi),我的職責(zé)之一,就是保護(hù)地方長(zhǎng)官的人身安全。那些日子,肅州也連續(xù)發(fā)生了幾樁殺人案,兇手大都是粟特人和吐蕃人,數(shù)家商鋪、店家被搶掠不說(shuō),全家都被殺掉了。朱恩茂原也是一介武夫,但作為文官多年之后,就荒廢了武技。每一個(gè)人都是怕死的,朱恩茂尤其嚴(yán)重。責(zé)令我日夜帶人守護(hù)衙門(mén)和他的家室。在此情況下,我和朱恩茂一家都有交集。
朱恩茂的女兒名叫朱秀英,可能是因?yàn)槟赣H是鐵勒人的緣故,朱秀英長(zhǎng)得是俏媚艷麗而又與眾不同,高鼻梁,眼睛大而發(fā)藍(lán),頭發(fā)微黃發(fā)卷;臀部巨大,腰肢纖細(xì),嘴唇不薄不厚,但紅艷照人。有一個(gè)深夜,我覺(jué)得有點(diǎn)困,正坐在小亭子里打瞌睡,忽然覺(jué)得脖頸上一涼,閃電驚醒后,下意識(shí)地問(wèn)對(duì)方是誰(shuí),有何企圖?對(duì)方一直不吭聲,劍刃在我脖頸上也紋絲不動(dòng)。我又說(shuō),要?dú)⒕蛣?dòng)手吧!對(duì)方還是不出聲。我這人脾氣暴躁,尤其受不了技不如人,還被人凌辱。這對(duì)于一個(gè)武人來(lái)說(shuō),是天性,也是血性的表現(xiàn)。見(jiàn)對(duì)方久不出聲,也不動(dòng)手,我怒喝一聲,站起身來(lái),借著星光,回身一看,那人居然是朱恩茂的女兒朱秀英。
一個(gè)女子,有如此好的身手,令我驚詫莫名,正要開(kāi)口說(shuō)話,卻聽(tīng)朱秀英噗嗤一聲笑了出來(lái),而且笑得花枝亂顫,這使我更加羞慚,厲聲說(shuō):朱大小姐,朱女俠,我張某人技不如人,殺了便是,請(qǐng)不要這樣侮辱我!朱秀英這才說(shuō),張侍衛(wèi),本女俠不是羞辱你,而是用這個(gè)告訴你,一個(gè)武人,最重要的不是你的格斗技術(shù),勇氣和體力,是你感覺(jué)的敏銳與警覺(jué)。
朱秀英說(shuō)得很對(duì)!
而她怎么忽然就沉尸花城湖了呢?
越是接近花城湖,我反倒不想白瓷鴛鴦?wù)硎Ц`的事情了,所有的思維都集中到了朱秀英沉尸花城湖這一樁舊案上來(lái)了。
在岸邊停下,戰(zhàn)馬汗水涔涔,獨(dú)自越過(guò)群草,到湖邊喝水去了。此時(shí),金烏西墜,大地輝煌。站在野花爛漫的土丘上向北遠(yuǎn)眺,只見(jiàn)莽蒼大地上,殘陽(yáng)如血,弱水河兩岸的烽火臺(tái)好像倒插的劍鞘。當(dāng)年,漢李陵就是從這里帶兵遠(yuǎn)征而終生未還的;當(dāng)朝詩(shī)人、畫(huà)家王維前些年勞軍至此,寫(xiě)下了“大漠孤煙直,長(zhǎng)河落日?qǐng)A”之佳句;而現(xiàn)在,回鶻占據(jù)了弱水河右岸的大片領(lǐng)地,只要放開(kāi)馬韁,不要一炷香的功夫,就可以席卷金塔盆地和肅州城野。
入暮時(shí)分,大地愈加莽蒼,星子逐漸隱現(xiàn);我沿著花城湖走了一圈,卻發(fā)現(xiàn),這個(gè)湖并不是圓形的,尤其是西北方向,有一道斜斜的彎道,然后是大片的蘆葦,一眼望不到盡頭。靜靜地坐下來(lái),岸邊有癩蛤蟆的叫聲,還有一些蟲(chóng)鳴,水中不斷泛起水泡,魚(yú)兒在忙著捕食。再到彎道旁邊,靠近蘆葦叢的時(shí)候,我只覺(jué)得有一種熱騰騰的東西,是空氣,又好像人的體溫。
對(duì),是有人生活的那種煙火氣和肉身活動(dòng)的味道。
怎么可能?
我放開(kāi)馬匹,讓它自己到遠(yuǎn)處吃草。
我覺(jué)得,這片蘆葦叢中,一定有不尋常的東西和某些隱秘的存在。
午夜時(shí)候,一切安靜。
蹲在蘆葦叢旁邊,我居然聽(tīng)到了說(shuō)話的聲音,有男聲,也有女聲,還有嬰兒啼哭。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震驚了。起身,輕手輕腳地?fù)荛_(kāi)高大的蘆葦,向內(nèi)走了幾步,一切卻都像沒(méi)有人和其他動(dòng)物活動(dòng)的痕跡。再向前走幾十步,還是沒(méi)有任何可疑的跡象。我再蹲下來(lái)傾聽(tīng),剛才的聲音卻不復(fù)出現(xiàn)。蘆葦叢中安靜極了,唯有水緩緩蕩漾和滲入的聲音絲絲入扣,好像一種自然的音樂(lè)。
曹太守起本郡一半兵馬,約有兩千人,與我一同去往花城湖。軍隊(duì)行到距離金塔倉(cāng)庫(kù)不遠(yuǎn)的地方,司庫(kù)騎著一匹快馬迎了上來(lái),見(jiàn)到曹太守,翻身下馬之后,奔過(guò)去就說(shuō),大人大人,白瓷鴛鴦?wù)砘貋?lái)了!曹太守面露驚異,仍舊一臉不信地厲聲問(wèn)司庫(kù),司庫(kù)說(shuō),真的真的,一點(diǎn)沒(méi)錯(cuò)。曹太守臉色放松,思忖了一下,又問(wèn),你確定是原物,沒(méi)被調(diào)包,沒(méi)有損壞?司庫(kù)說(shuō),真的是原物,毫發(fā)無(wú)損。曹太守哼了一聲,打馬直奔不遠(yuǎn)處的倉(cāng)庫(kù)。
我也驚異,正當(dāng)大軍圍剿搜查蘆葦叢的時(shí)候,白瓷鴛鴦?wù)砭尤伙w回了原地。
這又是怎么回事?
見(jiàn)到原物,曹太守決定將之帶回肅州城,由府庫(kù)保管。我上前說(shuō),那蘆葦蕩中定有蹊蹺,大軍既然開(kāi)拔至此,不如……
曹太守哼了一聲,斜著眼睛看著我說(shuō),你笨蛋啊,腦瓜子被驢子咬了;花城湖乃是邊地,大軍進(jìn)入,一旦引發(fā)誤會(huì),回鶻出兵,這責(zé)任你能擔(dān)得起嗎?
大軍回返,我留在金塔倉(cāng)庫(kù)。
那蘆葦蕩中到底有什么秘密?思忖再三,我決定一人深入,探個(gè)究竟。
還是夜晚,我弄了一只小船,從寬闊處出發(fā),劃過(guò)彎道,進(jìn)入蘆葦蕩。我發(fā)現(xiàn),那些蘆葦雖然看起來(lái)沒(méi)被人動(dòng)過(guò),而且青青蔥蔥地長(zhǎng)在岸邊和水中,但它們卻是能夠被自由移動(dòng)的,只要船頭一碰蘆葦?shù)陌胙糠郑蜁?huì)主動(dòng)閃出一條水道,小船進(jìn)入和出來(lái)一點(diǎn)阻隔都沒(méi)有。
再向前,蘆葦越發(fā)茂密和高大,船只穿行很困難。我一邊劃動(dòng),一邊警覺(jué)地看著密不透風(fēng)的四周。大約有三里多的路程,一點(diǎn)異常動(dòng)靜也沒(méi)有。再向前劃動(dòng),撥開(kāi)一層很厚的蘆葦,前面忽然出現(xiàn)幾座小巧的木質(zhì)房屋,窗欞上依稀有燈光。我快劃過(guò)去,把船停在一個(gè)隱秘的地方,然后蹚水過(guò)去,爬上一片由木樁和木板做成的平地,走到其中一座亮著燈光的窗戶前,正要捅開(kāi)偷看,門(mén)卻開(kāi)了。
是朱恩茂和朱秀英,朱秀英懷里還抱著一個(gè)大約一歲多的孩子。
再后來(lái),我居然看到了我的岳父趙可安夫婦,還有小姨子趙雪琴和他的丈夫冉長(zhǎng)安一家人。他們笑著讓我坐下。我惶惑不能自已,也覺(jué)得有些震驚。攥刀的手背上冒著粗大的青筋。我岳父趙可安哈哈笑著說(shuō),張?jiān)剑覀兌贾滥氵t早會(huì)回到這里的。不要害怕,都是自家人,誰(shuí)也不會(huì)傷害你。須發(fā)皆白的朱恩茂也呵呵笑說(shuō),我和你岳父同在肅州多年,早已是莫逆之交。雪琴、長(zhǎng)安他們一家也是。說(shuō)起來(lái),這地方,這花銷建筑,還是長(zhǎng)安家出的資金呢!
我腦袋還在發(fā)懵,但戒備漸漸消除。
一夜之后,日光再現(xiàn)。
我毅然決然地離開(kāi)了蘆葦蕩。
回到肅州城,我就向曹太守提交了辭呈。他笑著說(shuō),這一次,你雖然沒(méi)有直接偵破案件,但很費(fèi)心賣力,我正要寫(xiě)奏折,為你請(qǐng)功,怎么突然要離職歸田?我笑笑說(shuō),太守大人的好意在下心領(lǐng)了,只是家中父母年事已高,多次信札要我回去。在下不才,跟隨大人多年,寸功未立,現(xiàn)在又年屆四十,該是回鄉(xiāng)侍候父母大人的時(shí)候了,萬(wàn)請(qǐng)大人恩準(zhǔn)!
曹太守又笑了笑,走到我跟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說(shuō),你是孝義之人,本太守也極為理解你的心情,愿意回鄉(xiāng)就回吧。
知道是虛假之言,我還是唯唯告退。
往家走的路上,我還想,我這一決定,會(huì)不會(huì)遭到妻子反對(duì)呢?再說(shuō),她是不是也想去花城湖與父母、妹妹等一起隱居了呢?
我沒(méi)想到的是,妻兒不僅在家等我,對(duì)我的辭職決定,妻子竟然也沒(méi)有絲毫怨言,還對(duì)我說(shuō),早該如此的!我說(shuō)了岳父母和朱恩茂、冉長(zhǎng)安、趙雪琴的事情。她說(shuō)她早就知道的。岳父母也曾要她說(shuō)服我一同到花城湖隱居。妻子怕我性格耿直,貪戀軍旅,又常懷建功之心,不會(huì)過(guò)早歸隱,也就一直沒(méi)說(shuō)。
至于朱秀英沉尸花城湖的事情,那也不過(guò)是他們制造的一個(gè)假象。因由很簡(jiǎn)單,朱恩茂就是想給人造成失女的事實(shí)。這么多年來(lái),他們?cè)诨ǔ呛圃炝硕嗥鹩腥顺潦诤嫩E象,用以阻止周邊人接近花城湖,以防他們的隱居點(diǎn)被人識(shí)破。盜取白瓷鴛鴦?wù)恚彩侵煨阌⒏傻摹Kf(shuō)并不想據(jù)為己有,或者搞什么陰謀活動(dòng)。是他父親朱恩茂年事已高,老是頭疼,據(jù)說(shuō)枕白瓷可以減輕頭部發(fā)熱,清腦,醒目,鎮(zhèn)痛。朱秀英盜取后,朱恩茂枕了幾天,我岳父趙可安聽(tīng)說(shuō)我在負(fù)責(zé)偵破此案后,立即派人說(shuō)給了朱恩茂。冉長(zhǎng)安說(shuō)這個(gè)也不值幾個(gè)錢,當(dāng)即令人畫(huà)了圖紙和樣式,派人至邢州郡找白瓷廠重新訂做。朱秀英又趁夜至金塔倉(cāng)庫(kù),將白瓷鴛鴦?wù)矸呕卦弧?/p>
這件事似乎到此就算真相大白了。可是,我和妻兒回到邢州郡大嶺關(guān)故鄉(xiāng)第二年,安祿山范陽(yáng)起兵,不過(guò)一月,就打到了洛陽(yáng)。沿途郡縣尸積如山,血流成河,不論城鄉(xiāng),皆為焦土。高仙芝、封常清在潼關(guān)被魚(yú)朝恩奉命斬首;哥舒翰出兵失利后,投降安祿山又做了官。唯有河?xùn)|的郭子儀、李光弼效忠于皇上。再后來(lái),李亨在靈武繼位,李隆基躲到成都樂(lè)不思秦。整個(gè)天下,戰(zhàn)禍頻仍,一個(gè)煌煌帝國(guó),頃刻之間,日暮西山。
我的故鄉(xiāng)因?yàn)槠h(yuǎn),而免受涂炭。每次有人從山外帶回消息,我都沉默半天。妻子在我耳邊輕聲輕語(yǔ)地說(shuō),王王朝朝,君君臣臣,窮賤富貴,流氓草寇,歷來(lái)都是這樣的,現(xiàn)在,你也四十多了,也不要再想皇帝家的事情了,守著高堂和我們娘兒仨,種田為生,也未嘗不是完美的生活。
我點(diǎn)點(diǎn)頭。問(wèn)她說(shuō),怎么舍得生身父母和兄妹,跟我一起回這山里呢?
妻子看著一朵雞冠花說(shuō),女人,實(shí)際上是以夫家為重的,與之既有子女,便是血濃于水的了。盡管此地生疏,但有你,有兒女,有公婆,有這疊嶂之山與幾畝薄地,簡(jiǎn)簡(jiǎn)單單過(guò)一輩子也不錯(cuò)。
我起身抱了抱妻子,在她額頭上親了一下。
妻子臉頰緋紅,宛如我和她剛結(jié)婚的時(shí)候。
有如此賢惠的妻子,安閑的生活,已經(jīng)足夠了。
可在很多時(shí)候,我總是忍不住摘下掛在墻上的長(zhǎng)刀,拔出,寒光如雪,刃口鋒利。我不由得嘆息一聲,自言自語(yǔ)說(shuō),當(dāng)年那個(gè)夢(mèng)想功業(yè)的武人,已經(jīng)在世事中徹底沉淪了。他已經(jīng)不是他了,我也不是我了。古來(lái)多少英雄,大多的,也只是大夢(mèng)一場(chǎng)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