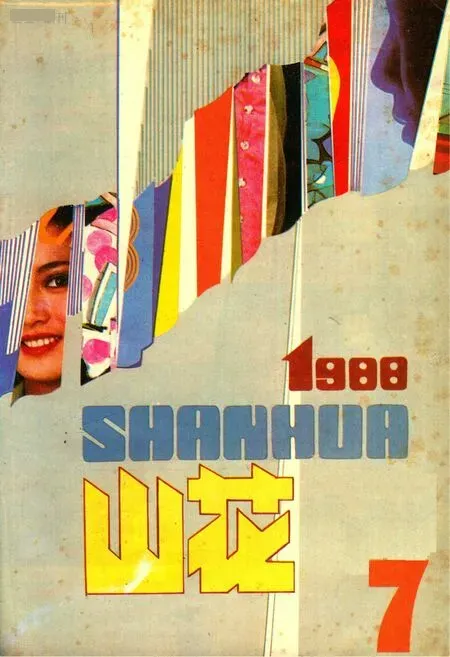我不在那兒
雨后的那天傍晚,父親的行李袋癟了下去。起初,我只看見它空落落地張開一條縫,潮濕的墻灰飄在拉鏈邊緣,像一把散發著腥味的頭皮屑。吃晚飯的時候,姥爺說起夜里又咳痰,母親終于忍無可忍道:“你再這樣下去會死的!”燈光昏暗,她的臉藏在陰影里,只有耳垂的抖動讓我覺得似曾相識。那還是很久之前,父親的行李袋還塞在柜子最底層。每個早上,我都能看見他的綠色面盆在水泥地板上招搖,它讓我想起動畫片《變相怪杰》里那副著名的面具。母親圍著家具打轉,一會兒冰箱,一會兒洗衣機,然后是馬桶和拖把。最后,她從臥室徘徊至廚房,盯著燃氣爐上淡藍色的火焰,背對著我:“恁爸晚上回來了沒?”她又高又胖,像一堆層層疊疊的軟泥巴,只有耳垂生機勃勃,召喚我。
“回來了吧。臉盆在那擺著。”
“擺著?里面有水嗎。”她說得像問句,又像肯定句,我有些不知所措。小時候,我總是不記得父親有沒有讓我轉達他不回來的訊息。傍晚有那么多游戲——方磊、宋慈,每一個小伙伴都要跟我玩,我們從街西玩到街東,最遠到達護城河。護城河邊有一排天天逗小孩兒的悠閑阿姨,她們會給大家分帶著煙灰味兒的瓜子。這樣玩起來,一直到晚上,父親交待的那些,我就都忘了。
“再這樣下去會死的。”
我從時間另一頭回來,用筷子扒著剩下的幾口菜飯,湯卻忍著沒喝,只看沸騰的熱氣盈盈繞繞,很快就和墻壁的花紋揉成一團。
父親這次離開得有些不同。我們都不知道他要走,只覺他起得早了些。我沒有聽見母親焦慮地翻身,也沒有想象她全身赤裸、吊著兩枚軟趴趴的乳房歇斯底里的情景。我靠著床頭,聽見父親在大聲漱口。他把水半吞進胃里,等到好像在體內煮沸了,再咕嘟嘟吐出。等我下了狠心從被窩里鉆出來,走到地板結冰的洗手間時,就只能看見外面立著的行李袋了。
母親已經開始吸豬骨頭的骨髓。我的手在耳朵上揉搓,以期聽不見這聲音。很快,我聽見刺啦一聲。她面向了我,手里還捏著撕下的一頁臺歷。
“這不是上月那一頁兒嗎?”
“是上個月的。現在已經一月了。”
“再買一個唄。現在誰還用臺歷啊。”
“明你別起來太晚,恁姑要來。”
她低下頭。一開始只是盯著手邊沒吃完的包子,然后就開始盯向拖鞋、地板。就好像在一路盯著自己是怎么老的。一條腿翹在凳子上,另一條勾著椅腿。嘴角微微下斜,一小團唾沫星子掛在那里,看起來還在向曾經的梨渦移動——現在那里已經是一條淺淺的峽谷了。
父親走后,母親一度想給大門換把鎖,不過換鎖的師傅說得一百塊,她就遲疑了。過了幾天,她也就不再提這事,下班后匆匆往家趕,從六點坐到十二點,有時候看電視,有時候進我的房間跟我聊天。她從不敲門,直接進來,讓我覺得自己仿佛還在上中學,條件反射般關掉游戲、正在看的電視劇。這很不好,但我還是忍不住這樣做。母親總是一副愁苦的樣子,跟我說著話,眼睛卻望向別處。這讓我感到慶幸,也有些尷尬。除非她站起身,看向外面。操場、商業區、舍利塔——代表我們這兒現在和過去的東西,都堆在那里。當她的注意力在那個范圍游移,我就不會感到不適,可惜不總是這樣。眼下這房子里只有我們倆,她變得很木訥,像一臺轉動失靈的實時監控器,我只好跟她說晚上仍去宋慈家。
“其實你不用說的。這也不是你爸第一次走了。”
宋慈白得出奇,皮膚很薄,看得見淺淺的紅血絲。小時候,我和方磊喜歡拿彩色筆把她手臂上、腿上,甚至臉上的紅血絲描出來。有那么幾次,我們快要把她畫成世界地圖。不過她現在胖了,整個人像充水的大娃娃,離遠看,就像人群中一只雪白的大地球儀。我覺得她現在的身體更適合我們發揮,那些紅血絲被胖肉撐開,均勻分布在皮膚的天南地北,到處閃爍。我喜歡在她肥碩的腰部按來按去,手指敲打出哆來咪發嗦的音節。她像小時候一樣笑起來,房間都顯得大了。
“我們煮倆雞蛋吧。”
小區逐漸滅了燈。我們的臉出現在對面人家灰色的玻璃窗上。
“你說他們睡著沒。”
“燈都關了,肯定睡了吧。”
“關了也不一定睡著呀。”
已經十二點了。我沿著曲曲折折的紅色圍墻回家去。路燈閃著,背影被拖得很長,我不敢回頭看它。
父親已經離開一個月了。
小時候,他也經常離開。有時候兩個小時,有時候一個晚上。像世界上很多父親一樣,我睡著了他才回來,我醒來了他還睡著。
我們偶爾會在早晨相遇,也有時候是晚上。他總是匆匆忙忙,吞咽著一根蘸滿豆漿的油條,或者熱好的白粥。我們很少說話,只記得有一次針對某邊境問題發表了不同的看法。我很快不記得自己說了什么,只覺得必須那么說。那天的飯因而吃得有些久,母親很高興。她提議晚上去護城河邊走走,我拒絕了,接著父親也拒絕了。她有些難過,悶聲吃飯,我突然有些愧疚。下樓推車去學校的時候,我看見父親踉踉蹌蹌從狹窄的樓道下來,嘴里含著一顆檳榔。
“我出去一會兒。”他斜著嘴,褐色的唾沫粘在嘴角,像一枚火星子。
我尾隨著他,沒走幾步,就被遠遠甩在了后面。后來我一度想,是我不愿意再往前走,還是父親真的要甩掉我。這想法生根發芽,逐漸讓我感到一陣陣心驚。母親的哭聲一點點從墻壁往下滲,路過三層、二層,直到當時爺爺奶奶住的這間現已變成車庫的一樓。我聽見她在打電話,一陣一陣都是忙音。我知道再站一會兒她一定讓我去找父親,所以只好撒腿就跑。
家里的燈還亮著。母親像個巨大的影子懸掛在臥室,并逐漸往客廳移動。路過行李袋的時候,我丟了一把父親遺忘在古玩架上的剃須刀進去。行李袋已經放在那里很久了,丟進去的時候,都能聽到灰塵紛紛墜落的聲音。
“他早就不回家了。一天,一月,我看這次是一輩子不回來啦。”
“你天天沒個好臉,他咋會想回來。”
冬天的客廳像冰窖一樣,母親把爐子重新生起。新鮮的火星冒出來,姑姑們的手烤得通紅,哈出來的熱氣在她們中間團來團去。她們壓低了聲音,我聽得更清楚了。我屏住呼吸,蜷縮回被子里,炭火的熱氣仿佛一路蔓延到房間。我盯著天花板上兩條白色花紋,看著它們繞過整間房,爬出內墻。腳汗津津的,卻已經變冷。那濕冷蔓上來,腿也有了寒意。可我還是不想起床。
她們的聲音原本在客廳盡頭,這會兒離臥室近了。我不知道誰先站起來的,反正母親站了起來。她在屋里也喜歡穿高跟鞋,腳步聲格外清脆。我仿佛聽到她衣裙摩擦的聲音——這聲音也許不是來自她,但她的身體一定在這所有聲音當中搖擺。這會兒她應該已經走到廚房,聲音明顯遠了一些。大姑還在絮叨,二姑的博美吠叫了兩聲。洗手間的水龍頭一直滴水,不知是誰過去把它擰緊了。家具本安安穩穩擺著,此刻桌椅腿卻有了一些挪動的響聲。這感覺讓人有些不安,我只得起床。
已經十一點了,但天氣陰沉沉,只有六七點似的。我突然期待開學,盡管這是最后一個學期了。長吁一口氣,雙臂扶著洗漱臺,我看見鏡子里困倦的臉。眼袋陷下去,眼角已經有了一道淺淺的細紋。我想起發現母親眼角的皺紋也特別突然。那是六年前的一天,我從長途汽車下來,一夜未睡仍精氣十足,滿是汽油味的大衣裹住當時只有八十斤的我,行李袋比父親那只還要顯得碩大。我把它放在父親的摩托車后座上,坐在母親背后,她的眼角像兩條干癟的橘皮折疊在一起。父親載著我們以極其危險的弧度穿過中心大街,嘴里不停說著:“不要亂動,你們要相信我。”
已經有人尷尬地踱步,姑姑們指著墻壁上多年前的全家福,說著一些過去的事,關于父親小時候怎么上學,關于我小時候怎么不聽話。從洗手間半開的窗戶,能看到整個小區簇新的塑膠花壇、音樂噴泉,還有幾棵光長枝條不長葉子的樹。灑水車把幾條主干道沖洗得清爽宜人,可是無人經過,只有幾只野貓飄來飄去。
沒有那么多樓的時候,各層各戶人滿為患,真的蓋起一棟棟新樓房,搬進來的住家卻寥寥。為了容納這些新樓,整座城市讓出了許多空間。電影院、商場、游戲城,還有一個老年活動中心都不復存在了。高中時,我和宋慈經常糾集一幫同學,晚自習后到小區空置的毛胚房玩天黑請閉眼。我們擎著手電,反復陳述A或者B為什么是或不是殺手的理由。玩到最后,剩下的往往只有我和宋慈。也有時候,方磊會加入我們。只是那時,他已經不那么愿意在人前和我們兩個相貌普通的女生呆在一起。更多時候,我們私下會面。他從家里跑出來,手里捏著新的物理習題冊,迅速抄上我的答案,又讓宋慈口述一遍英語作文。等到一切結束,我們會討論一下父親的出走問題,或者開發一些新游戲。比如我們經常躲在沒裝門的毛胚房內,平躺在宋慈從家里偷來的涼席上。我的手放在方磊的脖子上,方磊把手搭在宋慈的脖子上。默數完一、二、三,狠狠掐住對方。有那么幾次,我們同時感受到了耳鳴。這讓人快活。可終究很短暫。手松開的一剎那,我聽見母親在樓下撥打父親的號碼,《獻給愛麗絲》的彩鈴聲不斷從電話里傳出來,一遍一遍沿著空蕩蕩的樓層上升,就是沒有人接聽。
我憋著口氣,“你們有時間不如研究下我爹去哪了。”
“是啊。去哪了?”
“誰知道。”
她們分開站著,彼此無話,卻沒有要走的意思。母親轉過臉,站在廚房門邊盯著那口在煮水的鍋。我看向客廳的落地鏡。有一角已經略微殘破,像隨時都要倒,可我就是不想跨過去把它扶正。
“他就沒錯?說走就走,想過別人的感受嗎?”
母親哭起來。“怨我。”她坐下來,低著頭。
“晚上我不在家吃飯。同學聚會。”
我捏著那條信息。手機屏幕一直亮著,這會兒有些發燙。
“他先給你發短信的?”
“這重要嗎?你是不是很想見到他?”宋慈說。
“我比較關心今天誰給錢。”
“肯定是方磊啊。”
“他以前抄作業現在還會給錢?”
“要你給錢你來嗎?”
我不看她,眼睛朝向更遠的地方。整個餐館幽幽暗暗,只有我們這一排被白熾燈照著,其余均處在曖昧不清的光線中。酒保和服務員百無聊賴地靠著吧臺,有一兩個干脆趴在無人的餐桌上。
“等很久了吧。”方磊說這話的時候,我突然很厭惡他。
“也沒有很久。”我說,“我媽剛才來電話了,我可能馬上要回去。”
我站起來,很快往外走去,從這家店出去拐個彎,是新開通的一號線地鐵。這個點進去,可以趕上末班。坐到第六站,是我家附近那條街。一直坐到終點,就能到火車站。但我還是在家附近的那一站下了車。
路過四五個空的垃圾箱,我感覺眼前仿佛沒了屏障,天地為蓋,但我的身體卻有些僵硬,不能自由穿梭。沒有星星,月亮跟著我,也只是一掛隱隱約約的影子。我一路奔跑,它也跟著晃動,直走到小區盡頭的那棟樓,它才和我一起停下來。
我慢慢上樓,沒有走電梯。六樓并不很高,但我走了很久。很多房子都是空的,連門都沒有。戶與戶之間彼此通氣,我像一團飄忽不定的能量。
“今天回來挺早啊。”母親站在門口,不穿高跟鞋的她顯得很矮。我站在她對面,像一座細瘦的山,骨架挺拔,肉卻爬不上去。
“我睡衣呢?”
“洗了。先穿你爹的吧。”
我瞥見那套黑藍條紋的搖粒絨睡袍。它搭在衣柜門的把手上,看起來瘦瘦小小的。
“隨便吧。”套上它,兩肩陡然空掉一截。我有些難過。
方磊和宋慈的信息在群聊一欄不斷顯示,仿佛他們想交流又只能通過我傳遞。
“你爸回家了嗎?”
每當遇到無話可說的時候,方磊就會這么問一下。
我蒙上被子,像最開始住在這個房間時一樣。那一年我八歲,灑水車會在晚上八點穿過小區后面的那條街,車燈總能在我臥室的窗邊印下一道淺淺的光暈。
“給你爸打個電話。”母親常常這么說。
那時候城區沒有現在大,隨便走走,就能到城市的邊緣。我在各種地方看見過父親的車,有時候是在新開的洗頭城按摩城門口,有時候是在涮牛肚攤前。他比現在要精神,摻在一幫中年人隊伍里,格外挺拔。我站在人群里喊他,他不應,往往第二第三聲才看向我。
我像吊著一個影子一樣,把他帶走。快走到家門口的時候,他會在靠墻的一片花圃前小解。也只有那時候,他回歸每一個醉醺醺父親的本命。像長舒一口氣,又像停頓一下,繼續克制。他最終會跟我回家。
“我們知道你今天心情不好。”宋慈說。
“我不是因為這個心情不好。”
母親房間的電視聲越來越大,終于演變成哭聲。我屏住呼吸,努力不讓哈出的熱氣蒙住手機屏幕。我全身繃直,預備只要她哭到第五分鐘,就去她的臥室。可在第四分鐘,她就止住了。我放松下來,用被子蒙住脖子,接著是下巴、鼻子、整張臉。我右手掐住脖子,左手則緊緊捏著被角。終于,我感覺到一陣輕輕的眩暈,可這感覺也遠不如小時候。
那時候我們都喜歡去宋慈家玩。她家是一座獨立洋房,樓下帶大院子和游泳池。夏天的時候,方磊、我,都會去她家。我們給臥室上鎖,躺在宋慈父母的大床上,方磊在中間,我和宋慈的位置不斷變換。我們屏氣凝神玩裝死人的游戲,方磊總是忍不住,開始撓宋慈,宋慈先撲向他,然后撲向我。我們三個扭在了一起。她的手按在我的脖子上,我伸向方磊,他伸向宋慈。我們確信聽見了自己的心跳,雖然宋慈說那是脈搏。
中午的時候,宋慈媽媽會做一桌子菜給我們吃。如果不掉飯粒,她就準我們到游泳池里面玩。可方磊不喜歡游泳,只喜歡掉飯粒。那時候他最矮,看起來像我們的弟弟。當他坐在游泳池邊看著我們的時候,我們覺得應該照顧他。
“你們倆什么時候能像我媽一樣穿胸罩?”他問。
就這樣到下午五點,宋慈媽媽和宋慈會送我們到附近的商場,我在服務臺旁邊等逛街的母親,方磊等他做按摩的父親。那是我們城市當時唯一的商場,一樓是兒童樂園,我在那里見過很多小朋友,后來他們都離開了這兒。
“你以后會離開這兒嗎?”
“我爸說,我們這里的每個小孩都會離開。”
方磊站在我前面,一路隨自動扶梯下降、上升。我也跟著他,下降、上升。黑黑的折疊滾軸像要黏住我的頭發,將我吞沒。我將看著自己從腳下流過。
“你的零食!”
他在后面喊著,而我不看他。我決心離開這兒,去別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我一路狂奔,眼前掠過我們城市的諸多景象,日后它們都在回憶中沉淀成灰色——也或許,是很多種顏色攪在一起,成為了灰色。像少數獲得批準入住的居民,我們的家像在一排灰色樓墻上挖出了幾個閃耀的大洞。每當夜晚來臨的時候,窗戶透出不同層次的暖黃色光芒,也有時候是白色。它們彼此檢索著自己的位置,就像我和宋慈都喜歡站在窗邊往外望,雖然對面只有一棟新樓,而對面的對面還有一棟。我們猜測,那后面的后面的再后面許多,還會是一棟棟樓。有些可能不屬于我們城市,但也差不多。它們不規則地排出去,在整片大陸馳騁。它們彼此長得一樣,就像我們。
可我們一樣嗎?
我看著宋慈。藍色美瞳讓她的眼睛在一臉胖肉中顯得醒目。這比我的瞇瞇眼好多了。方磊徘徊在客廳,接著又走進廚房,最后,在臥室的木地板邊緣局促地坐下來。
“你家真是越來越小了。”他嗓音低沉,像螞蟻在我們腳下亂爬。
已經初一了,外面的鞭炮聲響起來,城市變得熱鬧,雖然再過一陣子,該走的又會再次上路。
“我媽打算把房子賣了。”我坐在床邊,“不過她叫價那么高,有人買嗎?”
“就算買了,真的有人住進去嗎?前陣子我在售樓處門口看見一個土豪,張嘴就要買一層。”
“你媽是想搬家,徹底離開這兒吧。”
“你真覺得你爸是因為她要走?”
“他早就想走了。”我說。
“誰不想走啊。”宋慈說。
“你不會走的。”方磊回過頭,“我也不會。”
他的兩條腿隨著身體轉過來。手比小時候粗壯許多,但每根指關節的形狀還是清晰利落,好像敲一敲就能發出響聲。宋慈已經開始玩手機,我看向別處。就這樣沉默了幾秒,他終于在我們中間躺了下來。
如果沒猜錯,母親這個點就該回來了,這個菜她買得有些久。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又去那些地方找父親了。我皺著眉,繼續看向別處,直到方磊的手按在我肩上才反應過來。接著,宋慈也按在了他肩上。我在等著他進一步向前,最好徘徊在脖頸,直接掐上去。
“你在想什么?”他的手停下來,另一只手撐著下巴。我只得坐起來。
“我們去外面吧。”
方磊應了一聲,宋慈不說話。像沿著一條外表光明的隧道,我們從最上面一層毛胚房走起,從客廳進了朝南的臥室,接著是餐廳、廚房、次臥和洗手間。這是一套復式房,最上面是個帶洗手間的尖頂小臥室。我們鉆上去,方磊探了探腰,身體像一張弓,把房間整個頂了上去,而宋慈的胖肉遮住一半陽光。
“去下面。”
我們來到了當年玩游戲的那間毛胚房。幾年來,它多次易主,每次易主都有些小變化,可每一個變化都未能讓它真的改變。和別處不同,它裝了窗門,只不過門一擰就開。這次我擰開的時候,地上掉落了一層細細的白灰。
和別處不同,這套房子只有一個大通間,據說,本要做商用房,可一直沒有公司搬進來。也有人說,要建藝術工作室,準備請一批畫家進來,可也沒有下文。
一側的水泥墻上,寫滿字跡拙劣的臟話。我撿起一截粉筆,在地上畫下浴室區、吃飯區、睡覺區等幾個位置,然后指向最中間的一塊:“當時我們就在這里。”
黃昏了。外面已是赤橙一片。天氣預報說今天有雪,可到現在也沒下,大概是不會下了。我有些焦躁,在房間四周踱步,右腳使勁摩擦著地板,皮鞋尖頭的形狀因而有些溫和。我突然覺得這套大通間真的是大,比我想象中還要大。外面已是藍黑色的天了。
“我媽還沒回來。”
“過年交通不好,外地的都回來了,地鐵都擠不上去。”
“如果真有那么多人,這兒怎么沒人呢。”
“我得去找她。”
我們的聲音墻灰一樣朝下一層層刮落。電梯停運,只好步行下去。
一開始真的在走,接著變成跑。我們穿梭在無數套毛胚房內,它們的邊界在夜晚模糊到不存在。我們的聲音——步伐、嬉笑,甚至還有干渴的呼吸,都清晰干脆,骨頭之間經過這么大的動作,也像透進了風,隨時都能和整個樓宇融為一體。
我們一路跨出這棟樓,跨出小區。路燈下都是夜色中形態模糊的行人。或站直,或駝背,甚或是坐在車上、輪椅里。
“你們走得太慢。”
沒有人回答,我吹起口哨。
馬路對面是一個戴小羊皮氈帽的男人,他挺拔的身姿讓人覺得是個青年,還有很多時間可以度過。這后來的時間能不能稱之為未來,我不知道。我看著他、他們,仿佛那也是我自己。我的動作和過去一樣,只是眼里盛著霧。我知道自己看得不夠清楚,可眼下只能如此。我還要跑,不是向著終點,不止向著母親,而是向著人群。那里有更多危險,更多安全。我知道自己還要更高,又或者終生都這么高,從此艱難地穿過人潮。
作者簡介:
王蘇辛,女,1991年生于河南,現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