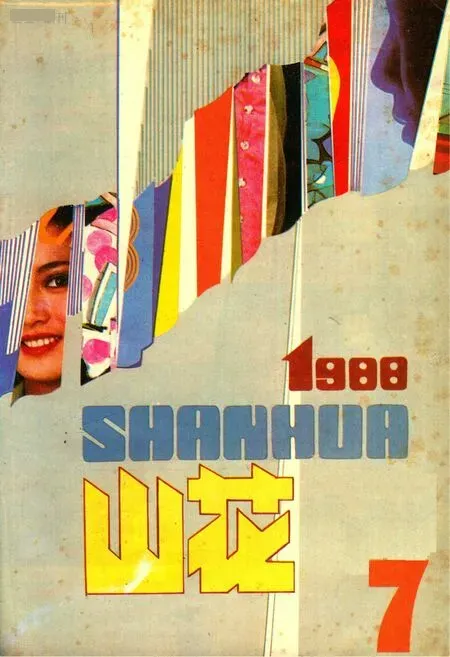說我的幾首詩
這些詩都是多年以前的作品。我都忘記了它們是怎么來的了。住在澳大利亞的荒原深處的朋友西敏(Simon Patton)翻譯這些詩的時候請我談談它們,以幫助西方讀者理解這些詩。這么多年以后,我與這些詩的關系已經是陌生人的關系,或許我可以對它們品頭論足一番了吧。我可以去追究它們到底要說什么,闡釋闡釋,就像我是我自己作品的詩歌教授。
《對一只烏鴉的命名》
我一般不會去想我寫的是什么。我其實并不確定我要說的是什么,我只是知道我已經說了什么。是的,我知道我說了一只烏鴉,一間房子,其它我就不知道了。詩是不知道的。有時候,他們告訴我,你寫的是這個,我喔了一聲,是嗎,我可沒想到。我還以為我寫的是那個。詩是詩人對語詞的召喚,聚合,但聚合之所也是開放之所,而不是在某種意義中封閉起來。對讀者來說,一本詩集似乎就是一本《奧義書》(古印度的一部經典),但是作者并不知道那奧義是什么,他召喚那些名詞、動詞、介詞(我比較不太喜歡形容詞)等等前來集合,是這些,不是那些,按照他自己的配伍排列起來,分行、斷句,這句長,那句短,這里是一個單詞,那里是一個詞組,那里是一個整句,就是這樣。我很講究語感、語氣,沒有語感,一首詩是出不來的,一首詩有一首詩的語感。有些詞是我忌諱的,我從來不用。或者它們習慣上是褒義的,我卻在貶義上與它們開玩笑。比如《0檔案》,里面全是些高大威武和莊重的詞,我戲仿它們,令它們滑稽陰險起來。比如《對一只烏鴉的命名》,這是一場語言游戲,我與烏鴉這個詞的游戲,它要扮演名詞烏鴉,我則令它在動詞中黔驢技窮。但是,這僅僅是語言學的游戲么,恐怕不是,這種游戲是富于魅力的,仿佛是為一只死于名詞的烏鴉招魂。它復活了嗎?我不確定。
一首詩是一個語詞的招魂之場,我經常想象我是那個甲骨文時代卜巫的巫師。我只是將我的語言游戲記錄下來。寫詩常常令我入迷,口干舌燥,忘記時間,筋疲力盡。我記得二十多年前我曾經穿越云南西部的高山,去一個納西族的村莊里與一位老巫師(東巴)見面,我目睹他的招魂游戲,我記得他在正午的陽光下大汗淋漓,一頭牛中魔般地忽然倒下。
我知道我要寫一只什么烏鴉,但我不知道這只烏鴉最終意味著什么。
奧義,如果可以明說的話,詩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奧義的魅力就在于,你永遠無法直接說出它,于是你得通過巫術、面具、語詞、藝術、舞蹈、音樂什么的。但是,人們往往會因此以為詩是暗示某種奧義的擺渡工具,這正是我忌諱的。對我來說,在一首詩中,奧義是不歸我管的東西,它是在語詞的途中自然生產的。我知道我寫什么,但這個什么不是奧義。詩是詩自己的游戲,奧義會在詩這個場的運動中生還。就像大河流動,河邊的人會感到震撼、濕氣逼人,似乎已經被波浪帶走、揣測遠方、大海……但也會感覺到干渴、疲倦、沉悶就要沒頂于黑暗。
我很喜歡烏鴉。在云南它們不常見,只是鬼影般地一閃。但是烏鴉這個詞卻是俗語,“天下烏鴉一般黑”,我小學時就知道。但我見過不能說是黑的烏鴉,但也無法說是白的烏鴉。烏鴉就是黑暗嗎,我不知道,每一首詩都是對黑暗的命名。
我寫詩,我希望黑暗自烏鴉飛出。我熱愛這種徒勞。
《啤酒瓶蓋》
就是這樣,晚餐時候,我看見一個朋友用開瓶器在一瓶綠色的啤酒瓶上撬了一下,它就“嘣”地一聲跳出去了。一個啤酒瓶蓋現在失去了它的用途,作廢了,被遺棄了,馬上就要被忘記,于是一首詩開始了。其實我已經看見過數百個這樣的場景,“嘣”地一聲。但語言并不覺醒。對此麻木不仁,不知道可以說什么。忽然有一天,那一聲“嘣”之后,我的語言也“嘣”地一聲,打開了,我記得這首詩寫得很快。
詩是先驗的。我只是召喚,復活之而已。
《致父親》
這首詩是用鋼筆寫的,后來我都用電腦了,只是初稿還先要記在小本子上,然后再用電腦修改。用電腦寫和手寫是不一樣的,手寫慢,因此思維必須非常集中,迅速記下要點。否則剛剛在黑暗里亮起來的那些詞就隱匿了。你必須快得就像抓住一道閃電,用石頭去擊中一條時速130公里的劍魚。
關于父親的詩我寫過三五首,這首最早。我父親一直不贊成我寫詩。他其實一直是文學愛好者,中學的時候組織過文學社,精通古典文學,毛筆字和古體詩都寫得很好。他對文學的判斷來自閱讀經典獲得的常識,這種常識數千年來一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通識,在1949年后中斷。在我出生的時候,他熱愛文學的前科已經被他隱匿起來了。他僅在春節寫副對聯。1967年,他被造反派將寫有“黑秀才”三個字的牌子掛在脖子上去游街,之后被流放。一夜之間頭發全白。有一次我發現父親藏起來的一些東西,里面有他青年時代報考博士生的報名表、閱讀羅曼·羅蘭《約翰·克里斯多夫》的筆記,我相當吃驚,他從來沒有表露過這些。很多年我根本不知道他愛好過西方文學。他絕口不提,也不準我寫詩。我只能偷偷地寫,到我年齡稍長,才慢慢明白在我父親的時代寫作會招來殺身之禍,并且這種危險一直在持續。但已經來不及了,我已經誤入歧途至深,執迷不悟,但我也不害怕,一直秘密寫著,等著有一天我的手稿被搜查出來似乎成了我的一種期待。對于我,寫作是一種黑暗。那時候中國沒有文學刊物,我不可能發表我的作品,我的詩是致命的,與我時代的語言背道而馳。我自虐般地想象著我的詩公布時世界大吃一驚的樣子,我渴望我的詩篇被查獲,以證明我生命的意義。我父親在政府部門工作了一輩子,直到退休,他屬于毛時代最后一批廉潔忠誠的干部。我與他的關系是多重的,有時候他是傳統的父親,仁慈,愛護、忠告,帶給我玩具。不準我寫作就是一種忠告,但他無法說為什么不準,他不能說。而另一些時候,他代表國家、政治正確。“于堅,你要遲到了!”“在學校要積極上進!”到晚年,他的這一面完全消散了,只剩下那個古老的父親。我記得他83歲的時候,對我說了一句,兒子,你寫得不錯。然后轉過身去繼續澆花。我一生似乎都在等著這句話。
《文森特·梵高》
我在80年代看到了梵高作品印刷品,他對我來說不是一位畫家,而是一位朋友,一位詩人。他是一位令人感動的藝術家,一位傳教士。我青年時代的偶像之一,有段時間,我以為自己就是梵高。他的激情、丑陋、燃燒、真誠和色彩都令我著迷。他在比利時礦區當傳教士的經歷,就像我自己。中國文革期間,國家將大批青年知識分子流放到工廠、鄉村,讓他們接受工人農民的改造,我16歲剛過,中學還沒有畢業,就被分配到一家生產礦山用的運煤車的工廠當鉚工。我經常會去礦山。那時候生活非常壓抑,國家奉行禁欲主義,我的青春期極度壓抑。梵高的經歷引起我強烈的共鳴,我能直覺到梵高藝術的起源。有時他令我想到李白。李白有一首詩寫到礦山的冶煉,“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郝郎明月夜,歌曲動寒川。”李白詩歌中的線條也是螺旋式地上升、旋轉的、燦爛的。
無比地熱愛生活,渴望生活,但是“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在自己的時代里永遠是麥田上的烏鴉。
《玉米地》
其實我并沒有見過詩中的場景。我青年時期,經常在故鄉的山崗漫游,荒涼、安靜,火棘上掛著一串串紅色的果子。似乎某個部落的祭祀剛剛結束,祈禱的聲音還在空地上彌漫著。云南與中國內地不同,這是一個諸神依然與人同在的地區,就像屈原詩歌描寫的那樣。云南深刻地影響了我的世界觀,萬物有靈對我是很自然的。那時候唯物主義猖獗,漢語里已經消滅神靈、祭司之類的語詞,我是復活者。另一次我在怒江峽谷漫游,忽然,歌聲響起,在江岸的空地上我看見傈僳人披著羊皮袍子,手拉手,彈著琴圍成一個大圈,邊跳邊旋轉。中間放著他們的行囊、酒瓶、野豬、玉米。
我很想加入他們的行列,但我身后有二十多個人坐在長途汽車上,他們迫不及待地要離開。我一生都在試圖回到這個隊列中去,我曾經通過愛情,友誼等等加入他們,但都失敗了,我只有通過詩。這是唯一可以使我加入到他們的行列里的道路。
《上教堂》
我第一次進入一座西方教堂是20年前在比利時的根特。我記得那是一個陰天。之前讀過許多西方文學作品,它們將教堂描寫得有血有肉,就像一位滿臉皺褶的老人。我已經很熟悉教堂,我自己虛構了一個“平素就有的”教堂。我以為教堂會很熱鬧,有牧師、有許多窮人,自己會像進入一個中世紀的村莊那樣受到款待。但真的來到一座大教堂里,它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巨大、森嚴、冰冷、陰暗、堅固、線條精確的辦公室。正面是十字架,后面是管風琴,使徒們的大理石雕像冷漠無情地屹立在黑暗里,掛著一絲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微笑。上帝的辦公室,但他沒有來上班。一個博物館,許多黃銅指示牌、有些區域用帶子隔開。我很奇怪,迷惑地跟著人們參觀這個地方,它并沒有我期待的那種法力。但是我還是很喜歡這些建筑物,它們令崇高、莊嚴這些抽象的概念變成了一個個空間,仿佛進入了大象的腹部。
我更喜歡小教堂,在西方,它們像蜂窩一樣,數不勝數。我記得在法國奧爾良附近的鄉村中有一個,因為詩人維庸在這里住過而著名。
小教堂是黃色的麻石砌成的,教堂中間鋪著彩磚過道,兩邊是長椅。只有三個窗子,兩個在祭壇的兩邊,一個正對著祭壇。這令教堂的光線很暗。教堂執事是一位滿頭金發、身材臃腫、戴眼鏡的女士。那時候已是黃昏,我因她的金發一亮而發現她,她在兩排禱告席之間晃了一下,似乎是剛剛顯身。她和我們說話的神情就像一位家庭教師,我以為她就要邀請我去品嘗她做的奶酪。但是她說,你們必須離開,我要下班了。
《翠湖公園》
我一生都是環繞著這個公園長大的,我熱愛它。我在它的湖水里學會了游泳,也曾經與女孩子幽會。但從前我不明白它對我的生活意味著什么,到了我中年時代,昆明城開始巨大的拆遷運動,許多古老的街道都被拆掉了,小巷幾乎完全被拆掉了,城市變得空蕩蕩。這時候我有一種嚴重的危機感,惶惶不可終日。我擔心他們把翠湖也填掉。如果這樣,我在故鄉就沒有任何熟悉的地方了,我童年長大的街道、小巷、四合院都拆掉了,只有翠湖幸存。這令我開始思考翠湖的意義。翠湖成了一個對象。它本是存在,現在它被趕出來,我思考它,歌唱它。寫作就是從世界中出來,但是我還能因為我的詩而回到這個世界嗎?
《尚義街6號》
古代中國詩歌有一種傳統,就是直接表現事實。比如王維的“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這是一個事實。但是,這個事實并非眼見為實。而是表現性的事實。一般所謂表現性的,只意味著寫意式的虛構。而在王維這里,詩人確實是眼見為實,但漢語是一種無法眼見為實的語言,它天然的表現性、模糊性令它永遠與現實隔著一層詩意的霧。漢語是圓的,而意義卻是一些直線。漢語就像毛筆一樣,有一種天然的表現性。中國山水畫也講寫生,“工畫而無師,惟寫生物”,但是無論如何寫生,水墨呈現的都不是攝影那樣的“生”。筆墨決定了中國畫天然的表現性。在水墨畫里面,如果是故意的寫意,那么就完全是抽象的了。
這種材料決定的表現性與西方的表現主義不同,它為“眼見為實”天然地賦予一種詩意的不精確性、似是而非。“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并非一個事實,而是一個“意境”,其意何在,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重要的是境,這個境詩人必須牢牢抓住,一不小心就容易墜入“意”的單向度貧乏。無境之意、無中生有易寫,“意境”、有無相生難寫。
“尚義街6號”實有其境。地址確實是昆明市尚義街6號。這是一幢位于昆明老城南部的、1947年建造的法國式的兩層臨街樓房。這條街及其周邊是舊時代僑民和商人集中的地區,看上去很像巴黎的某個街區。這個街區的興起正是由于1910年法國將一條鐵路從越南海防修筑到昆明,滇越鐵路的終點站就在這一帶。到處是梧桐樹,百葉窗和褪色的黃色墻壁。我在云南大學中文系的同學吳文光家就住在這里。尚義街6號的二樓,吳文光獨自占了一間七八平米左右的小屋,窗子開朝西面,在那里可以看見梧桐樹,落日,云南高原永遠蔚藍的天空以及另一幢法國式建筑的紅色屋頂上的鴿子,貓和麻雀。尚義街6號是80年代中期云南大學中文系一群大學生詩人、作家自發的地下小沙龍。我們之所以在吳文光家聚會,是因為當時這些朋友大都沒有單獨的房間,只有吳文光有。這里方便秘密談話,在那個時代,談論諸如薩特、索爾仁尼琴之類的名字都可能有人去告密。在大學生宿舍里,告密被許多人看成是一種公民責任,進步向上的行為。吳文光小屋的光線不好,永遠處于陰暗與朦朧之中,看不清事物的細節,只能把握一種整體的氛圍,猶如一處教堂中的懺悔室。我記得我們有過無數的談話,從存在主義到新小說派,從契訶夫、托爾斯泰到老子、莊子,從《癌病房》到《聶魯達詩選》,從帕斯捷爾納克到福克納,從《人·生活·歲月》到《城堡》、《變形記》,從斯大林時代到中東形勢,從法國電影到荒誕派戲劇,從蕭邦的音樂到黑人的舞蹈……話題關于西方現代派文學,關于氣功、關于中國哲學、關于中國政局,關于云南高原某幾天的天氣,關于女人、性交、關于生活方式……這個沙龍一周往往要聚會三四次,從黃昏持續到深夜。這些危險的談話和聚會成了我們的精神寄托,智慧得到交流,才華得到肯定,經常吵得面紅耳赤。在這里,我有一群非常優秀的朋友。我的詩在那時候很難發表,那時候詩壇流行的是想當然的、崇尚虛構的浪漫主義作品,普遍無視存在。我的詩表現了日常生活,這在中國那時的詩中相當罕見。尚義街6號的這些朋友堅定不移地肯定我的作品,給我極大的鼓勵。
將自己的朋友寫進詩里,是中國古典詩歌的傳統之一。杜甫有《酒中八仙歌》,李白有《贈汪倫》。這些傳統在文革之后中斷。《尚義街6號》發表時,引起很大震動,許多讀者不能理解,他們習慣歌頌國家英雄的詩,而此詩寫的是我的朋友,他們有什么資格進入“詩的圣殿”?這是一種庸俗而危險的生活和“心懷不軌的小人物”。本來,傳統中國是富有禪意的、熱愛生活的社會,文革令禪意喪失,生活成為罪行。我記得在1966年,人們的罪證包括胭脂、領帶、高跟鞋、發型、香煙甚至葡萄酒。人們指責這首詩粗俗、明白如話,沒有對生活進行“詩意”的升華。居然提到“裙子”“拖鞋”“空蕩蕩的大廁所”“雜種”,我相信這是那時代的漢語首次在詩中使用這些詞。我希望的是“直接就是”,直接就是、有無相生導致的隱喻、暗示、自嘲、微妙的反諷等等總是為我始料不及。那是一個被嚴密控制的時代,寫作是唯一可能的自由,我想我做到了。《尚義街6號》最初是在我和朋友創辦的地下刊物《他們》上面發表,1986年發表在《詩刊》第11期,那時候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詩人和評論家擔任了這個刊物的主編和編輯,因此它得以僥幸出現在這個國家最重要的詩刊的頭條。但是二十多年來,人們對這首詩一直褒貶不一,它的綽號之一是“非詩”,就像是我的一個罪行。一些讀者朗誦這首詩時喜歡將里面的人名換成自己朋友的名字,它有很多被篡改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