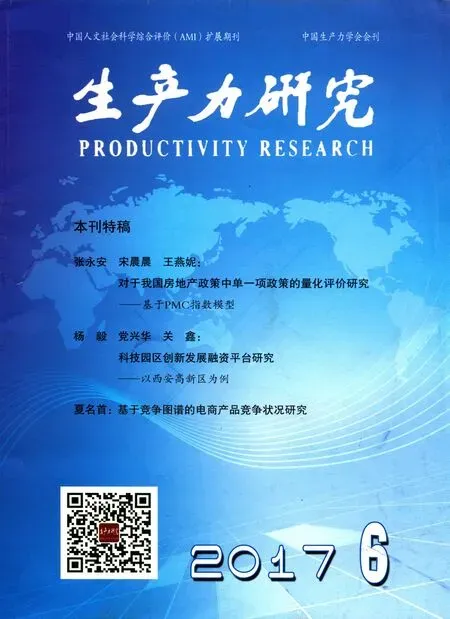內部治理對農村信用社支農效率影響的研究
——基于陜西省調研數據
王文莉,陳 園,謝瑞陽
(西安理工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54)
內部治理對農村信用社支農效率影響的研究
——基于陜西省調研數據
王文莉,陳 園,謝瑞陽
(西安理工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陜西 西安 710054)
農村信用社內部治理是影響其支農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選取陜西省2009—2013年43家縣域農村信用社的調研數據,運用D EA方法分別測度內部和外部支農效率,采用面板數據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結論顯示:股權結構、董事會、監事會特征及高管持股比例均與農村信用社支農效率相關,但顯著程度不同。基于以上結論,建議農村信用社應保持合理的股權和董事會規模,增加外部監事占比,加大高管持股比例,從而進一步提高其支農效率。
農村信用社;內部治理;支農效率
一、引言
長期以來,“三農”問題能否得到有效解決一直影響著我國改革發展的道路,而從金融視角出發來解決“三農”問題至關重要。農村信用社(以下簡稱“農信社”)作為農村基層的金融服務部門,具有隊伍龐大,網點眾多等優勢,并且在解決農村融資難問題,縮小城鄉差距,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等方面做出重大貢獻,一度成為我國金融支農的中堅力量。農信社的支農效果可以用支農效率來進行衡量,支農效率是指其通過自身資源為農村需求主體提供金融服務,并對推動“三農”發展所做的貢獻大小[1]。根據定義,可以將農信社的支農效率具體分為內部支農效率和外部支農效率兩種。其中,內部支農效率是指在一定存款的基礎上,農信社發放涉農貸款的額度和覆蓋面;外部支農效率是指農信社通過支農服務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發展所做的貢獻。然而,從目前來看,農信社的支農效率并不高。因為不管是涉農貸款的覆蓋度還是為“三農”發展的貢獻程度都是不夠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內部治理的不完善。
因此,本文嘗試研究農信社內部治理分別與內外部支農效率之間的相關性,考察制約農信社支農效率提高的關鍵因素,從而為農信社支農發展提出對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國外對農信社支農效率的研究大多從技術效率、規模效率以及政府政策等方面來探討,很少有從公司治理角度來研究的。大多數學者認為農信社綜合效率的提升源于技術效率的進步而不是規模效率(Andrew C.Washington,1999;Fu X and Polzin C,2008)[2-3];也有學者從政府政策角度研究,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過度看中政策性的目標就會導致農村金融機構綜合效率較差(Yaron,1997)[4]。但是,也有少數學者從股權結構、董事會和高管層來研究支農效率問題。對于股權結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權形式對農信社支農效率的影響上,有學者發現產權形式與農信社成本效率顯著相關(Neil Esho,2001)[5];而對于董事會主要從其監控管理來進行研究(Fried、Lovell and Turner,1996)[6];在高管層方面,主要考察高管層激勵的提高對效率的影響(E.Grifell-Tatje,2011)[7];對于監事會的研究幾乎沒有。
國內對農信社公司治理問題的研究大多從結構和機制來研究對績效的影響,研究與支農效率關系的文獻不多,但已有的成果為本文提供了有參考價值的研究思路與方向。
(一)關于股權結構對農信社支農效率影響的研究
國內學者大多通過產權改革與經營績效的關系來研究農信社的股權結構,有關效率的研究很少。目前研究股權集中度與農信社績效的結論主要有四種:正相關、負相關、不單一和無關。選取的樣本不同會導致最終得出的結果不同,因此應因地制宜的對農信社的股權結構進行設置。有關效率研究方面,一部分學者認為產權缺失是我國農信社效率低下的原因,并提出提高我國農信社效率的有效途徑——合作制(譚中明、張靜,2002)[8]。然而,實踐證明合作制不適合農信社的發展。
(二)關于董事會特征對農信社支農效率影響的研究
國內學者關于董事會特征的研究較多,但主要集中在董事會規模、會議次數以及獨立董事三方面對農信社績效的研究,對支農效率的研究也較少。在董事會會議次數與績效關系的研究上,主要存在兩類觀點:第一類觀點認為兩者之間關系不顯著;第二類觀點則認為董事會會議次數對績效有影響,但不同要素、不同時間、不同背景下影響情況不盡相同,其中董事會會議次數對財務效益性指標在統計意義上均不顯著,而對涉農貸款率有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金融研究處課題組,2008)[9]。目前已有很多學者開始研究獨立董事規模對農信社支農效率的影響,認為獨立董事對管理層進行監督,同時客觀評價管理者工作,對促進管理者提升農信社支農效率具有積極作用。
(三)關于監事會特征對農信社支農效率影響的研究
關于監事會治理的研究主要源于上市公司。大部分學者認為監事會在公司治理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目前我國公司治理結構中監事會基本形同虛設,沒能有效發揮監督職能(陳勝,2013)[10]。有些學者對監事會的特征進行了更加詳細的研究,認為監事會會議次數與規模越大,公司績效越好(卿石松,2008)[11],但也有學者認為規模的增大會導致“灰色監事”的出現,不利于監事會監管作用的發揮(薛祖云、黃彤,2004)[12]。
(四)關于高管層激勵機制對支農效率影響的研究
國內關于高管層激勵機制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結論:我國農信社高管激勵薄弱,容易引發信貸風險,阻礙農信社服務“三農”的職責發揮(劉賀磊,2012)[13]。高管層持股并不能對其形成長期有效的激勵,但是董事會成員薪酬激勵和股權激勵能夠提高董事會成員責任感和工作動力,從而提高支農效率(郝臣、徐偉、李禮,2005)[14]。
三、農信社內部治理對支農效率影響的機理及假設提出
本文分析內部治理對支農效率的影響機理,并在參照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及考慮數據的可獲得性的基礎上,從股權結構、董事會特征、監事會特征與高管層激勵四個方面提出假設,為后續實證研究打下基礎。
(一)股權結構機理分析及假設提出
股權結構是公司治理的基礎,它決定了農信社治理結構的構成和控制權結構。股權結構通過治理機制對農信社的支農效率發生作用,本文對股權結構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1.股權集中度對支農效率的影響。農信社不同的股權集中度對其支農效率有不同的影響。股權高度分散的情況下,由于分散的小股東缺乏監管力度,經營者容易利用個人職權謀取私立,易產生第一類委托—代理問題,從而阻礙農信社支農效率的提高;而股權高度集中情況下,絕對控股股東會聯合其他經營者為自己謀利以及利用各種方式去侵占小股東利益等,易產生第二類委托—代理問題,使得農信社資金外流,農戶貸款減少,農信社支農效率較低。相對以上兩種情況,適度集中的股權對農信社支農效率的提升有利。
2.股權制衡度對支農效率的影響。股權制衡度的高低對農信社的支農效率也有影響。較高的股權制衡度有利于解決委托—代理問題,因為當農信社股權制衡度較高時,任何一個大股東在做重要決策(如高管人員的任免)時都要考慮其他股東的意見,而不能隨意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并且農信社中存在一定量的大股東能更有效監督高層管理人員的行為。因此,股權制衡度高可以限制大股東對小股東的利益侵占行為,促使互相制衡的大股東們更有動力參與和監督農信社的經營管理,進而提高經營績效,但會降低支農服務的力度(hartarska,2005)。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
假設1:股權集中度與農信社內部支農效率成倒“U”型關系。
假設2:股權集中度與農信社外部支農效率成倒“U”型關系。
假設3:股權制衡度與農信社內部支農效率負相關。
假設4:股權制衡度與農信社外部支農效率負相關。
(二)董事會特征機理分析及假設提出
董事會的效力受到董事會規模的影響,較大的董事會規模與較小的董事會規模相比是不太有效的,這是因為當董事會規模較大時,其中一些董事會成員會產生道德敗壞,投機取巧行為(Jensen,1993),這一假設已經在大公司的董事會樣本中得到證實(Eisenberg、Sundgren&Wells,1998;Yermack,1996)。當董事會規模較小時,董事會不能很好地行使對經理人員的監督職責,造成經理人員出現懈職和推脫責任的情況,不能很好地履行經營管理職責,這樣就造成農信社內部管理混亂,經營遇到障礙,支農能力發揮受阻。董事會是連接社員與高管層之間的橋梁,提升農信社的支農效率,必須發揮董事會的功能,將其規模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Liption,Lorsch,1992)。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
假設5:董事會規模與農信社內部支農效率成倒“U”關系。
假設6:董事會規模與農信社外部支農效率成倒“U”關系。
(三)監事會特征機理分析及假設提出
監事會的職責是對董事會和高級管理者的經營決策以及業務執行情況進行監督,防止董事會、經理濫用職權,損害公司和股東利益。監事會功能的發揮,可以對“內部人控制”問題起到掣肘效果,進一步的降低委托—代理成本。監事會會議次數頻繁,監事會對董事會的監督作用就能夠體現出來,能夠及時發現經營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有些學者認為,農信社公司治理方面是外部治理在發揮作用,內部治理并沒有得到完全發揮,尤其是監事會職能(李永平,2009)。因此,在實際的公司治理中,增加外部監事的占比有可能會加強對農信社的監督力度,進一步提升農信社的支農效率,這一點有待后續驗證。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
假設7:監事會規模與農信社內部支農效率成正比。
假設8:監事會規模與農信社外部支農效率成正比。
假設9:外部監事占比與農信社內部支農效率成正比。
假設10:外部監事占比與農信社外部支農效率成正比。
(四)高管層激勵機理分析及假設提出
農信社的高管薪酬激勵制度可以有效避免委托—代理問題的發生。曹廷求和段玲玲(2005)的研究表明高管人員持股比例的增加會改善農信社的經營現狀,提高其支農服務的效率。馬宇等(2009)得出高管人員的能力越強,持股比例越高,則農信社的總資產利潤率越高,但對高管人員實行績效工資得出的結果卻相反。一般認為,對高管人員的激勵機制有利于提高其工作的積極性,進而改善農信社的經營績效,提升其支農效率。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
假設11:高管人員持股比例與農信社內部支農效率正相關。
假設12:高管人員持股比例與農信社外部支農效率正相關。
四、指標選取、模型建立與樣本統計特征
(一)指標選取
1.農信社內部治理指標的選取。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試圖尋找目前農信社內部治理中有助于提高其支農效率的經驗證據,驗證前面提出的假設。由于數據的可得性受限,因此采用股權集中度(top)、股權制衡度(g)、董事會規模(d)、監事會規模(j)、外部監事占比(l)和高管人員持股比例(s)來考察農信社內部治理因素對支農效率的影響。具體定義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定義表
2.農信社支農效率指標選取。本文將農信社支農效率分為內部支農效率y1和外部支農效率y2。鑒于農信社具有政策性服務“三農”的特點,本文選用非期望產出DEA模型測度其內部支農效率,修正的三階段DEA模型測度其外部支農效率。所用數據主要來源于調研,范圍涉及陜西省43個縣域農信社,發放問卷300份,收回問卷256份,問卷回收率達85%以上,達到要求。測度結果如下所示。
(1)農信社內部支農效率測度結果分析。陜西省2009—2013年各農信社內部支農效率平均得分為0.597、0.519、0.530、0.640、0.719。榆林神木、榆林府谷、商洛丹鳳和銅川宜君的農信社并列排在第一,排名在后面的四位分別為寶雞隴縣、漢中漢臺、漢中略陽和寶雞渭濱。
(2)農信社外部支農效率測度結果分析。陜西省2009—2013年各農信社外部支農效率平均得分為0.443、0.370、0.464、0.468、0.535。排名在前四的分別是渭南韓城、渭南蒲城、西安閻良和安康旬陽的農信社。
測度結果顯示陜西省農信社歷年內部支農效率平均值都大于外部,說明農信社在維持自身經營和服務“三農”方面選擇了前者,這正好反映了農信社在服務“三農”方面的弱化。
3.控制變量。本文選取資本市場完善程度(b1)、政府治理(b2)、信息披露(b3)、資本結構(b4)四個指標作為控制變量。具體定義如表2所示。

表2 控制變量定義表
(二)模型的建立
本文主要運用面板數據模型,采用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的方法對農信社支農效率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研究內部公司治理各個因素對農信社支農效率影響的情況。
首先,進行數據平穩性檢驗。由于樣本數據是面板序列,因此采用LLC、IPS、ADF和PP四種方法按三種檢驗模式對樣本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發現,四個統計量的p值均小于0.05。因此,判斷該序列是平穩的。
其次,進行 Pearson相關分析。結果發現不管在內部支農效率還是外部支農效率指標體系中,投入或產出指標內部均沒有強相關關系。
最后,確定模型的估計方法。本文采用F檢驗和Hausman檢驗后確定應該建立個體隨機效應模型。
根據以上分析,建立農信社內部支農效率影響因素面板數據模型為:
y1i=a10+a11top1i+a12g1i+…+a16s1i+b11i+…+ε,i=1,2,…,k
建立農信社外部支農效率影響因素面板數據模型:
y2i=a20+a21top2i+a22g2i+…+a26s2i+b21i+…+ε,i=1,2,…,k
其中,y1i表示第i個縣域農信社的內部支農效率,top1i,g1i,…s1i表示第i個縣域農信社內部支農效率的影響因素,b11i、b12i、b13i、b14i表示控制變量,a10為常數項,a11、a12、…、a16表示待估參數,ε表示隨機誤差;外部支農效率影響因素面板數據模型亦同。
(三)樣本統計特征
本文實證所用數據主要來源于問卷調查和財務報表數據,研究對象為陜西省農信社。鑒于數據的可得性,選取2009—2013年陜西省縣域共43家農信社內部治理的數據,其中12家農村合作銀行、7家農村商業銀行、24家縣聯社。
通過SPSS17.0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和篩選,陜西省農信社治理結構的統計特征如表3所示。

表3 陜西省農信社治理結構描述性統計
從表3可知,在股權結構方面,股權集中度最大為0.98,而最小為0,整體均值僅為0.192,說明陜西省農信社股權集中度差異明顯,從整體來看,股權集中度仍然較低。
在董事會治理方面,陜西省農信社董事會人數最多為11人,最少為0人,差異很明顯。但是,從整體來看董事會人數均值為4.85,略低于國家公司法規定的董事會人數2/3的下限,未來在董事會治理方面仍要加強董事會規模的構建,使其更加合理化。
在監事會治理方面,監事會規模均值為4.56,略低于國家公司法規定的監事會人數2/3的下限,說明陜西省農信社在應適當擴大監事會規模;外部監事占比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0.98,差異很大,說明陜西省農信社在外部監事設置方面不均衡,應加強外部監事規模的設置。
在高管層激勵方面,高管持股比例在0~9.012%之間變化,均值為1.168%,說明陜西省農信社高管層持股比例普遍偏低,不存在高管層控股的現象。
五、實證分析
(一)數據處理
在進行實證分析前,對樣本數據進行相關性的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1.股權集中度與內部支農效率相關系數為-1.021,說明股權集中度的平方與內部支農效率呈強負相關關系,符合假設;與外部支農效率相關系數為-0.065,說明股權集中度對農信社發放支農貸款服務三農的影響不大。
2.股權制衡度與內部支農效率呈弱負相關關系,跟假設相符;與外部支農效率呈強負相關,說明加強股權制衡改革可以有效改善農信社外部支農的效率。
3.董事會規模與內部支農效率相關系數為-0.047,說明董事會規模與農信社內部支農效率相關性不大,這與假設不相符,假設認為董事會規模與農信社內部支農效率成倒“U”型關系,但是結果仍具有一定的參考性;與外部支農效率相關系數為-0.108,跟假設相符。

表4 陜西省農信社變量相關檢驗表
4.監事會規模與內部支農效率正相關,與假設相符合;與外部支農效率相關系數為0.065,這與假設不相符,說明監事會規模的擴大對農信社發揮服務“三農”職責的幫助不大。
5.外部監事占比與農信社內、外部支農效率均正相關,與假設相符,但其對內部支農效率的影響大于對外部支農效率的影響。
6.高管層持股比例與農信社內外部支農效率均正相關。在實際操作中,增加高管層持股比例可以提高農信社支農效率。
(二)估計結果
回歸結果如表5、表6所示。

表5 陜西省農信社內部支農效率樣本系數表
通過以上研究發現,內部治理對農信社內部支農效率和外部支農效率的影響存在差異,主要有以下發現:
1.股權結構對支農效率的影響。股權制衡度對農信社內部和外部支農效率的影響程度一樣,都是顯著負相關關系,而股權集中度對內部支農效率的影響顯著,對外部支農效率的影響不顯著,這是因為內部支農效率強調的是涉農貸款投放的范圍和覆蓋面,外部支農效率強調的是服務“三農”的效果,而內部股權制衡度越高對內部支農效率的影響更加直接。

表6 陜西省農信社外部支農效率樣本系數表
2.董事會特征對支農效率的影響。董事會規模對內部支農效率的影響顯著,呈倒“U”型關系,董事會規模對外部支農效率的影響不顯著。董事會規模與農信社內部支農效率成倒“U”型關系,隨著董事會規模的擴大,農信社內部支農效率先增加后降低,這一結論符合假設;董事會規模對農信社外部支農效率的影響不顯著,不呈倒“U”關系。
3.監事會特征對支農效率的影響。監事會規模對農信社內部支農效率的影響不顯著,對外部支農效率的影響顯著,說明提高監事會規模可以明顯提高農信社外部支農效率值;外部監事占比對農信社內部支農效率和外部支農效率的影響都很顯著,說明提高外部監事占比,可以促進農信社支農效率的提升。
4.高管持股比例對支農效率的影響。高管層持股比例對農信社內部支農效率值和外部支農效率值影響都很顯著,說明提高高管層持股比例,可以刺激高管人員管理的積極性,對提高農信社支農效率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
六、結論
實證研究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1.適當集中的股權可以減少控股股東對各小股東利益的掠奪,防止集體利益被侵蝕。為此,農信社可以嘗試引進機構投資者和大型法人持股者或者動態股權調整機制。本文結果表明,股權制衡度對農信社內外部支農效率影響不同。隨著股權制衡度的提高,農信社的內部支農效率降低,外部支農效率提高。這就說明農信社應該結合實際,建立符合自身發展目標的制衡機制。
2.董事會規模與內部支農效率之間呈倒“U”型關系,所以農信社應確立合適的董事會規模,這樣才有利于其支農職能的發揮。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大多數農信社基本達到了理論上的合理規模,然而支農效率并沒有得到很大的改善,主要原因在于董事會成員的不作為,導致農信社實際權力掌握在董事長或者總行行長的手中,易造成“內部人控制”問題。因而,農信社今后應注重完善董事會的制衡機制。
3.外部監事占比的增加有利于農信社支農效率的提升。因為外部監事的存在可以對農信社的財務以及風險狀況進行及時充分的了解和監督,有利于農信社資產質量的提升。并且只有定期對外披露農信社的資產財務狀況,才能得到有效的外部監督,及時發現并解決問題,為農信社長期支農服務的發展打好基礎。
4.高管層持股比例對農信社內外部支農效率的影響都很顯著。因此,在實際中,要增加高管層的股權占比,這樣可以提升高管層的監督管理水平,督促其更好地提高農信社經營績效,提高其支農效率。除此之外,農信社還可以嘗試行政激勵、聲譽激勵等創新型激勵方式,不斷強化激勵機制的健全,促進農信社支農效率的提升。
[1]褚保金,張蘭,王娟,2007.中國農信社運行效率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地區為例[J].中國農村觀察(1):11-23.
[2]Andrew C.Worthington.Talmudist indi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Australian financial servic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Institutions and Money,1999(9):303-320.
[3]Fu X,Polzin C.Do Modern Technologies Work for the Rural ICT and Rural Credit Institutions in India?[R].Britain:University of Oxford,2008.
[4]Yaron J.,Benjamin and Piprek,GL.Rural Finance:Issue,Design,and Best Practices[R].World Bank,1997.
[5]Neil Esho.The determinants of cost efficiency in cooperative financial institutions:Australian evidence[J].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2001(25):941-964.
[6]H.O.Fried,C.A.K.Lovell,J.A.Turner.An Analysis of the Performance of University-affiliated Credit Unions[J].Computers Ops Res.,1996,33(4):375-384.
[7]E.Grifell-Tatj6.Profit,Productivity and Distribution:Differences across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the Case of Spanish Banks[J].Socio-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s,2011(45):72-83.
[8]譚中明,張靜,2002.農信社效率問題的產權分析[J].江蘇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116-118.
[9]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金融研究處課題組,2008.農信社法人治理與績效的關系研究——基于四川的經驗分析[J].農村經濟(11):86-91.
[10]廣東惠州農商銀行監事長陳勝.發揮監事會和監事長職能的思考[N].中國農村信用合作報,2013-12-24(7).
[11]卿石松,2008.監事會特征與公司績效關系實證分析[J].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3):51-55.
[12]薛祖云,黃彤,2004.董事會、監事會制度特征與會計信息質量——來自中國資本市場的經驗分析[J].財經理論與實踐(4):84-89.
[13]劉賀磊.農信社公司治理與信貸風險關聯度的實證分析[D].山東大學,2012.
[14]郝臣,徐偉,李禮,2005.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治理若干特征分析——基于2004年38家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管理現代化(5):62-64.
(責任編輯:C 校對:R)
F832.35
A
1004-2768(2017)06-0023-05
2017-03-20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公司治理視角下農村信用社服務能力的提升”(14BJY104)
王文莉(1968-),女,陜西楊凌人,西安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財會金融系教授,研究方向:小型金融機構信用管理;陳園(1993-),女,陜西西安人,西安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財會金融系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小型金融機構信用管理;謝瑞陽(1989-),女,陜西渭南人,西安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小型金融機構信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