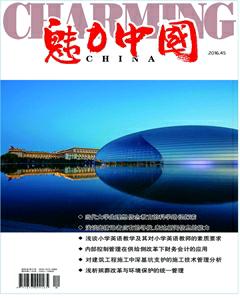濟慈的詩歌美學及社會政治意識淺談
賀思嘉
我國有不少時政評論家對濟慈的生平做出了簡介,其認為其是英國浪漫主義領域當中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詩人,其在英國詩歌領域政壇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之中既有浪漫主義的特性也有一定的 思想情感融入其中,其在詩歌當中所主要推行的就是永恒美的主旨。從另外一個層面上來說,通過詩歌當中情感的表達對人性進行反應,從而對現實世界進行諷刺。詩人濟慈其在年輕階段就在詩歌領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詩歌當中起主要所進行推崇創造力和想象力。
在對濟慈的政治思想進行評判的過程當中,不同黨派對其其中的內在思想所表達出來的內涵也有不同程度上的認知。但是在大致上我們分為兩種類型,其中一種觀念就是指濟慈在詩歌當中所表達出來的思想內涵就是遠離政治,避免塵世的煩擾,較為清高。得出這種觀念的依據主要就是其在詩歌創作的過程當中并沒有結合當時的政治形勢做出評判。這種原理塵囂的說法在當時的社會政治當中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其認為符合濟慈基本的人生觀念。
而另外一種政治思想主要就是認為其在詩歌創作過程當中,將永恒美以及想象力作為其詩歌創作當中的根本觀念,從另外一種視角之上也就是說其對于現實生活的逃避,不能夠直面現實社會。對于永恒美的追求也就是濟慈逃避現實的另外一種映射。
濟慈詩歌在20世紀中期當中可謂是發展到了黃金階段,究其主要原因主要就是因為新批評派對于濟慈詩歌當中的種種見解進行研究和調查工作,但是卻不用傳統的眼光對濟慈的詩歌進行具體的評判。也就是其切斷了與傳統詩歌之間的聯系,使得濟慈的詩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約。經過時間的不斷推移,濟慈詩歌的探究工作仍舊傳承并延續這這種原則。在20世紀80年代當中解構主義批評家保羅.德曼在對濟慈的詩歌進行定位的過程當中,主要就是將關注點集中在詩歌的文化性方面。其對于濟慈的詩歌做出了這樣的評價,在對濟慈的詩歌進行閱讀的過程當中,其之中的洞察力主要是在日常生活習慣之中鍛煉得出,其詩歌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經過以上的分析研究我們對濟慈詩歌當中政治原則以及所表達的主要思想觀念進行描述,其思想觀念是否真的是遠離政治生活、追求寧靜。濟慈在創作的黃金時段,是否單純的對藝術的永恒性進行追求,在此階段當中對于藝術的追求已經達到了一定的境界。但是在對永恒美以及創造力進行追求的過程當中,其并沒有完全的與現實生活相脫離,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上對于現實生活當中的社會背景進行映射。其對于生活的追求同時也是浪漫主義的體現,但是實際生活當中的丑陋必將與浪漫主義的特征產生聯系。詩人通過時間的磨煉以及世事無常從而對自身的美感進行境界的提升。對于美感的享受,詩人對其有著自身獨特的理解,其認為美感即游離于現實社會當中同時又來源于現實社會,只有經歷過社會的丑陋不堪以及底層社會當中世態炎涼才能夠衍生出對于美感的追求,想要將自身投身于美的事業當中。
濟慈在初期進行詩歌創作的過程當中其本身的思想受激進思想的影響較大,其中李亨特對于濟慈的思想探究較為強烈,我們對此進行評判的主要依據就是其對于政壇上的的激情以及對于社會不公平現象的無情鞭撻。法國在經歷過法國大革命之后其經歷了資產階級革命。但是經過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之后,法國大革命當中所進行提倡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已經深入人心。濟慈其早期階段當中經歷過法國大革命,使得其骨子當中就具有一定的反抗思想,也正是由于該種情況使得其創作的詩歌更加具有感染力。但是,濟慈其本身也并不是通過詩歌來作為其政治斗爭的武器。
有批評家認為,濟慈所接受的幾乎完全是英國詩人的影響教育。他所習得的都集中于前人的作品。當然,濟慈受到文藝復興時期詩人的影響和早期浪漫主義及他同時代的浪漫主義詩人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但這并不是他詩歌經驗的全部。生活的本身對于他來說就是一部作品,培養著他內心中的人文主義情感。前人的思想在促成了這種情感轉化為他詩歌經驗中的人文精神潛質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在自覺地追求將詩歌審美與人文主義精神相結合這一點上,濟慈努力超越前人。他清醒地意識到詩歌中的內在生命力和創造力與現實世界的關系,在把對現實的批判和對永恒之美的追求溶入詩歌的時候,濟慈發現了詩歌與現實生活關系中的美學價值。
在濟慈的詩歌創作過程當中,其隱士的思想能夠在一定層面上進行映射和體現。濟慈在進行詩歌美感創作過程當中,對于審美意識有著高度的敏感性,其通過人文主義的內涵對其中的內在思想進行體現。其當中所進行討論的政治意識以及文化美感都在新批評歷史主義當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使得其詩歌能夠朝向人性方面進行更一步的發展,使得人們的認知程度也能夠得到凸顯和提升,從而對于濟慈詩歌當中的理論觀念以及其所進行表現的中心思想進行深入探究。
參考文獻:
[1]王僴中.濟慈的詩歌理念及其詩美藝術空間營造[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04:175-180.
[2]陳金平.《詠春》之美——濟慈的詩歌創作源初探[J].保山師專學報,2005,04:69-70
[3]羅義華.約翰·濟慈的詩歌與道德關系研究[J].外國文學研究,2005,05,:51-57+171
[4]李嘉娜.《詩品》視野下的濟慈詩歌創作——兼論西方濟慈詩評[J].中國比較文學,2007,03:168-180.
[5]游牧,邱儀.《恩底米安》與濟慈詩歌的神話唯美主義[J].東疆學刊,2009,04:32-39
[6]張鑫,王清海.“消極的才能”及其完美的注腳——濟慈詩歌《希臘古甕頌》評析[J].南都學壇,2002,05:66-69.
[7]耿寧,孟祥玲.論植物意象在濟慈詩歌中的應用[J].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1:113-117.
[8]劉新民.濟慈詩歌藝術風格散論[J].外國文學評論,1997,02:115-120.
[9]王永光.濟慈詩歌中的三種情感類型[D].上海外國語大學,2008.
[10]馬玉鳳.美即是真,真即是美——濟慈詩歌美學述評[J].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03:56-59.
[11]馬瑜.對濟慈詩歌意象的結構分析[J].云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04:87-89.
[12]劉治良.花神的國度想象的世界─—濟慈早期詩歌淺析[J].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03:68-72.
[13]劉朝暉.試比較克里利的詩歌尺度與濟慈的“消極能力”[J].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0,02:14-19.
[14]劉治良.濟慈詩歌創作成因探源[J].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04:58-62+39.
[15]邱儀.簡論濟慈的詩歌美學思想[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S1:46-50.
[16]鄭興茂.憂思與理想:從生態視角解讀濟慈的詩歌《夜鶯頌》[J].海外英語,2014,09:225-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