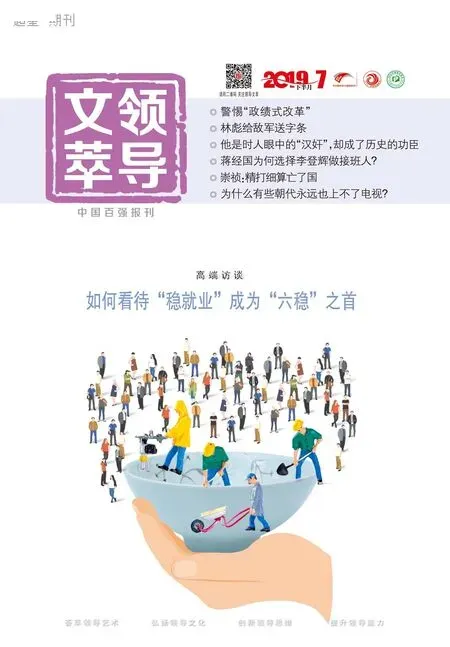為什么美國經常沒有安全感?
米爾斯海默
喬治·凱南(1904~2005),美國外交家和歷史學家。遏制戰略是整個冷戰期間美國應對蘇聯威脅所采用的戰略。喬治·凱南是冷戰早期一位關鍵的政策制定者。1947年4月,國務卿喬治·馬歇爾讓喬治·凱南建立了政策規劃司,該機構隨后成為美國國務院的長期智庫。在制定美國外交政策方面,馬歇爾非常倚重凱南的建議。確實,凱南在制定馬歇爾計劃中起了核心作用。
1926年,普林斯頓大學畢業一年后,凱南以外交官身份開始了其職業生涯。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里,凱南被派往多個歐洲國家,其中包括三次去德國和蘇聯游歷。他近距離目睹了希特勒的崛起和斯大林的統治。因此,在20世紀,凱南對這兩個最強大和最具影響力的歐洲國家所知甚多。在那些年里,對塑造美國外交政策來說,這兩個國家理所當然比任何其他國家更為重要。
凱南認為,權力是國際政治的貨幣,盡管大多數美國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國家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歐洲權力均衡。對美國而言,理想的境況就是歐洲“均衡”,或是我所說的平衡的多級體系。特別是,在歐洲大陸上應當由少數幾個大國,任何一個大國都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去支配其他國家。英國地處歐洲但不在歐洲大陸,應當扮演離岸平衡手的角色。換言之,當需要遏制一個國家因過分自大而試圖引起不均衡時,英國應當在歐洲大陸使用軍事力量。凱南認為,平衡的多極化有利于歐洲的和平并使美國安全。因為沒有歐洲大國能威脅歐洲的穩定和美國的安全。
對歐洲和平和美國安全的巨大威脅是地區霸權,即一個特別強大的大陸國家能夠支配整個歐洲。凱南寫道:“沒有一個歐洲大陸強國能夠支配整個歐洲大陸,這對我們和英國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他的推論直截了當:歐洲霸權應當“既是海上強國,也是陸上強國,削弱英國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如此——開始進行對我們懷有敵意的海外擴張。這一擴張是以亞歐大陸內部巨大的資源為支撐的”。相反,如果歐洲存在均衡,那么任何一個歐洲強國都很難自由地在世界各地馳騁——尤其是在西半球。
美國依賴于英國維持歐洲權力均勢,英國在幾個世紀以來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結果就是,美國“處在英國艦隊和英國大陸外交背后”,以得天獨厚的位置安全且容易地行事。實際上,倫敦和華盛頓都對確保沒有一個大陸強國能夠控制歐洲這一問題十分關注。但是,由于英國在地理上接近歐洲大陸,美國能夠袖手旁觀,讓英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遏制有抱負的歐洲霸權。簡而言之,美國可以把責任推卸給英國,英國實際上是美國的第一道防線。
然而,如果英國陷入麻煩,不能完成任務,美國就不得不插手,幫助遏制潛在的霸權。凱南說,這一邏輯解釋了為什么威爾遜政府在一戰中,甚至在1917年4月美國參戰前就對英國提供援助。凱南寫道:“隨著時間的推移,沿著這樣的前景,無疑發生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事情:意識到協約國失敗的危險,并意識到作為世界強國的英國被淘汰出局對我們的世界地位帶來的損害……其結果就是日益增長的親協約國情緒。”盡管美國“由于一個中立問題”參戰,然而,一旦它與德國交手,就很快意識到“避免英國戰敗的危險”和遏制德意志帝國是當務之急。
同樣的地緣政治邏輯也能夠解釋美國在參加二戰前后的行動。1940年6月法國戰敗后,羅斯福政府深感擔憂,如果戰勝蘇聯,德國納粹可能會將英國淘汰出局,最后占領全歐洲。因此,早在1941年12月參戰以前,美國就支持英國。實際上,羅斯福總統竭盡全力使美國參戰以確保英國的生存和納粹德國的毀滅。
對美國來說不幸的是,二戰后歐洲形成了新的不平衡。這有助于解釋為什么凱南對1950年美國的地位如此失望,也能夠解釋為什么他提出了遏制戰略。蘇聯從巨大的沖突中脫穎而出,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蘇聯實際上是如此的強大,以至于沒有哪些歐洲國家能夠形成均勢聯盟以遏制它。德國被摧垮并一分為二,其中一部分被蘇聯軍隊占領。英國和法國被戰爭嚴重削弱,并且二者都有自己不得不守衛的帝國。這使英法將注意力和資源從歐洲轉移出來。盡管美國最終將獲得英國、法國、意大利和西德的幫助,但只有美國有能力遏制蘇聯。
20世紀30年代末,歐洲兩個最強大的國家就是納粹德國和蘇聯。二者是死對頭,并都具有擴張主義的目標。西方民主國家——英國和法國——與兩國關系不好,因此無法與莫斯科合作來遏制德國。如果必要,也不能與德國合作來遏制蘇聯。因此,到了1939年,歐洲就是一個火藥桶。
但是,在發生戰爭的情況下,如果兩個“極權大國”結成聯盟,那么民主國家既不能打敗納粹德國,也不能打敗蘇聯。即使美國參戰,情況也依然如此。英國和法國打敗德國或蘇聯的唯一辦法就是他們與蘇聯或德國中的一方結盟。但是,在這種情況下,“與英法協作的極權大國”最終會占領歐洲大陸的東半部分。在這種情況下,這個極權國家將比歐洲任何一個國家都強大得多,歐洲將不會有均勢。實際上,西方民主國家面對的是一個經典的霍布斯選擇。毫無疑問,他們都支持蘇聯對抗德國,“憑借著軍事行動的磅礴氣勢”,在二戰結束之際,紅軍到達了歐洲的心臟地帶。那時,美國別無選擇只能扮作最終的平衡手,駐守歐洲對抗蘇聯。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凱南在《外交事務》上發表了那篇著名的關于遏制的文章。
不必驚訝,凱南思考亞洲權力均勢的方式與思考歐洲權力均勢的方式如出一轍,盡管在凱南時代,亞太地區對美國的戰略重要性較小。20世紀上半葉,當時有兩個大國:日本和俄國。凱南不無贊賞地指出,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意識到美國在日本和俄國之間保持權力均勢符合美國的利益。所以,用羅斯福的話說,“每一方都能對另一方采取有節制的行動”。
凱南認為,俄國作為強國,是更大的威脅。而日本作為島國,與英國很像,可以扮演離岸平衡手的角色遏制莫斯科。因此,在《美國大外交》一書中,凱南傾向于對日本持非常同情的態度。
隨著日本在二戰中戰敗,亞洲再沒有美國可以依靠以遏制莫斯科的大國,這意味著與歐洲一樣,美國不得不披上遏制的斗篷。
如果中國經濟在未來幾十年以最近幾十年的方式繼續增長,那么中國會成為亞洲迄今為止最強大的國家。如果凱南還健在,他會希望日本在遏制中國時發揮核心作用,正如他希望東京去遏制莫斯科在亞洲的野心一樣。不幸的是,即使是與中國的亞洲鄰國聯合,日本也不足以承擔這項任務。因此,美國將不得不增強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在召集遏制中國的均勢聯盟方面發揮帶頭作用,正如在冷戰時期對蘇聯那樣。
考慮到凱南的聲望與他的遏制觀點如此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考慮到美國會下苦功夫遏制正在崛起的中國,更為認真地考察凱南1947年文章中關于這一戰略的所說內容是有意義的。
(摘自《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