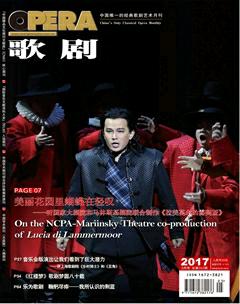懷念我的二姑荊藍
劉小蘭


我爺爺奶奶一共生了七個孩子,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陜北農村的生活相當貧困,有兩個孩子很早就夭折了,只活下來五個,二姑荊藍排行老三。她的原名叫劉金蘭,參加工作以后,改成現在的名字。
聽父輩們說,早年她是陜北綏德師范的優秀學生,校宣傳隊的活躍分子,由于對文學和戲劇的熱愛,考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
1947年,二姑進入華北聯大文藝學院學習俄文。入學的時候,她完全沒有俄文基礎,由于生性努力又不服輸,每天早上五點起床,在學校附近的樹林里大聲朗讀、背誦課文,刻苦用功,很快就趕上并超過班里的同學,成績名列前茅。她的俄文發音非常標準,深得老師的喜愛,晚年時她曾跟我談起過那段經歷。在那個時期,她還閱讀了大量俄羅斯原文名著,這些為她日后的表演和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俄文系畢業后,她本來可以做一名優秀的翻譯,但她心里還是放不下戲劇,最終她選擇了在中央歌劇院做一名歌劇演員。
我對二姑有印象是在“文革”后期,那時我的父母在干校勞動,我到了上學的年齡,就來到北京的二姑家,同爺爺、奶奶、二姑、二姑父一起生活。
“文革”期間,很多人都受到沖擊,我的大姑、大姑父由于早年參加過“三青團”的經歷,在60年代被停發工資、銷除戶口,下放到邊遠的農村勞動改造,家里的四個孩子沒有生活來源,無依無靠。二姑、二姑父雖然也挨整,但是生活還是有保證的,大姑家遭難,二姑給予了無私的幫助。記得二姑每月給大姑寄生活費,接濟他們全家的生活,并且常常寫信,鼓勵他們要堅強地活下去,相信黨和國家最終會還給他們公道。
我上小學時,二姑家住小西天一號總政大院,家里親戚朋友川流不息。三叔在新疆、大姑在寧夏、我父母在干校,誰家有困難,到北京來都住在二姑家,她都會給予幫助。我在她家和劉家同輩的孩子們生活得很愉快,也建立了很好的友誼。
盡管是借住在二姑家,她對我們的教育和管理是很嚴格的。我小時候相當淘氣,像個男孩子。記得有一次,爺爺派我去副食店買醬油,出了家門正巧碰上同學約我一起玩兒,我心想離做晚飯還早著呢,于是就跟同學大玩特玩起來,完全把買醬油的事情忘得干干凈凈。當時正值盛夏,天氣很熱,玩累了想吃冰棍,就把爺爺給的買醬油的一毛錢買冰棍吃了,等天黑了回到家才想起醬油的事。這可壞了,不但事兒沒辦,還把錢花了,想補救都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如實向二姑交代。為此她把我狠狠地批評了一頓,我哭了半宿,從此再也不敢貪玩誤事了。
小學三年級,我的父母先后從干校回到北京,我也搬回自己家住了,但是每逢周末和放假,我都會到二姑家聚會或者小住。在那個年代,物質生活十分匱乏,姑父在部隊,他的戰友或部下有時候會從外地帶一些“好吃的”過來,每當這個時候,二姑會招呼我們過去吃飯,到她家大吃一頓解饞,那是我們當年最快樂的事情。那時沒有電視,其他的娛樂活動也不多,二姑家有好多報紙雜志,每次小住,她都會指導我讀書。這些東西別人輕易不讓動,但對我例外,《小說月刊》《十月》《當代》《譯林》等等,閱讀成疊的雜志不僅豐富了我的假期生活,也為我后來的學習工作打下了基礎。
到上世紀90年代,二姑家熱鬧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先是爺爺奶奶相繼過世,姑父1994年也病故了,兒子曉里因孩子上學分出去單住,一家七口,轉眼間只剩下二姑一人。
二姑與姑父丁里相差12歲,他們的感情一直非常好。姑父從1957年“反右”時就得了糖尿病,“文革”時期又得過心梗,二姑對他的飲食起居照顧得細致入微。盡管她有時候脾氣很壞,但對姑父從來沒有發作過,他倆始終相敬如賓,讓我們這些后輩非常羨慕。隨著姑父身體越來越差,住院的時候越來越多,二姑每天雷打不動地坐地鐵到301醫院陪伴,從沒有半句怨言。
姑父丁里是一位杰出的革命藝術家,是解放區和新中國文藝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姑父去世后,二姑十分悲傷,但她沒有沉浸在悲傷中,而是以年近70的高齡開始學習電腦打字,去圖書館查閱資料,聯系總政有關領導,編輯整理姑父生前創作的劇本、文章和導演手記,用了將近十年的時間,出版了《丁里藝術集》和《丁里漫畫集》,為后人研究姑父的藝術思想和藝術成就。集結了寶貴的財富,也寄托了家人對他永久的懷念。在此之前,我只知道姑父曾經在總政文工團和總政文化部擔任要職,對他的生平和創作并不了解,二姑編寫的這兩本書,才讓我真正了解了姑父,他的才華、他對藝術的執著、他對新中國文藝的貢獻值得我們學習。
2005年,二姑唯一的孩子丁曉里(我的表哥),因病離開了我們。白發人送黑發人,這對二姑的打擊可想而知。第二年,二姑因悲痛罹患子宮癌,由于發現及時,年近80的她接受了手術。當時我們都非常擔心她的身體,怕她過不了這一關,然而手術后,她沒有自憐,也沒有沉寂,而是組織歌劇研究會的老專家們,在經費困難、人員不足的情況下,編纂了長達近百萬字的《中國歌劇史》,填補了中國歌劇創作的空白,為后人留下了一部資料翔實、文字流暢、有極高學習參考價值的歌劇著作。
曉里走后的十來年里,我與二姑走動得比較多,盡管親人的離去給她一次又一次的打擊,但她始終非常樂觀。她是個熱愛生活的人,家里總是收拾得干干凈凈。她喜歡養花,空閑的時候我會到花卉市場幫她買花,有的時候陪她上街買衣服、買生活必需品,偶爾出去吃吃飯,而每年最重要的聚會,是大年初三到她家包餃子。
記得2015年,在她家,包好的大餃子她吃了20個,比我們“年輕人”還能吃;2016年初三,她只吃了5個餃子就放筷子了,我好奇地問一向胃口很好的二姑為什么不吃了,她說沒什么,只說覺得胃脹,不想吃東西,當時大家都沒在意,只是囑咐她盡早到醫院檢查;到今年初三,大伙包好了餃子,她干脆一個都沒吃,只是靠在躺椅上昏昏沉沉地休息,而且消瘦得厲害,我預感到事情不好,卻由于工作太忙,沒有抽出時間再去看她。4月10日,她安安靜靜地離開了我們。
回想二姑的一生,早年離家奔赴延安參加革命,解放后在歌劇院兢兢業業地工作。她對家人的關愛,是我們的榜樣;她的笑容、她的樂觀、她的大嗓門、她對我們的批評與教誨,至今仍歷歷在目。在她離休以后,特別是晚年當親人一個個離她遠去以后,在孤獨困苦中,她以堅強的毅力,克服困難、奮力崛起,用積攢了半生的精力和人脈,做了大量有意義的工作。她的精神,值得我們后輩永遠懷念、敬仰、學習!